或许你从没踏入心理卫生学院(前身为板桥医院)。
但对1093名长期住院者来说,这是他们住了短则一年,长则数十年的“家”。
长期住院者中,有些可能会在医院终老,有些可能住了十多年后终于出院。
他们熟悉医院里的规则与生活,但也因此失去自由与自主权。
脱离医院体制回到主流环境工作或生活,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否陌生又冰冷?
心理卫生学院的医生、护士、职能治疗师、义工和长期住院者,带我们走进这个世界,看看各方如何一步一脚印助长期住院者融入社区,公众又要如何包容及给予支持?

长期住院者的24小时
每天24小时,你怎么过?
心理卫生学院长期住院者的24小时,规划得清清楚楚。
平日,七点左右起身。吃早餐,吃药,到花园散步或做点美术手工。
中午左右吃午餐,吃药,小休。午后可能有园艺、烹饪课或体育活动。
傍晚六点左右吃晚餐,接着在附近散步,然后吃药、梳洗。晚上九点上床睡觉。
周末,期待义工策划的手作课或表演,有时外出郊游,或到不同景点走走。
日复一日,心理卫生学院(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IMH)长期住院者的生活,或许就这样年复一年。

对于长期住院者来说,医院是熟悉的环境,日常事务都由医疗人员安排妥当,或许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但安定的代价是失去自由和自主权,不少长期住院者仍希望:找到工作,出院回家。
IMH如何照顾长期住院者?
心理卫生学院大约有2000个床位,其中1093个属于长期住院者。根据医院定义,住院一年或以上,就是长期住院者(long-stay patients)。每个长期病房大约有50个床位,有些人住了长达数十年。
让患者长期住院,绝非医疗目的或常态。一般来说,医院会尽力尝试帮助患者出院,例如让患者回家或转到其他疗后护理(step-down care)机构,如后港康复中心和四美康复中心。除非所有出院方法都行不通,否则一般不会长期住院。
大部分长住者至少65岁
目前,心理卫生学院长期住院者的年龄从20多岁到九旬以上,五六十岁男性占最大比例,年龄最大的两人高龄101。长期住院者之中,最常见的病症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有些人也同时患有某个精神疾病和智能障碍,如要独立生活,可能面对一些困难。
但困难未必无法克服。无论在心理卫生学院住了多久,无论是否和亲友失联,出院绝非不可能的事。
心理卫生学院医疗委员会副主席(临床品质)苏心荃助理教授说:“长期住院之后,要重新站起来并不容易。但我相信我们的长期住院者并非如此无助,只要相信他们,愿意赋予他们自主权(empower),给予机会,他们就会有显著的进步。”

苏心荃医生坦言自己是个乐观的人,但他这番话不只是乐观推算而已。事实证明,只要有足够支持和指导,长期住院者不但可以出院,还可以工作、自力更生。
三年前分组护理
2015年,心理卫生学院开始一项新企划。医院根据长期住院者的敏锐度和生理情况把他们分为六个组别,以便更好地满足各组照护需要。
六个组别包括:高龄组、临终和缓医疗组、智能障碍兼精神疾病组、维持性治疗组、病情未稳定组,以及缓速康复疗程组。各组需要不尽相同,例如高龄组因年龄关系,跌倒和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更高;临终和缓医疗组因为患上生理疾病,医生估计可能只剩下一两年寿命,所以心理卫生学院会和其他医院医生合作,为患者提供善终护理;智能障碍兼精神疾病组则比较需要多感官活动。
苏心荃医生说:“智能障碍兼精神病患者的需要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没有太多物质奢求,只要有某种他们喜欢的东西,例如某种食品、某个绒毛玩具、某种香氛或某种音乐,他们就会心满意足。”
维持性(maintenance)治疗组则因为是长期患病(例如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受治疗),因此不适宜太复杂的康复疗程,以免给他们造成太大压力。
至于病情未稳定这个组别,其实很快就会取消。医院为这组患者提供客制化疗程后,患者病情大致上都已经稳定下来,所以会转入其他组别。
出院概率相对较高,就会被编入缓速康复疗程组。
拟定可达成目标的疗程
缓速康复疗程(Slow Stream Rehabilitation)的宗旨是帮助长期住院者恢复自信,以及提升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康复水平,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最后出院并融入社区。
工作与出院不是医院单方面设下的目标。策划缓速康复疗程的时候,由职能治疗师、护士和医生等人组成的医疗小组与长期住院者细谈,了解他们的强处、兴趣、目标与想望。结果大部分住院者表示,希望有机会接受职能培训,多参与医院外的活动,以及出院。
医疗小组成员之一,高级执行护士吴艾思说:“长期住院者和你我一样,也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望。不过,有些目标不一定容易实现,我们的责任是和住院者沟通,和他们一起拟定一个有意义的目标。”
她举例:一名在医院住了十多年的男住院者想要到国大念书,但他已经四五十岁了,加上住院多年,念大学始终是比较遥远的目标。
吴艾思说:“我们和他讨论其他较可行的目标,毕竟他在医院住了十多年,或许不熟悉其他升学管道。”
医疗小组和长期住院者讨论并拟定目标,接着会为他们设计能够帮助他们达到目标的疗程。疗程内容包括多了解病症及自己服用的药物;自己做家务如洗衣;学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以及社交沟通技巧。
让长住者行使自主权
多年来,长期住院者生活大小事都由医疗人员负责。这个做法或许最安稳,但代价是失去自主权,甚至久而久之失去一些能力和技巧。
苏心荃医生说:“住在医院,所有日常事情都由医疗人员代劳,像每天要服用的药物,一般都由护士分发。我们尝试改变这个做法,所以安排一些住院者上课,并给了他们自己专用的药盒。不过,医院最重视的就是安全,要改变常态并不容易。最大的障碍其实是说服医疗人员为什么必须改变,所以在组织缓速康复疗程的医疗团队时,我们特别用心挑选适当人选,还一起到港台的医院考察。当然,改变是一种冒险,万一出状况,我们必须全力支持医疗人员。”
心理卫生学院资深职能治疗师Mellishia Kaur Hoondal认为:长期住院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已经长时间失去自由。她说:“住在医院,就没有机会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制造机会,让长期住院者行使自主权,例如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储物柜,学习洗衣,以及自己分配餐食。”
与长期住院者共处一个早上
缓速康复疗程到底怎么进行?为了进一步了解缓速康复疗程及长期住院者的生活,记者在医院特别安排下走进长期病房,和一些长期住院者一起相处一个上午。
学习服药了解副作用
上午10时,上药物课。长期病房内有个冷气房,装潢设计就像一般办公室可供大约十个人开会的小会议室。七名长期住院者(三女、四男)围坐在长形桌旁,面向着挂在墙上的荧屏,荧屏上放映着助理护士长胡小美准备的药物课资料。

胡小美满脸笑意,逐一问候了大家,接着温习上一堂课的内容,再继续讲解药物作用。讲课时,胡小美语调像个大姐姐,长期住院者偶尔自己聊天,有时答非所问,她都用温柔但坚定的语气提醒大家用心听。接着,她把住院者分为两组,讨论药物的优缺点,并请教育程度较高的住院者把大家讨论的重点写在白板上。
药物课程有八节课,内容循序渐进,接着长期住院者会学习计算自己每天必须服用的药物颗粒,护士也会在下课后逐一和他们温习内容。
胡小美说:“长期住院者不一定明白为什么要吃药,上课后除了明白吃药的原因,也学习怎么处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这对他们日后独立生活非常有帮助。不过,因为长期患病和住院,有些住院者的认知能力可能受影响,所以讲解时可能必须重复,教材要图文并茂,最重要是有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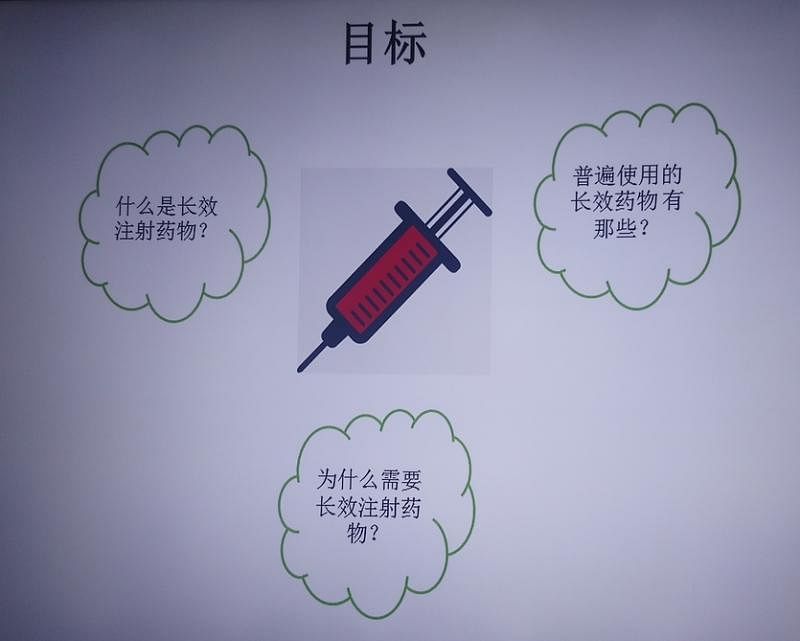
做手工进行心理教育
接着是手工时间。再过几周就是开斋节,长期住院者用彩纸制作开斋节红包封套,准备义卖。每包售价一元,订购者包括医院员工及基层组织。售卖所得会投入板桥医院慈善基金,并用于资助长期住院者的节目和活动。
一叠叠印有开斋节图案的彩纸摆在桌上,长期住院者手握剪刀,小心翼翼沿着粗线裁剪,剪好的彩纸交给其他住院者折成红包封套。其中一名妇女看见记者站在桌旁,主动递上剪刀和两叠彩纸,点头示意要我坐下来一起剪。

胡小美说:“手工和园艺等活动对住院者的康复有一定帮助,这些活动也是心理教育的良机。护士和大家一边做手工或园艺,一边分享疾病知识,住院者的接受度较高。”
心理教育(Psychoeducation)是一种以医学实证为根据的疗法,意即与患者和家人分享疾病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和面对疾病。心理教育大多用于较重大的疾病,例如失智症、精神分裂症和癌症等。
胡小美说:“医疗人员和住院者之间一定要培养信任和良好关系,这种‘治疗关系’(therapeutic nurse relationship)在精神科病房尤其重要。我们和住院者谈话时,就像和朋友或同事聊天一样,偶尔开开玩笑,最重要是不能高高在上。住院者可以从我们的言行感受到我们的态度,让住院者感觉到我们的信任,他们的感觉一定比较好。”
以手工活动为例,或许有人会问:让长期住院者使用剪刀,会不会太危险?他们能好好使用剪刀吗?
其实,长期住院者定时服药,护士也会小心观察,所以不必太过担心。
胡小美说:“如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不可能学会。就像工作机会,如果不让他们尝试,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工作表现如何。有些长期住院者或许行动比较慢,或是讲话声量较大,所以会吸引异样目光。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只要提供适当培训,还有多些耐心就行了。”
每天见面、相处,耐心和沟通不可或缺。对于长期住院者来说,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或许多年没见,或许一周只见一次,医疗人员却是天天都在关心、照护自己,他们自然也会关心医疗人员。
例如最近胡小美因为胆结石动了小手术必须请假,长期住院者知道后都非常关心。她说:“病假后回来上班,住院者看到我提东西就上前阻止。他们说我刚动完手术,不能提重物。”
叙述这件事时,胡小美笑得好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就这么简单。
出院前最迫切的需求:工作与住房
2015年至今,已有26人接受缓速康复疗程后,成功找到工作或出院,有些人回到自己入院前就买的组屋,有些则住进社区康复中心。出院后,他们继续定期复诊,医院也和他们保持联络。
苏心荃医生说:“大部分长期住院者的状况良好,而且进步非常快。有些虽然病情复发必须再次入院,但很快又能出院。”
他认为:长期住院者在医院可能住了十多年,出院后重新入院一两次其实在预料之内,何况医院外的生活可能截然不同。
他说:“长期住院者出院后少了说话对象,或许也会感觉迷惘。过去住在医院,身边总有护士和其他住院者,出院后必定需要时间适应。”
生活方式骤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压力有可能导致病情复发,所以医疗小组除了定期做家访,还会主动拨电保持联络。此外,小组会偕同长期住院者熟悉新住处环境,并联系附近社区组织,确保长期住院者出院后不会不知所措。
最重要的是,要让前长期住院者知道,万一碰上困难,总是可以联络医院求助。例如一名前长期住院者最近就告诉医疗小组,和他同住的另一名房客开始和朋友在家里大量喝酒,他认为这样的居住环境有一定风险,所以联络医院帮他另找房屋。也有前长期住院者在出院后,面对家人伸手要钱的困扰,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向医疗小组求助。

出院未必与家人同住
苏心荃医生说:“要帮助长期住院者出院,就必须帮他们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要赚钱养活自己,也要懂得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我们会接洽建屋局帮他们租房子,他们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也会安排他们回家试住几天,确保他们适应了才安排出院。”
长期住院者出院后,会不会和家人同住?不一定。因为家人未必愿意接受他们。
苏心荃医生说:“大部分长期住院者都是因为家人无法或不愿让他们回家,所以才会住在医院。长久下来,他们也习惯了没有家人在身边的生活。如果我们期待他们要回去原来住的地方,或和家人相聚才让他们出院,或许就会停滞不前。我们必须改变做事情的方式,无论如何要找到一个起点,才能开始看到改变。”
一步一脚印,开始走,才能朝目标前进,或许途中还会有意外收获。
例如最早开始在医院膳食部工作的长期住院者之一,在医院住了20多年,孩子已经40多岁了,多年来没有联络。医院除了帮他把组屋单位打扫干净,买了家具和衣服,也带他熟悉邻里环境,还联络了他的孩子。
苏心荃医生说:“孩子看到他的改变都非常惊讶,他们虽然没有同住,现在却开始保持联络。最让我们感动的是,长期住院者都非常努力,他们都非常珍惜出院的机会。”
长期住院者懂得珍惜,更懂得感恩。出院后,长期住院者都没有忘记照料自己的医疗人员和义工。
心理卫生学院义工计划经理蔡秀凤说:“一名年近60岁的长期住院者在医院住了至少八年后成功出院,现在还有全职工作。他经常回来医院探访大家,还用自己赚到的钱买咖喱卜请大家吃,这里就像是他的家。”
第一份薪水是前进的动力
目前,长期住院者的工作机会一般都在医院内,例如在医院膳食部操作洗餐具的机器及分配餐盘,或在护士教育中心清洗教学用的人体模型。此外,在心理卫生学院经营小吃店的社会企业BizLink,以及承包医院清洁工作的ISS也开始雇用长期住院者。
苏心荃医生说:“我们的住院者可以做的工作好多,他们也好努力。膳食部起初有点迟疑,后来却告诉我们,他们愿意聘请更多长期住院者。因为长期住院者勤奋,不像一些其他员工,可能只做两三周就走人。”
长期住院者的薪金按工作性质而异,一般时薪$1.50至$5。有些人在十多甚至20年前入院就没再工作,现在重新投身职场,大家都很珍惜工作机会。
苏心荃医生说:“隔了这么久没工作,手里拿到第一份薪水时,宛如拥有前进的动力,康复步伐也越来越快。但我们不想他们承受太大压力,所以开始时可能每天只做两三个小时,接着再慢慢加长工作时间。有了工作,有了目标,心理教育和病症管理才更有意义。”
工作可以赋予生活更多意义,也可以改变一个人。住院超过15年的黄伟雄(45岁)两年前开始在医院工作,首先是清洁事务,接着是膳食部,照护他的医疗人员都发现他越来越开朗,也越来越健谈。护士吴艾思原本担心黄伟雄第一次受访会紧张,或说得不多,没想到他侃侃而谈。

黄伟雄说:“我现在每个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都要工作,我负责洗杯的机器,工作不会辛苦,还可以交到朋友,很开心。”
吴艾思悄悄透露:黄伟雄现在时薪$5,医疗团队教他储蓄和理财,他最近用存到的钱包了红包给母亲,让母亲非常欣慰。问起这件事,黄伟雄似乎不以为意。他说:“妈妈最近脚受伤,给她钱看医生。”
吴艾思这么形容黄伟雄:“他是个快乐的人,没有很多目标,但我们认为他很有潜质,所以安排他工作。”
想不想有更多工作?黄伟雄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听起来好像不太在意工作,但随他一起到工作场所去拍照,他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的工作内容和环境,笑容和阳光一样灿烂。
出院可有时间表?
好奇医疗小组是否为长期住院者定下任何时间表,或期待能让多少名长期住院者出院。
吴艾思说:“缓速康复疗程是为期两年的疗程,这段时间内,长期住院者的康复状况不一定一直进步,或许偶尔也会倒退。所以说‘两年’其实只是指导原则,最重要是让长期住院者用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前进。”
换言之,“缓速”不是慢,而是根据住院者个别情况调整疗程,让他们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职能治疗师Mellishia Kaur Hoondal说:“病房之外的世界多变,长期住院者不一定能马上适应,他们或许也会发现自己其实更适合其他工作。他们必须试试,才能明白自己的强处和弱点。”
正如其他病症,康复不一定一帆风顺。再努力,也有挫败的时候。但Mellishia Kaur Hoondal强调:长期住院者都有‘survival instinct’(生存本能)。她说:“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帮助自己,尽量不会依赖其他人。但社会的支持还是非常重要,他们需要更多工作机会。”
苏心荃医生说:“我们希望有更多雇主聘请长期住院者,为他们提供更多类型的工作。长期住院者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工作和独立生活,他们应该得到这个机会。”
长期住院者的困境:渐失思考与行动力
访问心理卫生学院诸多医疗人员,大家不时提到一个英文词:institutionalized。
Institution的意思是机构、医院或制度;用institutionalized形容一个人,指的是他因为长时间在医院或收容机构的制度下生活,并遵守制度规则,因而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
苏心荃医生说:“患者成为长期住院者,部分原因是病情,但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也可说是我们(医院)的做法‘institutionalized’了他们,我们必须促进他们的康复。”
许多长期住院者患上精神分裂症,正向症状(positive symptoms,又称阳性症状)如幻觉和妄想较容易通过药物医治,较难医治,而且伤害可能更大的是负面症状(negative symptoms,又称阴性症状),如失去动力和活动力。
苏心荃医生说:“家人可能误以为患者很懒惰,也会因为照料他们而感觉到压力和倦怠,所以我们照顾患者之余,也必须支持他们的家人。”
理想情况是医院不再需要长期病房,患者都能在短时间内出院,与家人同住或融入社区。
苏心荃医生说:“医治精神疾病不难,挑战是如何融入社区。如果大家可以减少对精神疾病和患者的误解,那当然最好,但这需要时间。在改变大家的观念之前,患者更需要的是工作机会和住宿选择,社区组织的帮忙非常重要。”
杨冠盛(32岁,教师)八年前开始在心理卫生学院当义工,除了每周到医院陪伴长期住院者,也定期带他们出游。根据他的观察,公众一般不会公开歧视长期住院者,但有些人还是会作出不友善的举动。
他说:“有时候会听到公众说‘他们不应该来这里’,我每次听到都会当面纠正他们。看到电视剧以负面而且不真实的方式刻画精神病患,我也会投函指正。这个社会属于每一个人,公开取笑他们太低级了。”

杨冠盛把长期住院者称为自己“特别的朋友”,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纠正公众对于精神病的误解。
他说:“有时搭德士到心理卫生学院,司机会问住院者是否有暴力倾向。我会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住院者其实非常温和,也非常懂得感恩,每次看到我们都非常开心。大家只要有机会和他们相处,就会明白。”
替年长住院者办追悼会
长期住院者之中,大部分属于高龄组及临终和缓医疗组。随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传统做法是让他们转到一般综合医院,现在则是继续让他们留在心理卫生学院,并在这里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苏心荃医生说:“年长的长期住院者其实宁可在这里辞世,因为这是他们熟悉的环境,身边还有他们熟悉的医疗人员和其他住院者。如果转到一般综合医院,身边可能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临终护理非常重要,我们会尽量帮助他们实现最后的愿望。”
三年前,心理卫生学院开始每年为所有在医院辞世的年长住院者举行追悼会,让亲属连同医疗人员及义工一起道别和追念死者。去年,医院就为25名在医院去世的长期住院者举行了追悼会。
对于和家人失去联络的长期住院者来说,医院就是他们的“家”,医疗人员和义工就是最亲近的家人。

采访侧记
重拾记者工作之前,在心理卫生学院的初期精神错乱症治疗科计划(Early Psychosis Intervention Programme,简称EPIP)担任公共教育职务,有机会为患者策划并举行活动,如健康饮食课、运动课及远足。
当时接触的许多患者,和医院长期住院者一样患有精神分裂症,不同的是他们大部分都在病发初期求医,很多也有家人、朋友和师长的支持和鼓励,所以治疗功效佳,住院时间短,自然更容易回到原本的岗位,继续求学和工作。
医院的长期住院者如果更早得到诊治,如果也有更多人在旁支持,他们现在很可能就不用长期住院。
但过去无法改变,他们现在正为更好的生活积极努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在社区生活、工作,长期住院者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争取到原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机会。
一个人愿意为了目标而努力,就值得我们尊重,也理应得到更多机会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