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系列①
文接上期:风中的答案——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的百年观省
四、蜕变的标记
1、由传统开始
新马两地华人都是早期中国移民与后裔,本地华文文学的书写传统(起源),自然源自早期南来文人古典的文言文书写。
有人将此书写渊源上溯至15世纪,但至少在19世纪中后期左秉隆、黄遵宪等人领导的本地汉诗(文言旧体诗)创作已甚活跃,如邱菽园所云“近四五年中,余所识能诗之士,流寓星洲中,先后凡数十辈,固南洋荒服历来未有之盛也。”(邱菽园:《挥尘拾遗》,1901年)
新马华文学的传统汉诗创作,由19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如潘受等人的诗作。虽然文言文传统并未构成20世纪以来新马华文学的主流,但作为新马华文学的一环,尤其在起源时期的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这些19世纪的本地“旧文学”作品里,已经开始出现不少本土(“南洋”或“星洲”等)题材与叙述的创作。
文言文传统与本土题材的存在,显示中国元素与本土元素,早在新马华文学诞生阶段就已经出现与存在了。
2、新文学的转型
“马华新文学,简括说来,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以马来亚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1974年)
方修的上述论述,明确表示新马华文学从旧文学转向新文学的转捩点,就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
五四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是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与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与新思想,并形成普遍的文学创作思潮与标准。
1919年5月,五四运动在北平爆发,1919年10月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就开始有以白话文写作的文章出现,并被认为是新马华“新文学”的肇端。时间如此相近,显示影响的迅速,说明两者关系的密切性。

本地(及南洋地区)白话新文学的兴起并成为文学主流,无疑主要是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两地白话文新文学出现的背景与情境、内容与发展形势,却有许多差异,亦并未全盘承续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观与革命性。
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旗帜鲜明地号召文学改良甚至革命,全盘否定“旧文学”,文言与白话两阵营对立的矛盾,既尖锐又激烈。但在本地,由文言到白话写作的革新,却是一种低调的“渐变”过程,并未出现大动干戈、党同伐异的对阵场面。即使作为本地及南洋华文新文学最主要标志的报章副刊《新国民杂志》,也同时刊登文白两类作品(虽以白话作品居多)。
此外,新文学运动强调的反封建思想解放,在五四后的中国文坛促成新女性文学迅速崛起;在20世纪中期以前,新马华文学的女性写作基本乏善可陈。
如杨松年所说:“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新文学提倡确曾引起(本地)一些知识分子的反省,然而,在开始的阶段,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虽然支持白话,但采用温和的手法逐步推行。”(杨松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华文文坛》,1990年)
五四新文学对本地最大的影响,主要是白话文与部分新思想,从而造成本地文学的重大转型,奠定新马华“新文学”的基础与发展方向;但这种影响形式却是“温和的”“谨慎的”,可说是一种选择性的逐渐吸收,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完成转型的过程(如有学者就把本地文学早期的“白话文化”分成两个阶段/时期)。
这种选择性吸收,自然与本地社会环境有关,故五四白话文与本地新文学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元素的单向影响,更具有本地元素的有机反应,应该说是两地文化互动的结果。
3、本土意识的成型
本土意识在新马华文学的出现,经历过两个阶段。
首先是“南洋色彩”的提出:1927年《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荒岛》编者张金燕首先提出,应在南洋作品中树立南洋的色彩。
其次是“本土意识”的提出:1934年作家废名(丘士珍)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城》,提出马来亚“地方作家”的问题,并直接提出“马来亚地方文艺”的名词,第一次以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作为号召。
南洋色彩不仅属于外在景物层次,更往往带有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类似旧文学时期的南洋(异域)描写;地方作家与文艺的定位,就属于立足本土的写作意识层次了。
故方修即明确指出1931至1936年马华文学思潮的特点,就是“马来亚本位思想”的形成,这个时期“马华文艺思想界开始有了一个明确地理概念。”(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1986年)
其实“本土/本位”的内涵,远超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更具有归属感的“在地”概念。 这也导致二战后,新加坡一些写作者在1947年初提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问题,并爆发“马华文学”与“侨民文艺”的大论争。
这场有关本地文学主导性质的激烈论战,也是对本地文学身份与定位的大规模正面竞争。论争的结果是“马华文学”和“马华作家”(当时均包括新加坡)的直接形成。
基于社会与时代因素,当时马华文学的确立,正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4、两大主义的文学场
自新马华的新文学诞生以来,方修强调,“现实主义的精神却始终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全部的创作历史……成了(马华)文学创作的主流。”(方修:《新马文学史论丛》,1986年)。
无论是否认同方修的文学史观,现实主义确实在新马华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或主要)的位置,直到5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出现以后才开始改变。

一般以1959年3月诗人兼《蕉风》编辑白垚在《学生周报》发表诗作《蔴河静立》为马华文学的第一首现代诗,也是现代主义出现在新马华文学场域的肇端。白垚紧接着于4月《蕉风》化名凌冷发表《新诗的再革命》一文,大胆明确提出,“中国新诗运动的历史,完结于马来亚华人的手里;而现代诗的基础,也从那里开始。”这篇宣言似的文章,象征本地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的出现。
随即新加坡即发生第一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观的论争。时间为1963年12月至1964年8月,前后将近一年,主要争论者为钟祺与林方两人,双方针对现代派究竟是“毒草”或“新文学进程的一部分”展开争论,彼此不乏情绪性言辞,大有五四时期中国文白之争的尖锐与激烈。
1981年新加坡又发生第二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双方因台湾诗人洛夫一首诗作,对“诗应该明朗还是晦涩”两种诗观,爆发激烈论战,时间由当年8月至10月,前后仅约三个月,却在报刊先后刊登61篇文章,有40多个笔名的作者参战(据参与者之一怀鹰统计),结果虽无结论,但也说明在本地文学场“诞生”仅20余年的现代主义,已俨然具有能够与发展逾50年的现实主义“分庭抗礼”,举足轻重的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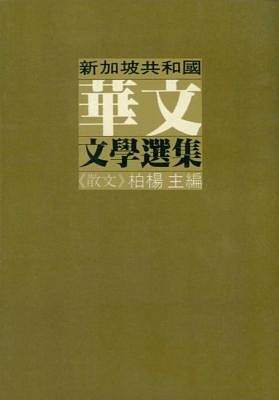
这也是上世纪本地最后一场文学论战,过后两种文学观在本地亦渐出现汇流迹象,双方创作内容渐趋注重本土化,文字上也渐避免晦涩难懂。
由于现代主义创作群的年龄相对较年轻,随着时间的发展与时代环境的变化,现代主义创作(或风格)在20世纪后期逐渐普遍,只是这时的本地华文文学创作世界,已开始进入“夕阳无限好”的另一个情境。
5、新世纪的多元
新世纪前后的新华文学,在延续本土化(或国族意识化)的同时,也出现许多新的现象/趋势。
一是新世代多元的创作观。以新世纪前后本地出版的文学杂志名称为例,如1990年的《风见鸡》(日语的鸡形风向仪)、1994年《后来》(后来就是未来)、90年代的《身土不二》(韩语形容人与土地不可分的关係)、2012年《Why Not 为什么不》(双语并称)等,一方面表现对语言运用的创意与敢于实验的精神,也体现其文学资源运用/引用的多元性(如日语、韩语与双语)。
新世代作者创作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现象,显示新华文学已开始进入世代交替和美学观念递嬗的新时期。
二是随当代西方学术理论观念而对自我定位的调整。新世纪前后的本地文学研究,开始转向以西方近代或当代理论为主,如后殖民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理论,往往带有强调与华文传统中心(中国)区隔或“离散”观念的去中心化意识(如史书美的华语语系论述,就有去中国化的鲜明意识)。
在如此观念下创作的新世代,形成的文学观与审美意识,如因身份“独立”产生的孤立与疏离,因强调在地多元语文而导致的语文混杂,因跨界观念导致主体分解等可能结果;特别是在碎片化的视觉时代,随华文水平不复旧观,又有非华文创作的“华人文学”新论和现象(如所谓“华马”论及“华新”的现象)等各种现实情境交集冲击下,未来新华文学的“新”走向与风貌,或许会进入一个充满混杂感的新阶段。
多元的混杂,可以是色彩斑斓,也可以是一片凌乱,或许处处生机,也可能不知何去何从。
《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曾策划一个报道系列,题为“后转调世代”(《联合早报》2015.05.06);“转调”是个音乐名词,指音乐进行中调的根音改变,造成情绪与节奏的改变。这个新词,形容贴切、寓意深刻、含义深沉,足堪玩味,尤可深思。
五、风中的答案
由于早期中国移民文化的血缘与时代背景,及南洋色彩与本土意识等的出现和发展,使中国元素与本土元素的互动关系,仿佛构成本地华文文学发展史的两大元素。
其实由新文学时代开始,西方元素始终也是新马华文学的一大构成部分。
如被方修认为是新马华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最早原由清末梁启超从日本引入译自西方的“写实主义”(最初译称),再经由中国南传,就是属于西方元素。主要出现于新华文学阶段的现代主义,更完全是源自西方文艺理论与观念的西方元素。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来新马华文学到新华文学的成长轨迹,主要就是中国、本土、西方三大元素,在不同时代里交集互动,相互消长的演进历程。这三大元素的历史关系与走向,共同形塑百年来新马两地华文文学生命发展的立体形象,构成一路蜕变的标记,贯串其间“始终像一根红线”(借用方修语)的主要因素,就是时代性(情境条件)。
时代是流动的,文学就在流动中变动。但流动不应是流失,而应该是流通,有来有去的流通,才能生生不息。
如同一条大河,纵然经历千山万水,雨雪风霜,百转千回,只有始终维持自己的源头活水,才能继续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水域,面对天地,无愧天地。
华文文学的生命根源,就是“华文”二字,无论书写形式或水平如何随时代环境而变化,只要依然是华文书写的创作,就是华文文学。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歌者鲍勃·迪伦讨厌任何标签,却获奖无数,被称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不同于当代各种创新的音乐类型,他的一生,始终延续着民歌的脉络和精神,始终守着传统的根基。
有来有去的路,才是一条可以行走的路;有根基的创新,才是有命脉的创新;有文化的自觉,才有真正自己的文化位置。
无论走过多少条路,只要一个人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能被称为男人。
答案,始终就在风中,始终一路相随,就看是否有人觉察,并且愿意用心守护,认真传承,努力发扬。
(杜南发是本地作家、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