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疾病的命名,原本是件略显学术、少人关注的事。然而,在这场“2019年冠状病毒病”疫情中,名称的重要性却突然变得不可小觑,颇有文章。简单易懂的“武汉肺炎”“中国肺炎”带有污名化歧视偏见,“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和“2019-nCoV”则都被中西方诟病为又臭又长的缠脚布。这个先后引发“口罩之乱”和“超市之乱”的传染病,也一直深陷命名之乱。
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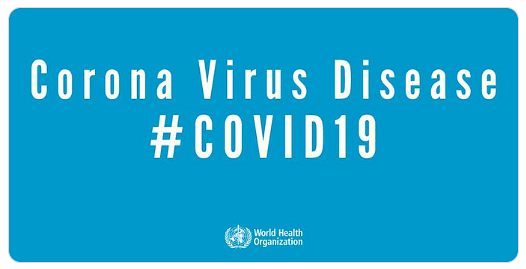
从“武汉肺炎”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两个月,“它”终于有了正式名称。
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11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命名为“COVID-19”,中文可翻译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该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中文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
“COVID-19”代表的英文缩写分别是:“COVI”冠状病毒(coronavirus), “D”疾病(disease),“19”指疾病于2019年暴发。
如此复杂拗口,难怪有病毒专家提出其他建议。
病毒学界建议将病毒命名为“HARS-CoV”
新加坡的杜克—国大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重点研究项目主任王林发教授、助理教授丹妮尔·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新保集团杜克-国大全球健康研究所署长麦克·默森教授(Michael H. Merson)在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合著的评论中建议,将病毒取名为“HARS-CoV”(Han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Han”取自武汉的简称“汉”。
于2月11日在《柳叶刀》网络版发表的这篇评论中提到,全世界病毒学家都在探讨“2019-nCoV”的替代名称,因为新病毒的命名长期看来不仅对病毒学家至关重要,一个好名字也有助于与大众沟通。
专家认为,将病毒命名为HARS-CoV,可“延续以征状命名的传统,如沙斯和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避免使用城市名称造成敏感”。
论命名的重要

世卫在2015年推出传染病命名准则,建议疾病名称应包括疾病症状、受影响人群、疾病严重性或者季节性特征、或已知引起病原体。名称应避免地理方位、人名、动物或食物种群、涉及到文化、人口、工业或职业和可煽动过度恐慌的术语(如不明、致命、流行)。
世卫指出,“COVID-19”这一命名“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易于发音,并且与该疾病有关”。
世卫组织说:“拥有一个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耻辱的名称。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格式,可用于将来发生的任何冠状病毒疫情。”
话虽如此……
全球各地过去暴发的传染病,命名方式五花八门,多以疫区地名而为人所知,如早期的西班牙流感、德国麻疹、日本脑炎,近期的伊波拉病毒、兹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也都是以病毒发源地命名。
不难发现这类地名命名方式,容易引发外界针对某一国家或社群。这可从最近一些欧美国家、甚至中国境内因最初的“武汉肺炎”、“中国肺炎”而出现的排斥武汉人、排斥湖北人乃至排华事件可见一斑。
另一命名大宗是动物病原体如禽流感、猪流感、猴痘症,后续也导致与动物相关的群体或职业遭歧视。
然而,即便与地名毫无关联的2003年沙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疫情,也因为英文缩写“SARS”与当年暴发大量病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英文缩写“SAR”过于雷同,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到香港,让香港二度中箭。
其他命名方式
一些传染病以发现疾病的学者命名,例如俗称麻风病的“汉生病”(Hanson's Disease)是为了纪念挪威科学家汉生(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他在1874年发现麻风是由某种杆状病菌侵入肌肤引起。
沙门氏菌是由美国病理学家沙门(Daniel Elmer Salmon)最早发现。
帕金森病因1817年英国医生詹姆斯·帕金森(James Parkinson)首先发表一篇记录此病的医学论文而得名。
也有一些病症是以职业命名。比如退伍军人症或军团病是源于1976年,一班美国退伍军人在费城出现肺炎及呼吸道感染现象。尽管过后发现是水源污染引起,但仍以退伍军人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