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疫情仍然胶着与焦灼的日子里,重读《纪弦诗拔萃》里的每一首诗作,心中有无比的欢愉和逸乐。
炎炎夏日里,在《富士山麓》里看着飘渺的山岚和云朵,听着迷人悦耳的乐音,像难得一阵清风徐来的同时,还有一股悠悠的清泉就在耳畔,涓涓不息的流淌和吟咏。
前两天在走廊上给花木浇水时,发觉有一盆种了至少十年以上的金边虎皮兰(也叫千岁兰),竟然冒出几串淡绿色的花蕾,有几朵已悄然开出白色的小花,十分讨人喜欢。
回到屋里,整理干瘪褪色的老书橱,意外地从角落翻出两件令人惬意的“旧相识”,一是已故台湾诗人纪弦2002年出版的《纪弦诗拔萃》,另一是1990年代在首都戏院附近的旧唱片和光碟连锁店买的激光录像光碟《富士山麓》。光碟的映像是胜又幸宣拍摄,音乐是都留教博创作的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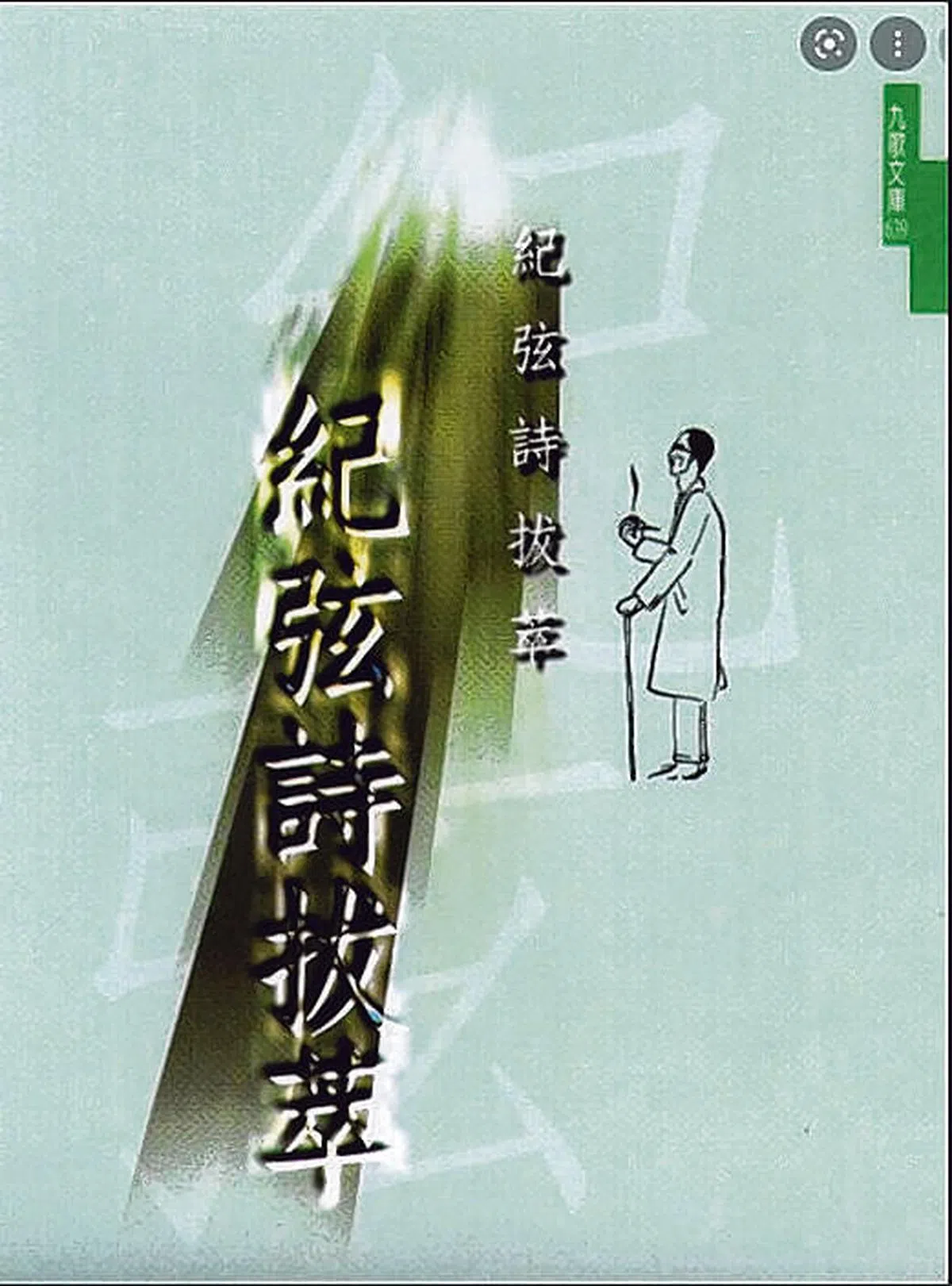
回首与这两件“旧相识”的“交谊”,已经是20年以前的事。霎时间,对元好问在《寄答飞卿》里的那一番感受,似乎有更真切的心领神会。诗云:“一首新诗一线书,喜于沧海得遗珠。古来献玉犹难售,此日闻韶本不图。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终放月轮孤。并州命驾才千里,嵇吕风流未可无。”嗯,古诗词也好,现代诗也罢,抑或是美景和乐音,在多变难料的日子里,总能给人多添一些美好的记忆和回味。正因此,医疗委员会副主席李清副教授才在他“医生执笔”的专栏里,建议“我们在应对未来新常态的当儿,也应该保持原有的基本生活节奏和习惯,在没有特殊工作要处理时,可钻研一两项比较需要专注、集中记忆力的事情,如看书、听音乐、学习新技能等。”
回想起纪弦老诗人,他1913年4月生于中国河北清苑,儿时跟着父亲辗转多地,后定居扬州。抗战胜利后,他前往台湾,执教于台北成功中学。1950年代他独资创办《现代诗》季刊,开创新诗的再革命运动,可说是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更有“诗坛祭酒”的雅称。1976年底,他寓居美国后,仍然写作不辍。2013年7月杪,101岁的老诗人驾鹤西归时,已经见证一个世纪的人世沧桑。
在《纪弦诗拔萃》的序文中,他说出版这部选集的原因,是想把20世纪自己的诗路历程作一次总结,今后他不打算编印全集,他认为“凡是全集,坏诗一定太多,那就是既浪费了纸张而又对不起读者的”。哦,果真是个性情中人,不仅展现诗人前瞻性的环保意识,他对读者认真负责任的态度,更是令人崇仰和钦敬。
从2002年的1月到4月,纪弦花了一百多天的时间,从一千多首诗作里,只选出95首诗作,还不到百分之十而编成《拔萃》,每一首诗还标示写于何年何地,足见他对于好诗的执着与较真,真正做到宁菁毋滥。
在当下疫情仍然胶着与焦灼的日子里,重读《拔萃》里的每一首诗作,心中有无比的欢愉和逸乐,尤其是辑一“大陆时期作品”的第一首,颇令人“惊艳“。那是他写于1933年扬州的《八行小唱》。诗人年轻时的不羁率真、目空一切,可谓袒露无余。当然,《八行小唱》也体现他并不排斥自由押韵的诗歌特色。一起来回味、读读。
从前我真傻
没得玩耍
在暗夜里
期待着火把
如今我明白
不再期待
说一声干
划几根火柴
读罢《小唱》,想起当下诡谲多变的冠病病毒,忆起自己年轻时曾读过元好问的散曲名作《骤雨打新荷》(双调),顿时思绪翻飞起伏,往事萦绕心头。“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当然,若真要邀宾对酌,切记如今只能二人,千万莫大意,招惹麻烦!
元好问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摸鱼儿》,破题就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嗯,其序文所言若属实,就更令人感触良深了。序文自云他16岁时,赴太原赶考应试。路上遇见一个捕雁的人,那捕雁人说今日网到一只大雁,就把它杀了。但那只漏网的大雁悲鸣不已,久久不肯离去,最后“竟自投于地而死”。元好问万分怆然悲悯,便把两只大雁买下,葬于汾水河边,垒石作为标志,称作“雁丘”。当时同行者都赋诗悼念,他也曾写一篇《雁丘辞》,但由于旧作不能歌唱,如今改写成能歌的《摸鱼儿》一词。如此看来,元好问当然也是个性情中人,因为被大雁的殉情深深触动,哀思难当而有此作。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谛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几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说回诗人纪弦,他那首写于1952年台北的诗作,情感真挚,用字突出,引人注目,题为《你的名字》,诗的最后一句,共用了六个“轻”字,读来浮想联翩,让人意犹未竟。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
当这植物长成了参天的古木时,
啊啊,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来。大起来了,你的名字。
亮起来了,你的名字。于是,轻轻轻轻轻轻地唤你的名字。
评论者多主张,这首诗应该是诗人思念他爱人而作,不过,也有人认为诗中的“你”,仅是个抽象的悬念,诗作或是委婉地表达对家乡或祖国的思念,哦,这也可说是各人读诗各有体会和收成的意趣和异趣。
对于现代诗的期许与坚持,纪弦怀抱的决绝豪气与狂飙特立,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他在次年(1953)写的《诗的复活》里,就睥睨一切、昂扬自诩宣告:“李白死了,月亮也死了,所以我们来了”,其傲岸不驯之豪气,颇有当年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了”的神采。
被工厂以及火车、轮船的煤烟熏黑了的月亮不是属于李白的;
而在我的小型望远镜里:
上弦、下弦,
时盈、时亏,
或是被地球的庞大的阴影偶然而短暂地掩蔽了的月亮也不是属于李白的。
李白死了,月亮也死了,所以我们来了。
我们鸣着工厂的汽笛,庄严地、肯定地,如此有信仰地,宣告诗的复活;
并且鸣着火车的尖锐的、歇斯底里的、没遮拦的汽笛,宣告诗的复活;
鸣着轮船的悠悠然的汽笛,如大提琴上徐徐擦过之一弓,宣告诗的复活。
诗人写于1964年的《狼的独步》,亦是台湾现代派诗坛的扛鼎之作。诗中共用了六个“飒”字,最后一句的“这就是一种过瘾”,如今读来,还是让人感到很“过瘾”!虽然,我们都不希望天地果真得了疟疾,更甭说是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了。
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嗥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
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
这就是一种过瘾。
五年之后,还不算老的诗人,似有难以排遣的乡愁。在1969年写的那首《云和月》里,一缕难掩的思乡情怀,似乎让他暂时搁置前卫无惧的现代派理论与范式,在那工整的短短八行诗句中,真情流露跃然纸上。读这首诗时,不禁想起台湾当下的疫情还在升温,而两岸依旧处于“势不两立”的态势,令人唏嘘不已。
云横秦岭,云也横大屯山。
倘若我就是云,那多好!
云啊,你可知道?在这里,
我朝暮西望,不见长安。
月吻淡水,月也吻扬子江。
倘若我就是月,那多好!
月啊,你可知道?在这里,
我日夜西看,不见家乡。
1996年,83岁的老诗人在美西旧金山半岛的圣马特奥,还有一首题为《乡愁五节》的诗作。诗的最后一节,他已经在想象自己下个世纪去到火星时,或许对地球会有一种浅蓝色的怀乡病: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
一旦我乘坐超光速太空船
去观光橙红色的火星时,
那就会产生一种对于浅蓝色的
地球之怀乡病了吧?
只不过,诗人又怎会料到,智人才刚踏入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就陷入一场必须与冠病病毒,一再折腾拉锯的“抗战”呢!
如此说来,诗人86岁时诗人写的那首小诗《月光曲》,似乎更令我舒心会意。对于沧桑人世,此时的他已然淡漠自处,犹如暗室里的一盏明灯,既洞察千毫,又笃定自如。诗,已经无须用太多的言语和文字,仅仅三行,16个字,就“波澜不惊”地抒怀写真了。嗯,真令人喜欢和欢喜!
升起于键盘上的
月亮,做了暗室里的
灯。
是的,在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一盏灯,有时通透明亮,有时忽明忽暗,但只要还是散发着亮光,就可以引领我们继续走在这不平坦的人生之路。比如,日本的映像作家胜又幸宣,他出生于好几个世代都与富士山息息相关的家族。1971年,既是气象学者和小说家的新田次郎(Jiro Nitta)在《文艺春秋》发表了小说《芙蓉の人-富士山顶の妻》,故事中出现的御殿场(Gotemba)第一家“富士本屋旅馆”,其实,就是胜又幸宣父亲的老家。2014年这部小说被改编之后,拍成NHK的电视连续剧,颇引人追看。

说回胜又幸宣,他的家族除了经营旅馆业务外,胜又的祖父忠义氏,抱着“我想向世界传达富士山的美丽”的信念,还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祖父花了不少钱买一台可以拍摄360度全景的全景相机,尽情拍摄富士美景,至今胜又还珍藏着祖父在富士山顶宝永火山口和本栖湖等处所拍摄的珍贵影像。胜又母亲的娘家,其实和富士山也有密不可分的因缘,母亲家的曾祖父就曾是一个强大的富士山登山者。因此,胜又可说是从小就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富士”的基因。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心里就老想着“将来毕业后,我想继续往音乐或摄影这条路上走去。” 碰巧后来他的一个朋友组成一支爵士乐队,高中时他因为参加铜管乐队,就被友人邀请去吹小号,并且有了“如果我有钱,一定会被音乐所吸引。”可最终他还是选择走上拍摄映像之路。
胜又在东京的一家照相馆,接受一年的摄影培训,后来又在照相机维修店,接受一年的维修训练。返回家乡后,他在经营相机维修店的同时,也全情投入了富士山的摄影志业,但其主题是以富士山的生物为主,他说:“我不想为游客拍照!”
根据“富士山俱乐部”29号通信里他所写的那篇《将神山怀抱的各种活动传递给下一代》,从1991年到1997年间,如果天气好的话,他都会给富士山摄像拍照。从日出前到日落,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最好的角度。他在山上不停地游走探寻,耐心地构思取景,有时也睡在车里,等待最美好的时刻到来。他拍摄的长达25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不仅传达每个季节富士山的真实面目,也传达山峰时而玩转云朵,时而顶着太阳的绚烂英姿。他深有感触地说:“从远处看富士山很美。但是,我总是试图捕捉富士山的本质。当我靠近富士山时,各种各样的生物,就住在我的怀里。我想把如此丰盈美好的大自然活动,一一记录下来,并将它传递给下一代。”
在富士山俱乐部,胜又幸宣是富士山南侧森林调查的负责人。在每月两次的调查活动之前,他们会通过航拍照片等收集详细的当地数据,调查时依靠GPS穿越过林间小路,探访未知的森林,寻找苍天的巨树。这当然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因为“准备应对遇险和背靠背调查,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他也坦承:“一旦加入富士山俱乐部,我就没有时间去富士山。”但保护好每一个森林,看来已经成为他最挂怀心事。
所幸,他已经拍过千姿百态的富士山神韵,我收藏的那张《富士山麓》激光录像光碟里就涵盖八种不同的景色,包括“黎明”“春”“夏”“秋”“冬”“草原与森林”“水之塚”和“现象”。最令人欣喜的是,每一个章节的景色都配上都留教博创作的优美乐曲。
在炎炎夏日里,看着飘渺的山岚和云朵,听着迷人悦耳的乐音,就像难得一阵清风徐来的同时,还有一股悠悠的清泉就在耳畔,涓涓不息的流淌和吟咏。哦,或许你对都留教博的名字并不熟悉,但若有兴趣,你可以在网络里轻易找到他那首至今让人心醉的名曲《最后的嘉年华》(Last Carni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