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记者张若谷曾与鲁迅打笔仗。1933年他开始旅欧西行,历时两年,并写下“海行五万里,陆行二万里”的旅行笔记《游欧猎奇印象》,书中关于新加坡的文章有七篇。在张若谷笔下,当年的新加坡是“欧亚航路的咽喉、东方人类的熔炉”。
在航海运输时代,新加坡是许多中国人前往欧洲求学或旅游途中的必经之地。曾经为鲁迅所不屑被讽刺是“礼拜五派”文人,并拟议在出版的《五讲三嘘集》中作为“一嘘”之对象的张若谷留下的著作多达十多本,其中的《游欧猎奇印象》在初版84年后还被拿来重新编排出版。
张若谷其人其事
张若谷,1905年出生于上海南汇,早年就读于徐汇中学,得到过中国著名教育家、天主教徒马相伯的亲炙。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应邀入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撰写《马相伯学习生活》等书籍。张若谷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又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深受法国文学思潮的影响。
1927年11月,《真善美》杂志于上海创刊,张若谷接受聘用担任主编。《真善美》杂志是一份原创文学刊物,选用的文章大多是轻松小品文,以及一些符合上层社会格调的小说及诗歌。
周作人的闲话体随笔就是通过这本刊物而得以广泛传播。此外,刊物还译介外国文学,但与当时的苏俄文学提倡“革命” “民主” “觉醒” “抗争”等潮流词语的风潮保持距离。
1928年12月17日,《南洋商报》第22版刊载一则署名“铭弊”的文章,题曰:“所谓冰冷的感情”。文章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最近也有张若谷之流,在反对北欧的文学底精神而赞美南欧了。”然而,《真善美》杂志以轻快优美的风格和明媚淡雅的趣味性,吸引了中上层社群读者,特别是上海女性读者的喜爱。张若谷十分推崇当时沪上正兴起的咖啡座,认为带来了“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他为此还推出一部取名为《咖啡座谈》的散文集。
为纪念《真善美》创刊一周年,杂志开辟“女作家号”,于1929年2月出版。这期专号刊登了二十多位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冰心等。每篇稿件在刊出的同时附上女作家的一帧玉照,这种看来略显轻浮的手法当时招致新文学作家的广泛批评,主编张若谷被人责备“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性”。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上海滩上大受女读者拥戴和青睐的作家。
享有高知名度的张若谷想乘胜追击,趁势创办《女作家》杂志,不过杂志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1930年3月20日,《南洋商报》第20版刊印“许由”撰著的《一九二八年之中国文坛(一)》一文直指,“至于张若谷的编女作家什志便是投机事业了,真善美的女作家专号确实轰动一时,到了张若谷以为这是一桩大生意——发财之道,继续编了女作家什志便连送人看都没人要了。”
1932年2月29日,《南洋商报》第6版刊登一则“沪二月九日讯”,大字标题是《沪上战区观察记》。新闻报道了记者那天前往“一·二八”中日对抗火线区采访的经历;与记者同行的三人中,其中“一位是音乐家张若谷君”。张若谷曾经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早在1925年,他就应《申报》编辑的邀约,“担任写关于音乐方面的文字”。
1932年,张若谷出任《大晚报》记者一职。年底,北新书局将他在《大晚报》上连载的小说《婆汉迷》结集出版。书名标题是波希米亚的中文音译,小说以巴黎为背景,却旨在讽刺当时的中国文学家和诗人,影射了鲁迅、郁达夫等人。对张若谷从来不屑的鲁迅,立刻予以还击。1933年初,鲁迅发表翻译自戈庚的“NoaNoa”。
“NoaNoa”是毛利语,意思是“野花香”。戈庚即是法国著名画家高更,这部著作是高更厌恶所谓的西方文明社会,在“泰息谛”与纯朴善良的野蛮人生活数年的纪录。针对张若谷新启用的笔名“罗无心”,鲁迅为“NoaNoa”的译者署名“罗怃”,并在小说的前言中挖苦调侃:“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
那一年3月3日,张若谷在《大晚报》,针对当时普遍使用的影射、暗喻等写作手法,发表《拥护》一文,声称“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却都应运产生出来了。”9日,他又在《大晚报》发表《恶癖》一文,“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对此,鲁迅开足火力,先后在《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署名发文反击。 4月4日,发表了《文人无文》;5月9日,再发表《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两篇文章皆收录于鲁迅的《伪自由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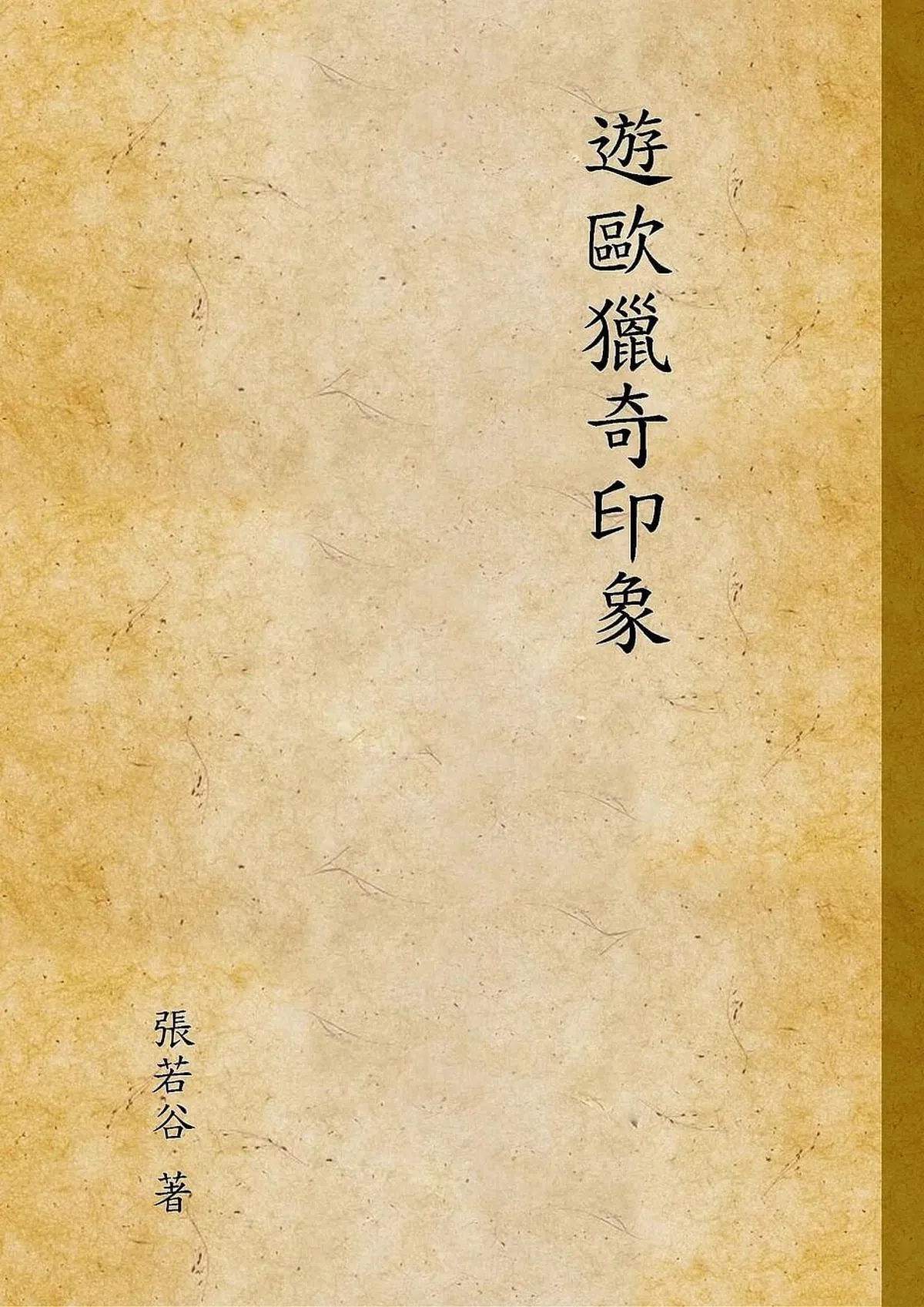
5月12日,张若谷乘坐“万德伯爵”特快邮轮,离别家乡上海,开始了他的旅欧西行,历时两年之久。《游欧猎奇印象》在1936年初版发行,书中收集了张若谷“海行五万里,陆行二万里”的旅行笔记。旅欧前刚与鲁迅在文字上过招的张若谷,似乎并没有让笔战干扰了出游的兴致,一路上他的文笔卓然,为当时中国人极少听闻的西陆风土人情跃然纸上。文章在数种报纸上发表后,一时风动四起,令张若谷本人声名大振。
2020年重新编排出版
纵览《游欧猎奇印象》一书目录,其中关于新加坡的文章共七篇,篇名分别是:《“狮岛”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侨》《在华侨欢迎会中》《“狮岛”的交通》《军事上的新加坡》《新加坡军港一瞥》《世界第九大商埠》。在文章中张若谷以记者自称,行文洒脱,善于调和都市市民读者的口味。在出游欧洲三周年之际,他又以极富吸引力的《游欧猎奇印象》为书名,将文章结集出版,颇受张氏读者群之青睐。202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将此书重新编排出版,可见其魅力之所在。
在张若谷笔下,当年的新加坡是“欧亚航路的咽喉、东方人类的熔炉”。张氏写道:“五月十八日离别上海后的第七天,天气晴朗,海波不兴。上午九时左右,‘万德伯爵’特快邮船,驶泊在新加坡的码头。”“炎阳把街道晒得像火坑一样,火伞高张,旅客们都戴上从香港新买来的白帽儿,或马尼拉草帽。大家怕热,都想以车代步。”“记者叨光,附随中华朝圣代表团,得参加新加坡华侨筹备的欢迎大会。会场在天主堂附设的华侨学校中,主席某中国教士,致欢迎词。他先用马来语,继用福建话翻译,记者一句都听不懂。后由代表团中杨汝荣主教用广东话答谢词,也不甚了了。”“我们参加的明明是华侨发起的欢迎会,可是因为语言不通,无异是赴一个外国语的演讲会。幸亏会场中张贴的各种欢迎标语,和欢迎词等,都是用中文写的。”
不乏猎奇笔触
张氏笔下的文字,对新加坡的交通状况语多赞赏,但字里行间也不乏猎奇的笔触,譬如:“男女并肩同乘人力车、马来铁路可直达暹罗。”“新加坡的街道,广阔而又整洁,道旁都有深沟低洼,为泻水及扫除垃圾的用。两旁植树,多高数丈的椰子树。交通代步的利器,有汽车、电车、马车、人力车、牛车,及火车。人力车高,而且大,作元宝形。分单人座双人座两种。双人座车身大如马车,可以二人并坐。在新加坡,男女并肩携手,合坐人力车,是极寻常事件。” “装载货物的,多用重笨异常的牛车,往往用牛两头并拖。但是牛性似乎颇机警,它们都善于避让汽车和电车。这几种不很谐和的车辆,混在一条街道上驶走的时候,却可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近代轻快的交通利器,直有取代旧式笨重牛车而驾上的趋势。同样地,20世纪的物质文明,早已征服了殖民地的原始文明。牛车和人力车式的文明早晚要变成为被淘汰的东西。”
在一篇《印度洋上》,张若谷告诉读者:“五月十八日傍晚,‘万德伯爵’号在新加坡解缆启程,向锡兰岛前进。”《南洋商报》在1935年1月25日和26日的“ 商余”版,分上下两次刊登张若谷的同名文章。但不同的是,那是作者写于西游欧洲回返上海的航程中:“十月二十九日,自英京苏格兰。十一月一日,在葛拉斯哥,搭招商局新轮海贞启碇。”经过多日海上航行,船“……到萨蓬Sadong,这是荷属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军港,在新加坡的西南。据海员们相告,该地是一个小村落,只有一条热闹的市街。居民为马来种人,亦有不少福建广东两省的华侨。土产以水果香料为大宗。间有出售貂鼠鹦鹉及稚虎者,可惜行囊羞涩,否则购买若干奇禽怪兽,分送上海诸亲友,亦可作新年礼物用也。”
吁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1935年,张若谷回到上海,出任《时报》记者。1936年,张氏出任南京《朝报》主编,后改任上海《神州报》记者。1936年2月5日,《南洋商报》第11版刊登“上海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全文,张若谷连同顾执中、庞学棠、谭丹辰、萨空了等一共61位新闻从业人员一齐署名,呼吁国民政府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反对压制对中日对抗真相作出揭露的新闻报道。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中美日报》创刊,张若谷在《中美日本》用中英双语发表大量抗日救亡的文章。1941年9月24日,张若谷在上海法租界,因抗日救国罪被日本宪兵汇同法国警务当局逮捕。在中外各大新闻媒体舆论的呼吁下,各界积极设法营救,最后日方不得不放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若谷赴南京,担任天主教《益世报》主编。1955年9月8日,张若谷因宗教原因被抄家,继被遣送中国东北劳改。后经法院复查,撤销原判,无罪释放。1967年,张若谷因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