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推手12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40年过去了,《南洋学生》不在了,《联合晚报》也消失了,但《南洋学生》通讯员与金声文艺学会的会员,今天已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文接上期)
在版位上,1981年4月推出《南洋学生》革新版,每日八小版,除了《青少年》取代《学府春秋》,也辟有《摘星少年》《童话屋》,一揽子让初院生与大学生、中学生与小学生投稿,全面的照顾到各年龄层学生投稿人。1982年5月,《南洋学生》以大开版形式出现,进一步朝独立学生报章转型,每天刊登“时评”,一如报章的社论,由资料室主任欧清池与我轮流执笔。
编辑室人手方面,最初有通讯员梁丽庭由实习生转正当编辑,及另一名副刊编辑陈佩儿协助;后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协议共同出版英文报《新加坡箴言报》(Singapore Monitor),内附中文版学生专刊《新一代》,两名编辑被抽调去新的报章。编辑顾问锺文苓与我讨论人手问题,我提议起用校对组的董农政当编辑,馆方也另外派一名实习生郭秀芬协助。郭秀芬擅长绘画,把《童话屋》版面设计得五彩缤纷。
董农政的空缺则由另一名通讯员张森林(伍木)补上,后来他也成为一名记者。梁丽庭与张森林相信是最早成为新闻工作者的两名通讯员。
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还有陈健良(米风)、林得楠(牧汉林)、陈韵红(圆醉之)、李凤婷、刘汶錝(仲仁康)、黄成财(乔克岑)、傅来兴(戴畏夫)等。除了他们继续与笔打交道,其他至今仍然活跃文坛的,还有蔡志礼(华之风)、梁文福、柯思仁、吴耀宗、傅艾笙、吴晓芬等。
活跃的通讯员还有周伟良(曾静、潇易水)、刘荣和(思逸)、江春才(独木桥)、张慧恩(柳依风)、郑丽珠(晓曦)、芦苇、汤石群、王明凤、陈惠然、李美玲、梅天祥(谷中青)、林夏芸、李蕙妘等等。
《南洋学生》通讯员不少也是金声文艺学会会员,两个组织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也许是个人喜爱诗的关系,两个组织聚集的多是爱诗的人。《南洋学生》常有诗作发表,还推出一连四期的青少年诗辑,耕耘者包括董农政、华诗音、文竹、牧汉林、依琳、东邪、钟怡、云谷涵等。华之风每期撰写评点录《说长道短话诗辑》,谈论雨庭、黄龙、雪鸥、乔克岑、董农政、夏龙、玉棠等的作品。
1980年代文风很盛,处于竞争状态的两家报馆,都不遗余力地搞活动,邀请名家开讲,通讯员有很多采访与观摩的机会,比如曾静采访三毛的《故乡在远方》,1981年9月8日以跨版刊登。伍木的余光中印象《一代诗人,千年火浴》,1982年6月16日刊于封面。柏杨到来时,就由《南洋学生》负责接待,他的座谈会侧记,亮星的《铁窗下的血泪耕耘》,刊在1981年2月21日。还有1981年,配合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成立举行的国际文学座谈会,请来白先勇等名家,米风采访的《那只南来的燕子》,就刊在1981年3月12日。
那时,现代派盛行,通讯员也难免受影响,笔下多有新奇而晦涩的句子,老一辈的同事难以接受。比如连载了十余篇的仲仁康的航海见闻录《铁船散记》,就被喊咔。
在《南洋学生》当通讯员还有不少特别任务,比如担任“南洋调查”的调查员,上街做田野采访;协助老报人彭松涛为出版《社团大观》资料收集。这些都是自愿的有偿工作。有通讯员还开玩笑地说,可以存“老婆本”了。
说起这回事,一群少男少女聚集在一起,总难免有伤春悲秋和感情上的问题,有恋爱的,有失恋的,还有其他的种种如会考的困扰,我还得充当情感治疗师,安慰那些泪流满腮的女孩和落寞失意的男生。当然,他们有开花结果的,也有无言的结局。
一首诗掀起一场现代诗论战
《南洋学生》还有两件事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
先是因洛夫的一首诗《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引起一场空前的现代诗论战。1981年9月3日,我发了通讯员戴畏夫的评论《欣赏现代诗的途径》,以“细胞论”回应叶霜在8月27日于《星洲少年》发表的诗评《晦涩难懂的诗》,果不其然,两人的诗观引爆了一场长达三个月的笔战,前后约61篇文章,40多名作者参战,参战者年龄在15岁至40多岁之间,不少是学生通讯员。以学生报而能引起一场名家与青少年写手的擂台大战,的确令人瞩目,后来连本尊洛夫也现身说法,可谓规模空前,影响深远。

当年多名学生通讯员——今日多在报界与文教界工作——大胆参与笔战,与名作家交锋,实属可贵;更难得的是,论战后,40年来诗坛无战事,而且出现汇流迹象,不能不说是一大收获。1980年代以降,现代与写实两派诗人的创作,内容上渐趋注重本土化,文字上也避免晦涩难懂。这是一个好现象,也可能是那场论争的意外收获。
我怎样为新谣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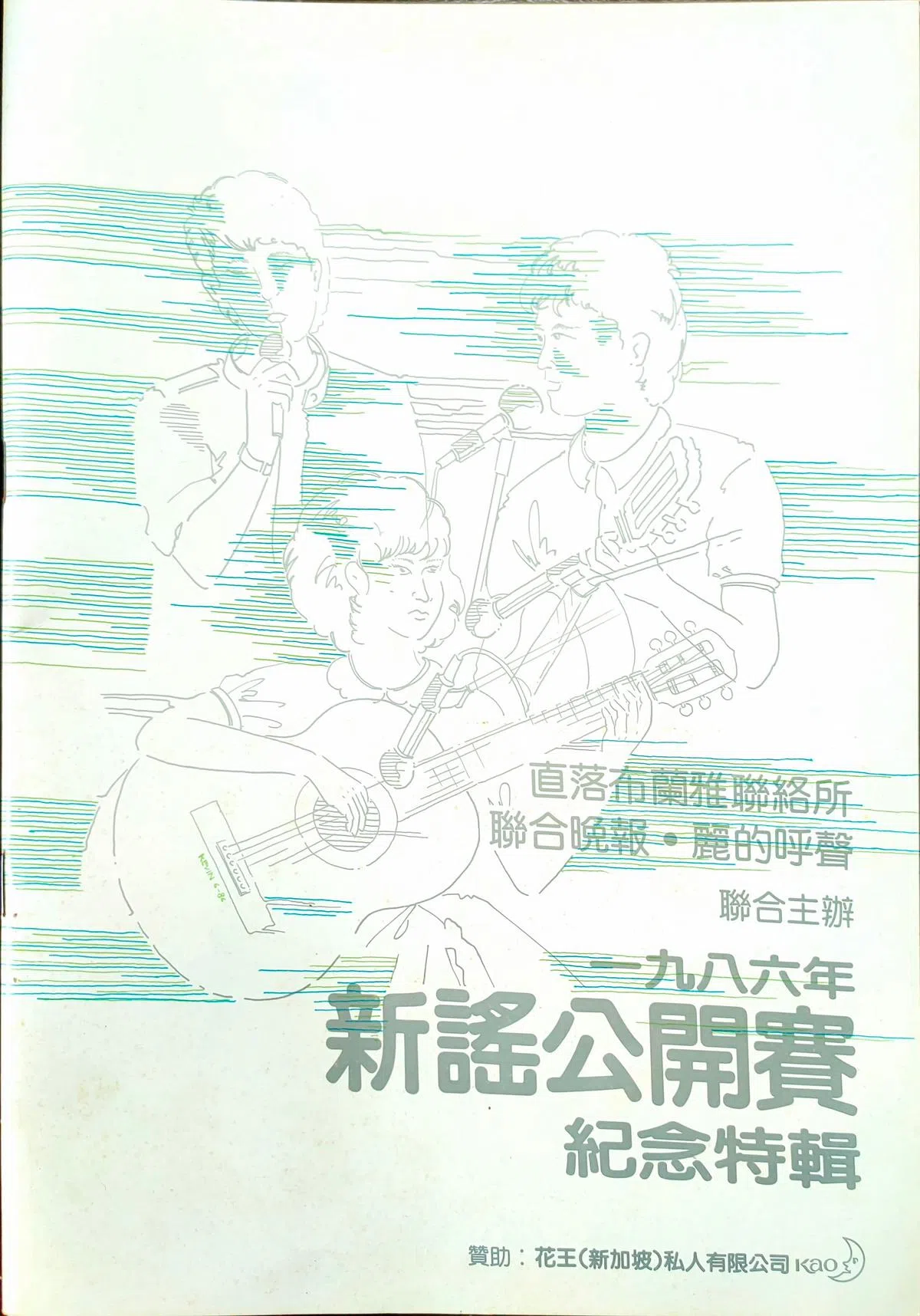

另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新谣的命名。
1980年代初,本地学府出现尝试自创歌曲的歌手,通讯员与金声文艺学会会员也多有喜欢自弹自唱的,我们在主办活动时,总出现如何称呼这类歌曲的问题。例如在友谊活动中心举行的欣赏会,就以“民谣风”称之。这类自创歌曲,歌手们称之为“新加坡年轻人自创歌谣”,名字既长而且难打题,也不容易推广。1982年,在《南洋学生》为歌手主催座谈会前,我要求与会者给歌谣定个名称。我建议,假如没有更好的提议,就用简化的两个字:新谣。座谈结束后,依然没有统一看法。有人认为,这两字不好听,像是“新加坡的谣言”。其实,“新谣”二字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
我认为事不宜迟,决定落实“新谣”这个名字,即日宣告新谣诞生。从此,各大媒体追随引用。2018年,“新谣”获选列入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40年后的今天,新谣已成为新加坡的一个身份认同的标志。

从《晚报·文艺》到《晚报晚咖》
1983年3月16日,两家华文报合并,出版《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南洋学生》与《星洲少年》稍后才以《联合学生》面世。我与董农政被分配到晚报,这是一份新的报纸,一切又从零开始。董农政在副刊组编文艺版《晚风》,一开始即大量采用《南洋学生》通讯员的稿,也是一种文艺的传承。我则重作冯妇,主编娱乐版,无兵无将,所幸有好几名通讯员愿意随我跑娱乐,像陈健良、周伟良、刘荣和、黄成财、郭永发等,每日两大版的《星海》就开张了。也因为一编就是五年,我有机会继续为新谣添砖加瓦,除了大篇幅报道新谣活动,也与人民协会、直落布兰雅联络所、丽的呼声等,联办两届新谣公开赛、新谣创作赛等,发掘不少优秀的新谣小组,把新谣推向另一个高度。
之后,我内调到新闻编辑组,参与六四天安门事件、波斯湾战争等大事件的报道。1994年中,总编辑陈正要我重开晚报《文艺》,由于只有三分一版,虽然每周出版五天,毕竟版位有限,我一样把焦点放在新人身上。只要是新人,或者看似陌生的作者,我都尽量给予发表,哪怕可能只有一节文字有点意思,也删删减减让它见报,就像在编《南洋学生》时一样。我知道,有人会“悔其少作”,但他们更需要的,也许是作品得以发表。
为了怕“人情债”占据《文艺》版小小的版位,我甚至不在圈里告诉人家我在编文艺版。也因为这样,我虽兼编《文艺》多年,却鲜少有人知道。在紧张的新闻编采冲线后,得以相对悠闲的心态编辑小巧精悍的文艺版,也是一乐。
那些年,我尽量发短小精悍的稿,当然,小诗最是适合了。最常做的是征诗,推出情人节、诗人节、中秋节等诗辑。
印象中,语凡的诗稿最多了,多到用不完。常见报的还有蔡履惠、灵犀、皂秋、陵旭、蔡建泰等,这些作者我都不认识,蔡履惠后来成为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硕士班的学妹,蔡建泰则最近在一个晚宴上见了面。
《文艺》偶尔也发表海外作家的作品,像印尼的柔蜜欧·郑、北雁,从本地到中国发展的萧村。
编辑组两名协助行政与《文艺》版电脑排版的编辑助理陈秀丽、白淑娴(贝斯涵),也都爱写文章,偶有作品在《文艺》发表。白淑娴2014年还出了一本书《孩在长大》,单看书名就别出心裁。
2005年11月,我兼编晚报言论版《尚议苑》。那时,报馆新来的女记者越来越多,我除了开设《新闻眼》专栏让资深同事点评时事,也设《报林西施》让新进女记者以年轻的视角,看生活看社会,磨练文笔。作者有应磊、洪奕婷、顾功垒、杨萌、陈彬雁等。另外还开辟《学府金钗》及《读书郎》,让在籍中小学男女生投稿。最难忘的是2007年7月,连载以轮椅代步的小六女生“折翼天使”卢家玮的11篇励志而感人的好文章。2014年,19岁的卢家玮克服重重困难,获颁年度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修读法律,完成心愿。
2007年10月起,《尚议苑》随晚报革新易名《晚报网咖》,我继续编至2014年,前后正好十年。除了邀请名笔如周维介、黄凯德,名人如小寒、陈之财等,以及编采人员撰写专栏,也一样有读者投稿的栏目,印象深刻的有“大头针”林秀融,写得很勤的蔡玉卿、黄德平、方苇莼等。除了蔡玉卿后来在我出书的活动上见面,其他作者也从未谋面。
报馆合并后,稿费都统一处理,编辑无需在稿费单上签名,因此,除了搞活动,编辑就是个隐形人。
不是结束的结束语
40年过去了,《南洋学生》不在了,《联合晚报》也消失了,但《南洋学生》通讯员与金声文艺学会的会员,今天已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有的在大学执教,有的在媒体奋战,有的在商场打拼,但都没有放弃文字的耕耘,也孜孜不倦地在为华文为文艺为培植新一代而努力。
像昔日的华之风——蔡志礼,除了领导当代艺术研究会、五月诗社,也是全国驻校作家计划的主持,《青春文选》的主编,并积极推广“南洋新诗乐”,多年来催生文坛新苗无数。昔日的牧汉林——林得楠,既是出版社的总编辑,也是作家协会的会长,除了自己在诗作上的出色表现,多年来也与蔡志礼一同推动多项文艺活动,像联办新加坡诗歌年、作家节,贡献杰出。也是创作歌手的仲仁康——刘汶錝,是杂志《优1周》总编辑。新谣才子梁文福,无论在写作上或新谣创作上已是一颗闪耀的明星。当年《南洋学生》的投稿者木子(李茀民),也是电视台与《联合晚报》娱乐版联办的《雾锁南洋》主题曲创作赛的冠军得主。我曾在新谣公开赛的讲座上期许,新谣能成为唐诗宋词元曲之后,新加坡文体的代表;也期盼,新谣能像美国民谣那样,出现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此外,金声文艺学会的汤玲玲、林松辉等,如今已是文坛健笔;林义平则活跃于锡山文艺中心。还有,通讯员王明凤的千金也加入晚报当记者。
多年来,人们总慨叹本地华文水平每况愈下,但事实是,新一代作者人才辈出,所以,一切都是进行式,不是结束。比如相对较年轻的陈志锐,既是优秀的写手也是热心的文艺推手。还有年轻的周德成、毛丽妃、林容婵,以及更年轻的安诗一等等,谁说文坛无人?
走过的必留痕迹,希望爱好写作的朋友,无需像水虿那样蛰伏在黑暗的水中,长达五年甚至七八年,蜕皮无数次才爬上水面,才有羽化成蜻蜓的可能。
我曾经的崎岖之路,但愿是你的坦途。而且,爬出水面后,会发现路上时时有贵人,哪怕我一开始就投身人称“恶人谷”的娱乐圈,会过所谓的“十大恶人”,也处处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们虽不是铜豌豆,是血肉之躯,但却要有关汉卿铜豌豆的精神。
在文学的长河里,在因缘际会的刹那,互放光彩,这一切看似偶然,却是我们的选择。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最近在一部连续剧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一本书的书名,也许可以做个注脚。
(下,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