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门功课,但人们鲜少能直面它;谈死是禁忌,孤独死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孤独死并不新鲜,近来愈发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不久前只和人口老化挂钩,但随社会形态改变,诸如弹性工时或零工,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交距离,孤独死可能只增不减。《我是人生整理师》是亲力亲为,近身观察的职人书写,《特殊清扫人》则以小说回应孤独死为何不断增加,以悬疑推理的笔法,探究死者内心,从终点追溯生前踪迹。
贫穷和疏离使问题升温
《我是人生整理师》作者卢拉拉是台湾殡葬业者,曾任“人生整理师”多年,职责是为亡故者整理遗物、住所和尸体,对职人身心冲击难以想象。他提到,疫情曾经加剧孤独死现象:确诊者在隔离的孤绝中死去,整理师身穿防护服进出,协助入殓、封棺和火化,家人被迫隔绝在外,一时间孤独死去不再只是年迈者的忧患。疫情后,社会看似在痊愈复苏,其实在边缘地带,贫穷和疏离使问题继续升温。
孤独死反映的是社会的缺口——长者驻扎冷气图书馆,或身处堆积成灾埋下火患隐忧的“垃圾屋”,这些在普世中干扰碍眼的现象,其实互为连接。《我是人生整理师》曾遇过亡者在炎夏中赤膊死去。当中多数是因为贫穷,被迫在没有冷气或电扇故障的住所中生活。对一些人而言是必需品的冷空气,也可能是另一些人够不着的奢侈品。而囤积症是一种无法扔掉物品的精神疾病,患者不能与拥有物分开,因而凌乱堆积物品,占据生活空间动弹不得。

房间反映居住者内心
《特殊清扫人》和《我是人生整理师》两书有一共同观察:房间反映居住者的内心。作为人生整理师,面对的是往生者最后活过的痕迹,然而孤独死的现场往往惨烈,不可名状之异味,凌乱堆积的物件。卢拉拉提到,最棘手的工作是垃圾屋。死者生前大量囤积无用之物:传单、塑料袋,过多的衣物、家具和电器,和过期食物形成的“生态系”,在在反映着淤塞的身心。
《我是人生整理师》后记中写道,现场物件可以透露生前的日子:健康和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没说出口的话。人生整理师接触的不只是事件现场,窥见从前,也目睹往后。如果死在出租房里,房东面对的烦恼是物业成了“凶宅”,房价大跌。与家属会面,为死者料理后事的过程也是现实见闻录,卢拉拉见过只在乎亡者遗物和财产的家属;也有殡葬业者为了业绩,利用家属想要弥补遗憾的心情,劝使他掏空钱包来办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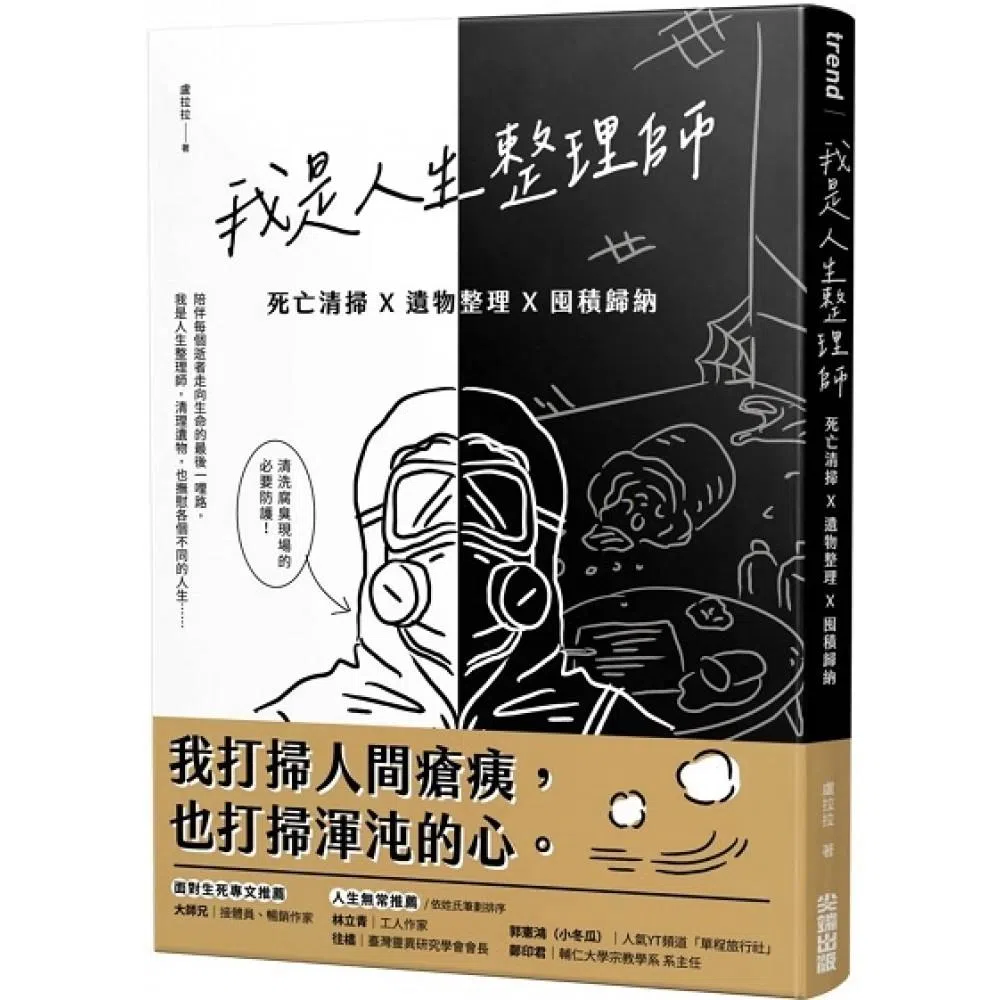
要求员工细心、迟钝
特殊整理师进入现场工作时,需要防护衣和防毒面具的层层保护,因工作暴露在细菌病毒等看不见的风险里。整理师的心灵是否也有安全屏障?《特殊清扫人》里写到,对新员工的要求是细心和迟钝。两个看似对立的词汇,折射了这份职业面临的矛盾纠结。
从作为案发现场的房子望出去,是庞大社会体系的问题。卢拉拉认为,政府的能力终归有限,必须要许多人努力把网织得更密,才能托住更多人。无论是殡葬业者,整理师或是社会福利团体,都可以助一臂之力。他相信关键在于“关心”,当人们遗失了关心和在意,冷漠取而代之,孤独死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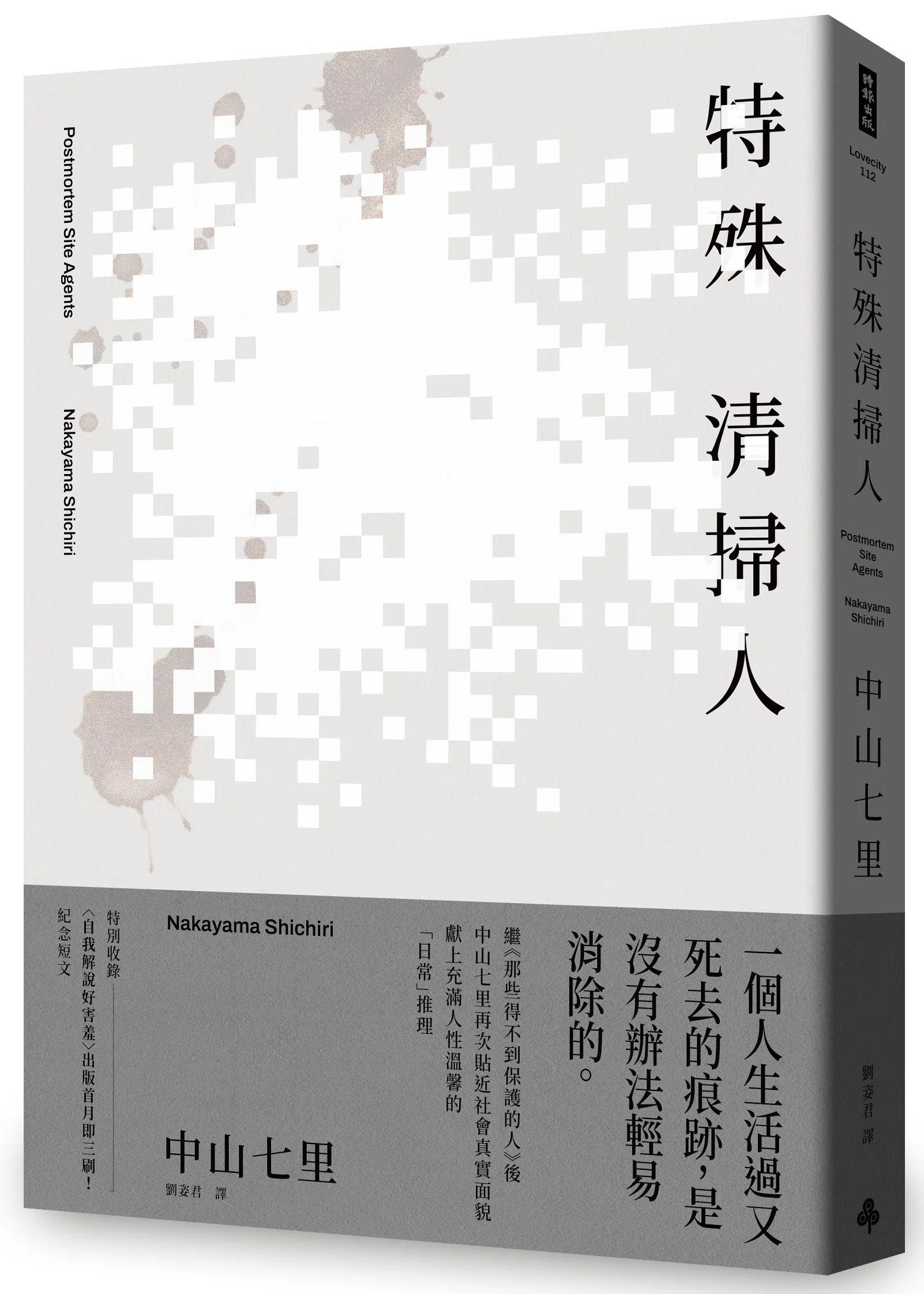
《特殊清扫人》是推理小说集,特点是四则故事皆从结局倒推,带读者跟随整理师先到现场,再一步步回溯死者的生前,从身边人与周遭事件还原故事的血肉。从篇名关键词感受小说基调:祈祷与诅咒,腐蚀与还原,绝望与希望,正负遗产;每个亡故者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中拥有立体的形象,毕竟数字容易使人麻木或掉以轻心。
“人心,是最悬疑的推理。”以推理小说出道、《特殊清扫人》作者中山七里那么说。他认为孤独死存在多年,要谈它为何增加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但爬格子的人还有另一份工作,就是“哀悼在孤独中死去的人,贴近他们的内心”。他尝试用几道推理小说的典型谜题,探究死者内心:为什么非死不可?如何死去?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也作为小说家对孤独死之社会议题的回应。
推荐阅读:
赖昭宏《伤痛的祝福》(大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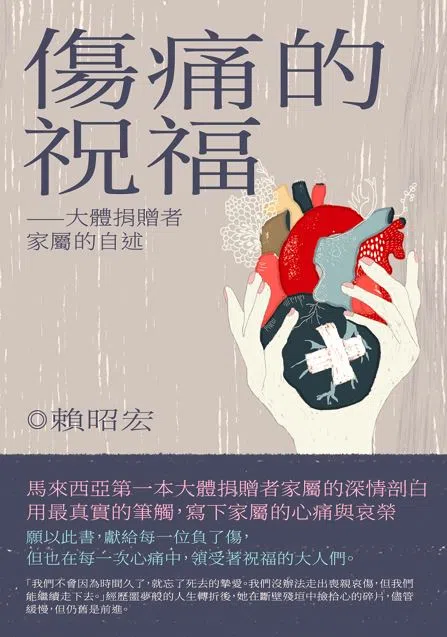
“不是只要有大爱,就不会觉得痛。”
大体捐赠者家属的真情剖白,以真实笔触写下家属的心痛与哀荣。父亲患病骤逝,不久后又发现母亲罹癌,作者一下肩负全职照顾者的身份,后遵从母亲遗愿,成为大体捐赠者的家属。她原来在国际慈善组织工作,也是器官和大体捐献的意愿者,不曾想过会以家属视角审视这一切。后来她修读生死学,学习丧亲陪伴和临终关怀,希望成为更好的“负伤疗愈者”。
伊藤比吕美《身后无遗物》(蕾克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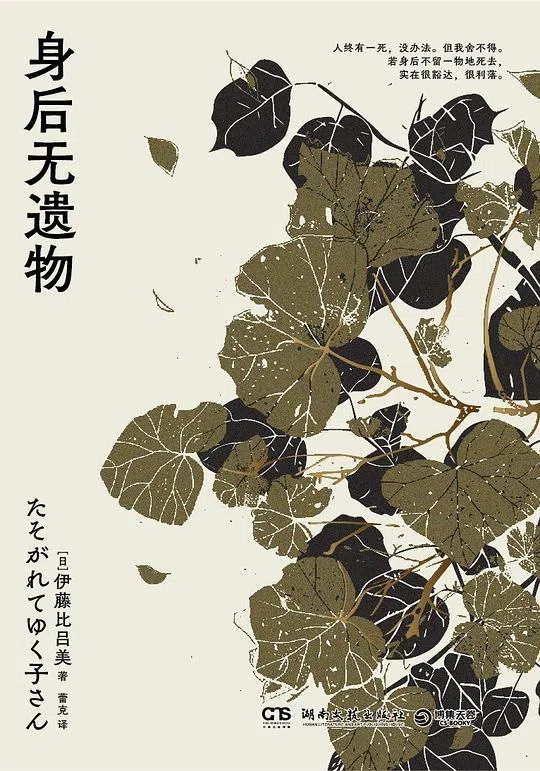
“我五十多岁时度过了快乐的更年期,现在六十多,感觉人生在褪色。老去这件事,实在太寂寞了。”
母亲住院四年离去,作者为她整理遗物时,希望自己也可以如母亲般,身后不留一物地死去。丈夫断崖式衰老后病逝,作者感受到老去的寂寞,独自生活的不便,但也拥有自由,可以活得自我。作者不因为老去而放弃自己,而是努力培养兴趣爱好,如跳尊巴、养狗、做饭、写作,让生活充实有趣。
独自面对衰老、死亡、告别,一步步走进孤独,但她从未忘记自己是谁。不惧怕寂寞,活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