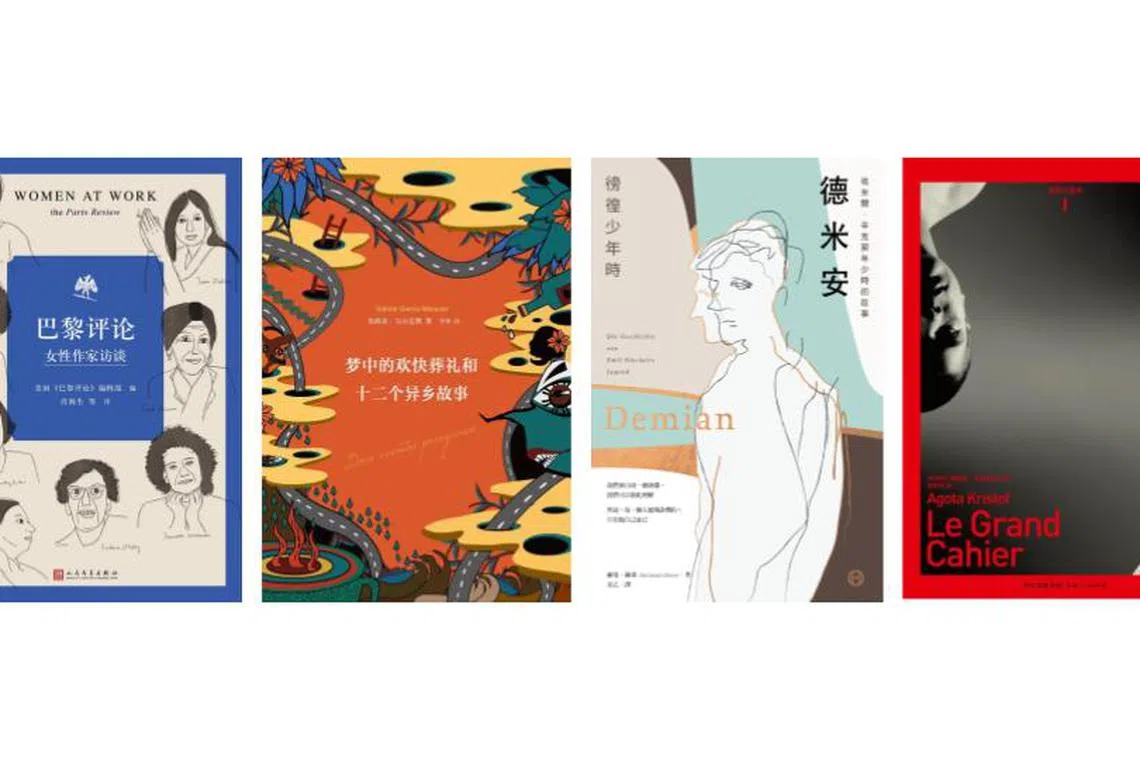文化奖得主林高2018年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担任大学基础写作的讲师,2024年功成身退。新生代作家随庭接棒,继续培养写作苗子。趁此机会,本栏邀请两人对谈,从教育者与创作者的身份思考写作的意义,并为年轻读者推荐书单。
先打开阅读的法门
林高说,过去六年开课,学生人数从16到36人不等,林高发现他们往往缺乏阅读一篇小说、一首诗的经验,因此写作课首先是要打开阅读的法门。
阅读与写作并重,但林高最在意的,是如何通过阅读与写作唤醒年轻人的审美意识。
“我觉得唤醒他们的审美意识更重要,因为不管写不写作,在你的生活中,作为一个人,审美意识有和无,(让你的)生活品质完全不一样。 ”
写作有助思考,林高认为,许多事情如果只是放在心里,过去就过去了,这些心里头的感情,加以整理,配合写作的技巧,展现为美,有益于人的成长。这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作家,“懂得写,知道怎么写”更为重要。
林高不同意文学是成本最低的艺术,“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作家,那就要看你做了多少准备,打算走多远。”
不要小看文字创作,所以他也不强求来上课的人成为作家。
能写作与成为作家是两回事。
此前林高以小说与诗为教学重点,随庭则会更着重于小说。随庭说,这与个人的创作经验相关,她也认为学生平时写小说的机会比较少,课堂是个很好的平台,先从阅读小说开始,分析小说好在哪里,作家为什么做出下列的选择。
培养学生表达能力
随庭认为写作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技巧。她想培养学生的思考和表达能力。她说当今流行的脱口秀,都必须先创作脚本。此外,短视频博主在从事的其实也是一种表达,这与小说创作是共通的。
她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国大中文系、研究生过程中其实很少写作,当自己重拾创作之笔,马上发现大学时代学会如何细读与分析的训练,对个人创作起着很大的作用。
写作能力可以培养,但在新加坡的华文写作大环境,我们看到的是,许多人离开校园投入职场后就不再提笔写作了。
写作课有没有培养作家的责任?随庭与林高都相对看淡,毕竟你不能干涉别人的选择,尽管看见有才华的人没有继续走这条路觉得很可惜。
不过随庭从另一个角度谈道:“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继续写作)可能也是一种幸福。我有个学生问过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写小说的那几天,心情很低落、很抑郁。因为当你沉浸在小说创作的世界里,故事又不是永远那么光明、那么轻松,甚至当你要写一个很哲学、很沉重的话题,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写作)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随庭坦言自己也常有类似的感受,渐渐觉得坚持写作是很困难的事。当她认定写作是她想要持续下去的事情,她给自己的目标就不是要得什么奖、出多少本书,而是创造一个可以容纳写作的生活。
这么痛苦为什么还继续?
随庭引波兰诗人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的名句回应:“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文学有结缘的力量
写作多年,林高相信文学有结缘的力量。年轻时投身教育工作,结识辛白、蔡欣等创作者,进而结交李向、林臻等前辈作家,进入文学环境。接着到台湾升学,走入人文氛围更浓的环境里。如果没有文学的结缘,林高很可能就掉队了。
此外,因为身体有神经痛的问题,林高无法长时间阅读,不敢太兴奋,直到退休后才有好转。“所以我非常欣赏自己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不然老早就掉队了。我竟然走到今天。”
林高说:“我觉得写作者一定要有一些信念,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不讲信念了……不过当你越想要文学改变什么,它越不能改变什么。所以你就让文学在那边,它在某个时候能发挥力量的时候,就会发挥力量。”
他感慨:“如果我没有写作,我将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真不敢想象。所以回到审美意识,对每个人是第一重要的。你写作不写作,去跳舞,去画画,去搞别的事情,但是审美意识存在,你的生活品质就会不一样,你到老了,你也不怕老了。写作帮助我认识这些事情。”
【林高给年轻人开的书单】
·张炜《文学八个关键词》
·简·赫斯菲尔德(Jane Hirshfield)著,杨东伟译,王家新校《十扇窗》
·葛兆光《唐诗选注》
·与谢芜村著,陈黎、张芬龄译《四海浪击秋津岛:与谢芜村俳句475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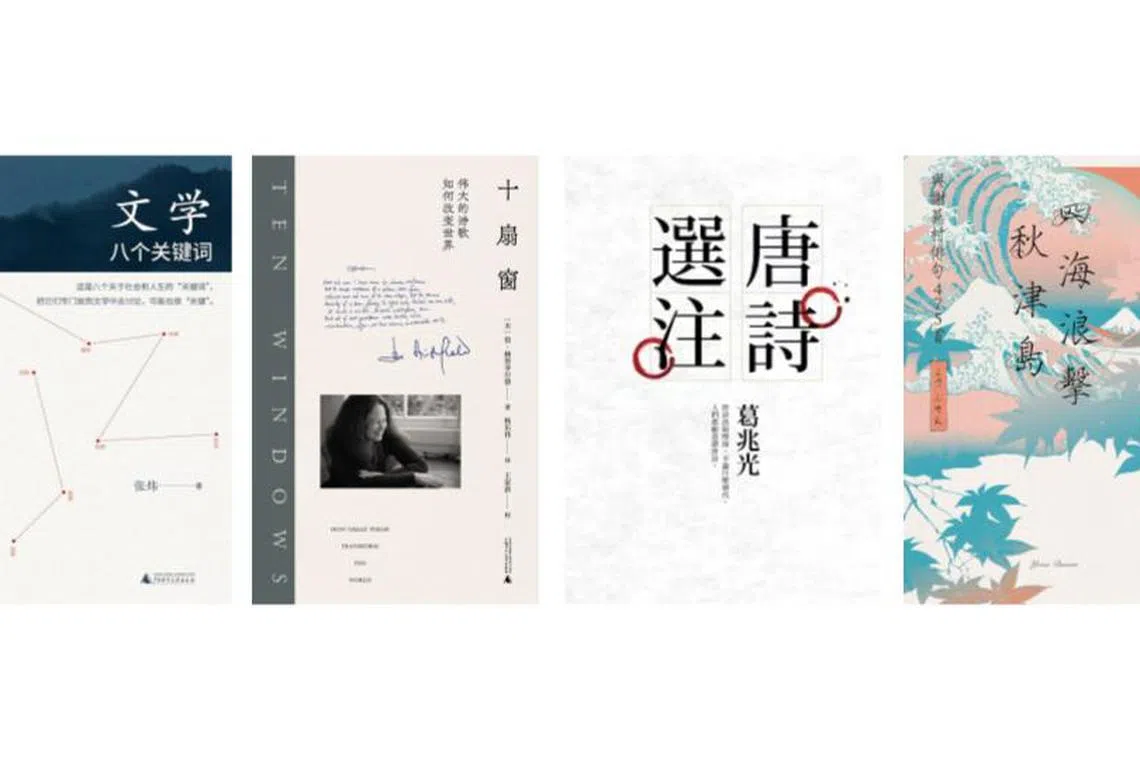
【随庭给年轻人开的书单】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德米安》
·雅歌塔·克里斯朵夫(Agota Kristof)《恶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