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书名曰《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作者苏美说,文艺女青年气质恬静,多愁善感,恃才傲物,不愁衣食,远离烟火灶台,不食人间烟火……文艺可以作为一种爱好,但永远都不是生命的全部。生活是踏实的、接地气的,所有纤细、敏感、伤春悲秋,在生孩子这件事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从怀孕开始 ,你的语言使用就身不由己了,你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回答医生提出的各种尴尬问题,你要协调丈夫、婆家和娘家的三角关系,你要经过各种常规产检的历练,还要忍受孩子给你带来的阵痛,这还不提因为怀孕没办法接的活,没办法升的职和没办法加的薪。你变的很难控制情绪,不能自理;你需要帮助却羞于启齿。”
面对越来越多的世俗压力,文艺随时成为笑话。交织在金钱、人际、家庭生活的欲望之网里,文艺女青年又能做什么呢?如同台湾作家赖香吟在《文青之死》中那么写:“如今文青当然不是个干净字,消费流行与装腔作态使它讨人厌,这本书回收此字,不是拥护,不在批判,而是想理一理文青这个字曾经干净的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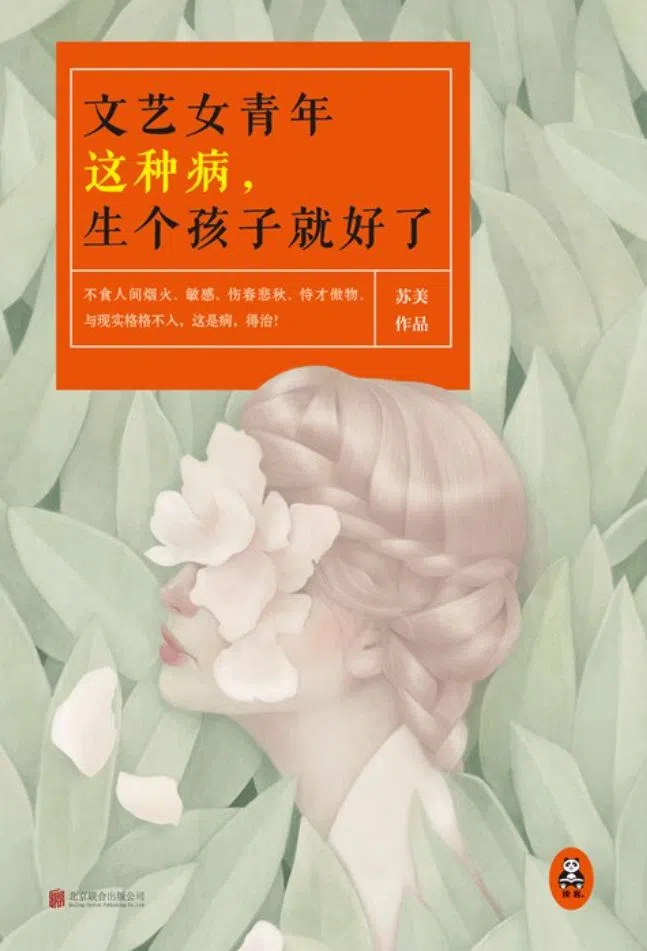
“文青”一词生命力源源不绝
《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和《文青之死》出版近十年,“文青”一词还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虽然释义早已不纯粹,褒贬不一。《文青之死》中开篇〈在幕间:一则伪评论或伪小说〉,熔炼历史和虚构为一体,对照前世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其丈夫友人,说着从古至今的妮亚、雷、曼殊和薇塔们。现世妮亚把自己全献给了写作,婚后亦然,即使引来情绪危机也坚持自我。而雷把兴趣转向政治与社会,战争的来临反而让妮亚不知如何自处,因而彻底漠视,绝口不提。面对社会,文青有文青的尴尬,即使是真正关心社会的那群。妮亚永远和世俗保持距离,曼殊却入世而自由;妮亚渐渐隐匿退出,当黑幕落下灯又亮起时,登场的主角已经换成曼殊。
我们还能在台湾作家胡晴舫全新小说《二十岁》里看到文青的后来。经过世纪末的政治动荡,世界格局改变,社会追求现代化,一代文青也会老会死,哪一种比较可怕:永远停留在二十岁,还是渐渐变油变滑,习惯在言语中加香精抹蜜?后来,他们或许结婚了,或许进了文化机构,一些些文学野心都用在写公文或电邮。如果语言训练是为了人类之间的沟通,进入体制以后,是不是也必须学会一套全新的语言,期许自己早日从菜鸟变老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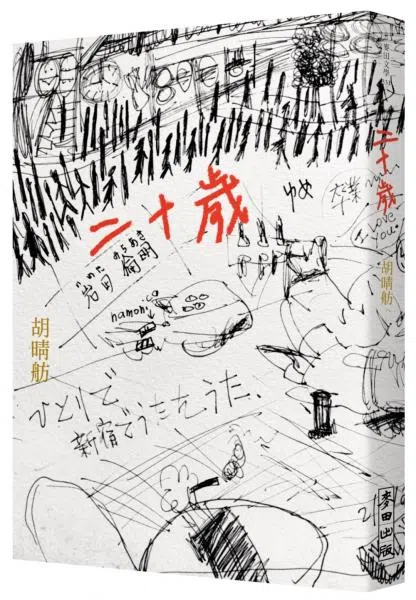
以为是魔幻原来是写实
〈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里的“我”还是学生时读卡夫卡《城堡》,以为是魔幻,原来是写实:“过去学院里的陈君,向以脑袋清楚,批判犀利叫人印象深刻,当我们议论事情,一旦打马虎眼,很难不被她扳倒,这使得她的左派信念不仅仅只是一种玫瑰色的光晕,而是带着防守与斗争的动能。我静静看着这样的陈君,把她那闻到剥削总是灵敏的鼻子,对权益计较分明的脑袋,转向应用于分工、年资、加班、公假种种算计。我们的左色青春,一场热情操练,结果是让我们变成精明苛刻的成年人吗?”
经过天安门事件、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民主风起,911事件,如果文青活得够久,也许就又能被重新记得。〈在幕间:一则伪评论或伪小说〉里,前生妮亚(伍尔芙)已经又被这个时代的人们重新追捧了,她成为新的流行符号与装饰,即使是忧郁或尖薄的下巴,也新添了现代性和女权主义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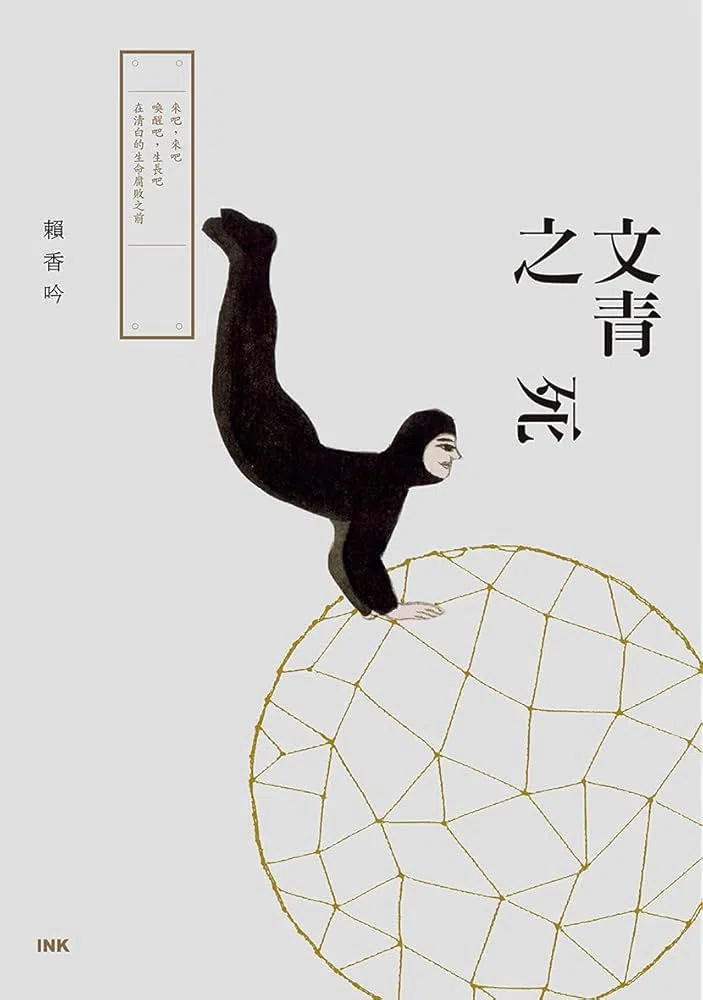
重新回溯与想象文青
而〈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从歌手艾略特·史密斯(Elliott Smith)之死说起。偶像死掉了,文青痛哭流涕,但世上明明没有了史密斯,他的网页还是继续更新,他的专辑还再一张张地出。带着被欺骗但又半带侥幸的心情,文青有了继续生活的勇气,感谢消费主义。文青也许还进电影院看“Before Sunrise”,即使身边换了人,即使不再承认自己还看电影,因为能从庸常生活间看出痛苦来的自己,已经消失了。
〈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的叙事语调就像和读者聊体己话,“我”为其他故事人物取代号,朋友陈思思又叫吉儿,约会对象有海报男、棒球男。而文青交流的结果是“我”怀孕了,棒球男的。结婚成家生小孩,情节走向又和苏美的故事对上了。有了孩子,“我”和吉儿不太听艾略特·史密斯了,作为一个妈不能悲伤,只能“现实地需要更多体力与乐观”。
小说中是那么写的:享乐是热的,痛苦也是热的。知识要拿来服务生命,而非拘抑生命。赖香吟便是那样,借《文青之死》九篇作品重新回溯与想象文青。“文青成为一个死字无妨,余下来初心不改就请挥别脆弱惶惑的自我,然后,怀抱着那么一点干净,继续向前走吧。”她在后记里如是鼓励那些,被错误的情感、志业的彷徨病去大半生的文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