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都害怕虫子,天真以为建了房子就可以杜绝虫子。
城市生活意味着人类以文明力量改造大自然,以各种结构排除人类以外之物,创建只属于人类的理想国。
可是虫子无所不在。
再牢固再华丽再多么无菌的房子里,虫子总要先人类而住。
都市传奇曰:若见一只蟑螂,即一家子蟑螂都已在你屋子里啦。
其实虫子比人类还适合住在人类的理想国,只不过是在缝隙里。
有时候人类还妄想利用虫子控制虫子,像是新加坡政府过去一年多来在试点放生的带病雄蚊,一旦与雌蚊繁殖,后代必定胎死卵中,但蚊子多起来却很烦人,会吸血的雌蚊还好,吸饱了动作迟缓,没吸血的雄蚊更难拍,在房子里咿咿咿的没完没了……
生活总在为这些琐事烦恼,应了张爱玲那句有名的虱子论。
虫子应当是顽强的存在,而人类却如此厌恶且惧畏,也许其中也有一点嫉妒心作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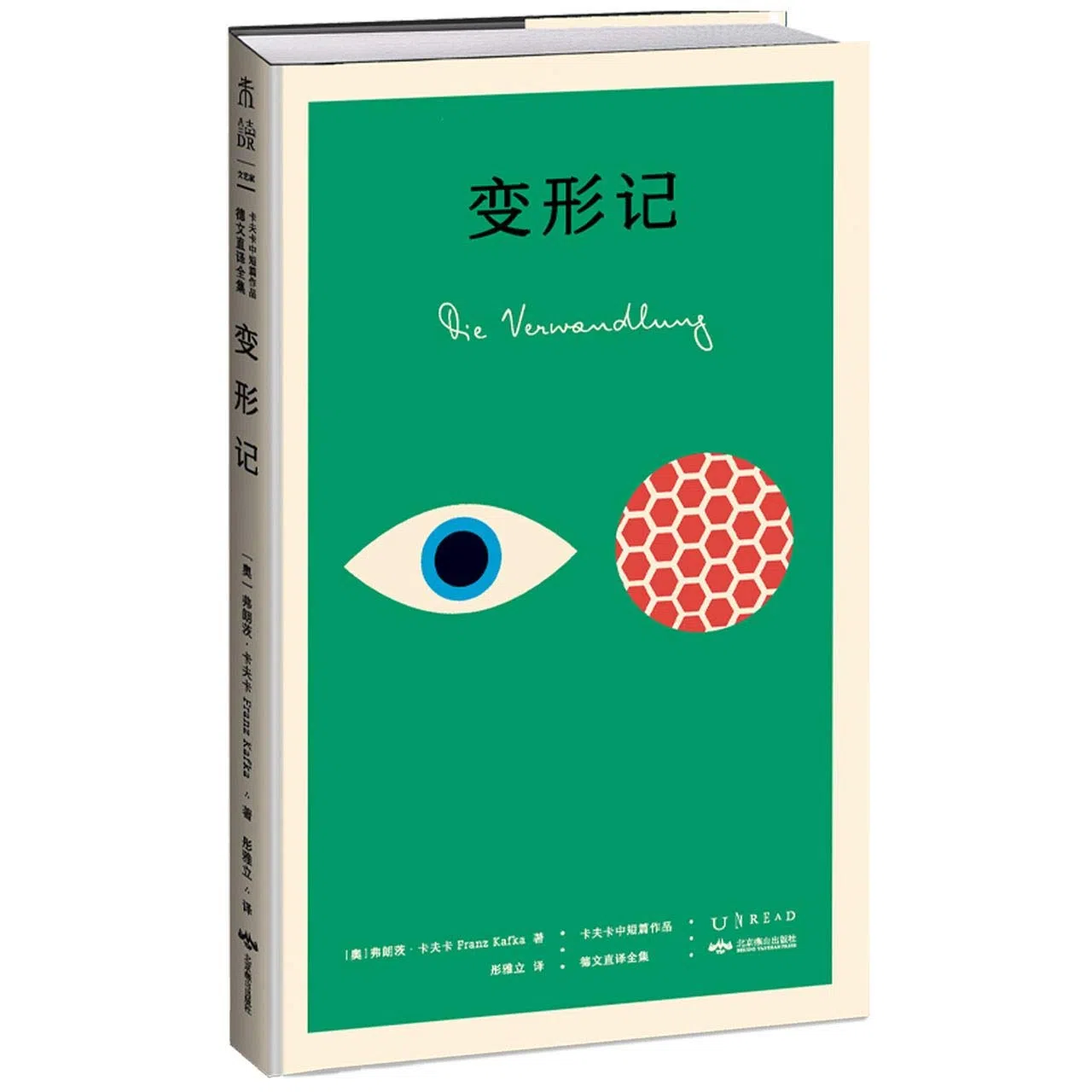
卡夫卡反思现代性
于是卡夫卡给世人一个最恐怖的文学起手式:“某日早晨,格雷戈尔·萨姆萨从不安的梦境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蜕变成一只阴森巨大的害虫。”
萨姆萨到底是变成了一只臭虫、虱子还是甲虫,诠释者多年来喋喋不休。台湾译者彤雅立的译本选用“害虫”——她注释:德文原著里使用“Ungeziefer”意为有害的昆虫或动物,词源中古高地德语“ungezilbere”与古高地德语“zebar”,意思是“不洁而无法用以献祭的牲畜”,后来也被用作反犹太之词语,如此说来,不管臭虫、虱子或甲虫,卡夫卡在意的,不是虫的品类或外形,而是这个称谓的历史脉络。卡夫卡或许是想用《变形记》提醒大家,人类集体文明理想国其实对个体之压抑,在某种历史情境底下,让人连虫子都不如——进而反思:现代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进步的承诺竟然全用来作为剥削的理由。
卡夫卡的叙事手法出了名如梦般跳跃,但《变形记》似乎是一间构造比较“正常”的房子,从头读到尾并不叫人太昏眩。
总觉得短篇小说就像一所所房子(甚至是一个个房间),小说家如室内设计师,如何运用空间,如何引导读者深入其中,极考验功夫。偌大的房子里,要如何调度那些虫的意象?下来谈两个短篇,或许可以做良好示范——韩国作家金爱烂《虫子》与马来西亚作家龚万辉《无限寂静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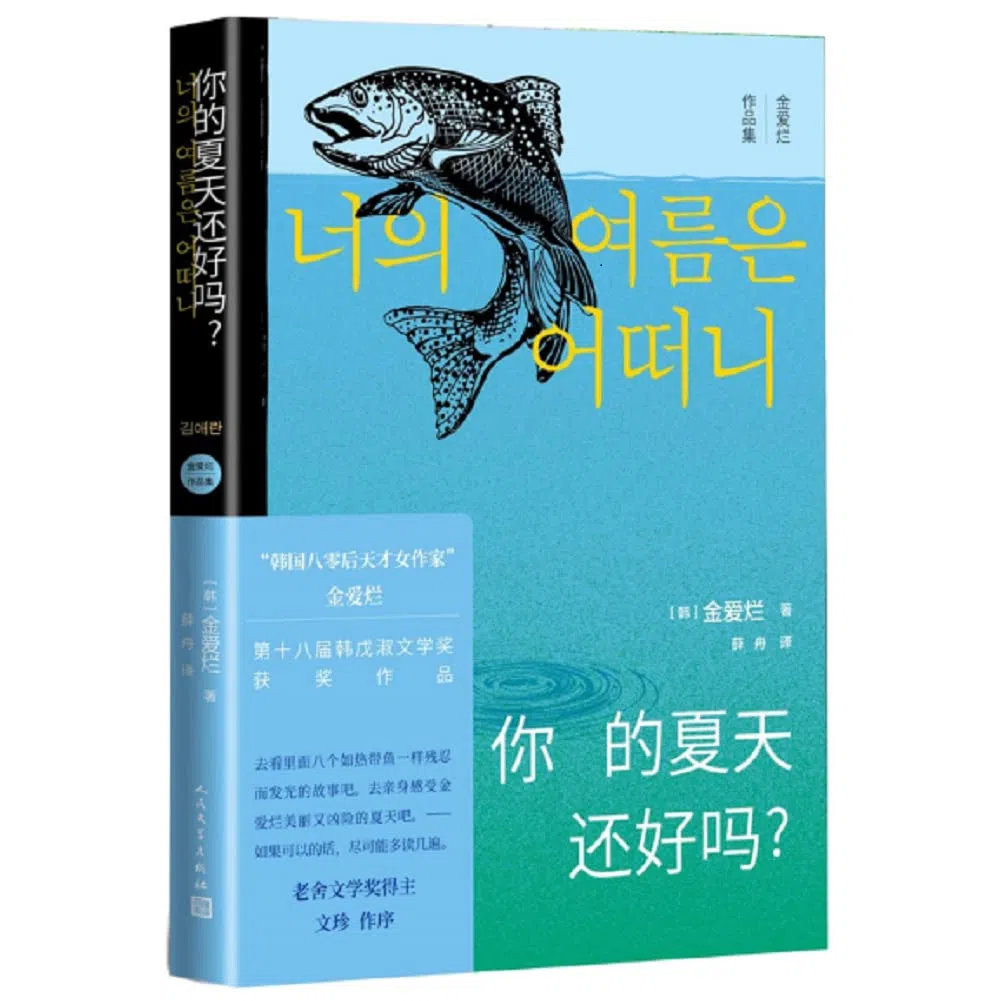
虫子推动剧情与转折
一对夫妻搬入“蔷薇公寓”展开新生活,却没想到是一连串生活烦恼的开始:妻子先是在屋外看见虫子,后来一条“钱串子”出现在屋子里,引起夫妻俩的恐惧。钱串子是一种多足,看起来很可怕,仿佛外星生物但其实无害的虫子。就在发现钱串子不久后,妻子怀孕了,第一人称叙事者妻子说:“孩子应该诞生于我们在洗碗池前交合,因为强烈的洗涤剂而浑身火辣辣的那个夜晚。搬到蔷薇公寓的第一天,孩子也入住了我的身体。”
精虫成了另一种虫子,从此女主人翁与这栋房子的命运重合。
金爱烂接下来以古典乐对位作曲的精准度,将这对夫妻,尤其是妻子的生活,与他们的房子及整座蔷薇公寓对照起来。当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蔷薇公寓这个社区也一天天改变,其中一个区域正准备拆除。怀孕其实并不在夫妻俩的计划之中,艰难做出生育的抉择之后,丈夫发奋工作,妻子独自在家,莫名的恐惧与日俱增,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结果夫妻关系日益疏远,而小说家选择虫子作为推动剧情与转折的意象,让这对夫妻始终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城市阴影之中,甚至连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成了虫子般的存在(“孩子在腹中蠕动,似乎急着爬出来,动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攻击性”)。
小说尾声,妻子走向被捣毁的社区,在一棵倒下的大树底下,发现“大量的虫子成群结队地移动。长长的虫子队列分成几排,像难民似的拥向城市——城市”,仿佛那也是他们夫妻俩的命运,随波逐流来到城市,却陷入更漆黑的境地。小说家安排至此,不可能让妻子安然回到房子里了,她必然要在荒野,在残破如末日场景,在虫队四面八方蠕向自己的紧要关头,孩子急着降生:
“‘救命!’遮板那边远远地传来汽车的噪声,仿佛有人故意散播的谣言,绕过A区域,消失又出现。只隔一层膜,我却感觉那声音太遥远,忍不住想哭。小腹痛如刀割。我用力握住混凝土碎片。远处,蔷薇公寓、旅馆、教堂、大楼一如既往地平静,而我不知道分娩能否成功。”
小说戛然而止。分娩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开放的结局牵动的是小说人物缘何走到如此境地的缘由:产前忧郁症?命运使然?但可以确定,问题肯定不在虫子,而在于城市生存法则里隐隐的隙缝先验地让人对未来无可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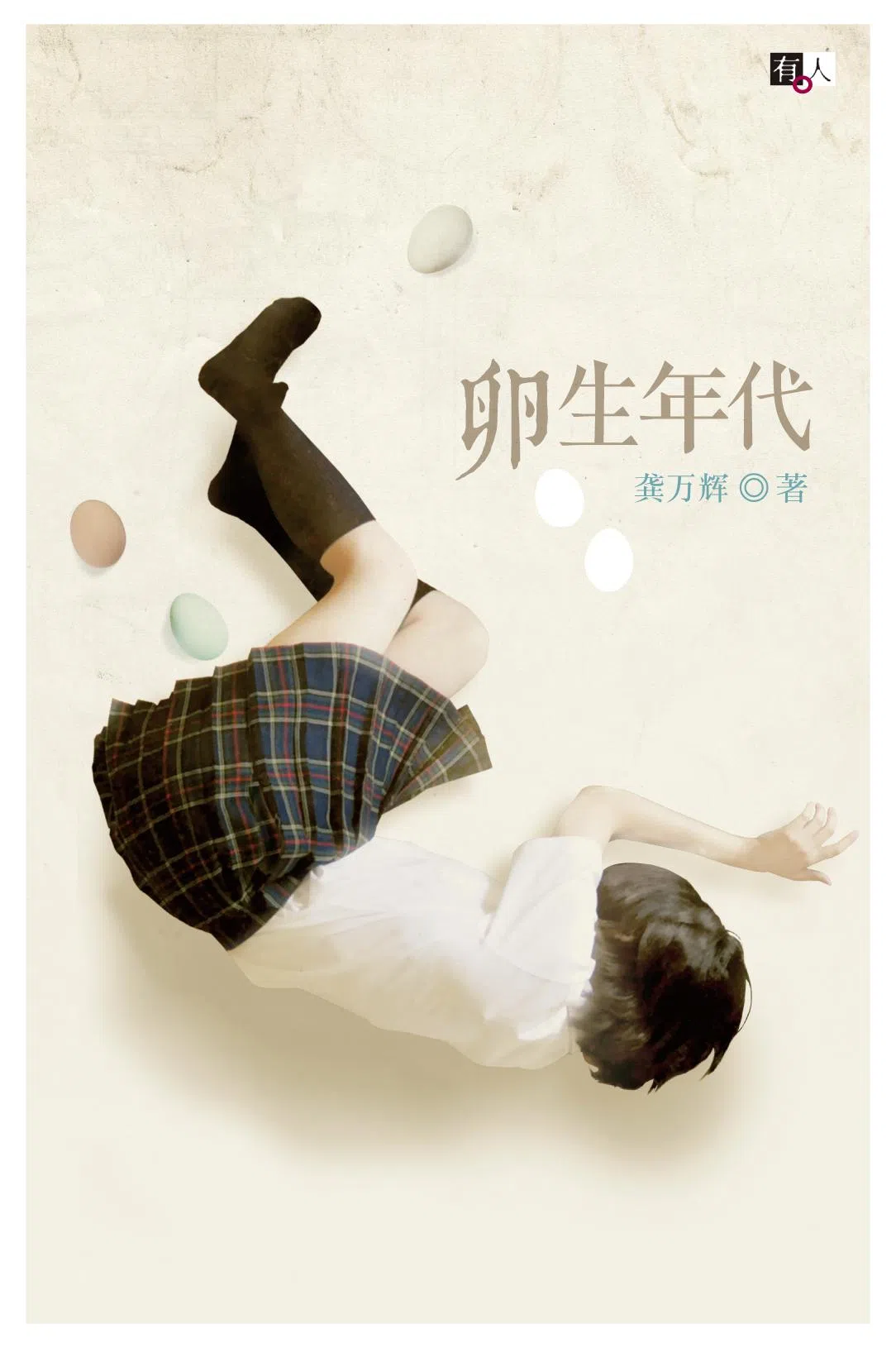
用声音的波纹勾勒寂寞
在龚万辉《无限寂静的时光》里,我们切入丈夫的视角,在寂静深夜的客厅里,听水蚂蚁制造的微弱且持续的噪音,混搭着妻子沉沉睡眠中磨牙的声响——大音希声。原来妻子因为失去腹中孩子而陷入昏睡,久久没能醒来。
他卷起报纸杀虫,“报纸拍在地上啪啪作响,随即屋子又回复一片安静,房门背后仍然传出妻子磨牙的细响,恍惚有什么正在被渐渐啃蚀殆尽。”
当其他小说家操作虫子的形象凝造恐怖氛围,龚万辉则利用声音的波纹,勾勒一对夫妻面对丧子之痛的寂寞。如何唤醒妻子?丈夫想起妻子曾说过“梦是没有声音的”,他此时仿佛也在梦中,唯虫子的噪音使他有了一点真实感。
恍惚间,“他发现妻子的身影正在慢慢地稀薄,仿佛错觉了自己可以穿过妻发出荧光的肉体,透视到床单的图案。嗤嗤咯咯,嗤嗤咯咯。那细微的声响此刻又自寂静中浮泛出来。他凑近妻的脸看她,想是妻子又在磨牙,却发现那细琐烦躁不住的咀嚼声来自屋子的各处,从木条砌成的地板,纸箱的背后,掩盖了水渍的天花板和墙壁之中流泻出来,无处不在。”
丈夫想要抚摸妻子,想要爱,却怎么也阻止不了妻子消失。
到此,叙事越来越魔幻。这是龚万辉的拿手好戏,这些房子、房间如砖瓦,慢慢构筑出获得花踪马华文学大奖的长篇小说《人工少女》。
《无限寂静的时光》尾声,丈夫用锤子砸破白墙,水蚁巢穴被捣毁,集体飞出,虫子脱落的薄翼铺满房间,但妻子继续沉睡,不为所动。
“他不知道,飞蚁倾巢而出之后,整幢公寓正在沉默且坚决地摇晃。窗架喀啦作响,悬吊的灯泡摇晃出忽长忽短的影子。公寓的窗外,倾斜的夜城光景一整片一整片地熄灭。他不曾知道整座城市不堪他的戳刺和敲击,在他的身后碎裂、崩塌……他此刻听不见任何声响,在那无限寂静的时光里,他心底却平静无皱,有一瞬间,他恍惚以为自己已经钻身进入了妻子的同一个梦中。”
这是同床异梦故事的变体,夫妻因为胎死腹中而出现隔阂,丈夫走不进妻子的世界,仿佛妻子关闭了自身的通道——当然,这篇小说始终是以男性视角切入。直到某个边界被敲碎(白墙),恐惧的事物飞散,丈夫终于有了进入妻子梦中的安慰,这又是庄周梦蝶的变体了。
这两篇关于房子与虫子的短篇小说,在虫子成群飞散的瞬间,一个看似悲剧,一个或已得到纾解,都是开放的结局,值得玩味。小说主人翁最后的变形,衔接起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使如此跨文本的阅读,也有了做梦般跳跃的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