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城市阅读节,请来了中国著名作家王安忆,带着新作《儿女风云录》,这是她以大上海时代变迁为主题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王安忆在“历史与我”讲座上,以质朴又不失幽默的语言,和读者谈了她的文学观和创作观。
王安忆第一部以“上海滩”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发表于1995年,它曾于2000年获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又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长恨歌》已成为上海文学的经典作品。

珠玉在前。相隔30年后,这部新鲜出炉的《儿女风云录》能否超越前作,还是炒了冷饭?相信无论是王安忆的读者还是研究者,都会心生好奇与期待。
《儿女风云录》开篇的时间点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期,地点自然是上海——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最早接触西方文明,也最为国际化的城市。
在那个时代,这片地方发展如此迅疾,一半紧追国际潮流,另一半停留在旧上海的时光中。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片魔幻现实的景象,并非矛盾,也非撕裂,而是各种奇妙对立的混合与交叠。
比如在新旧城市的时光罅隙间,总有人徜徉于旧时光里,把玩过往的种种物品,迷醉于曾经的荣光与浮华。
那日夜兼营的舞厅便开设在这样的罅隙间,为普罗大众而设,格调不高,却能够在变幻的光影与浪漫的节奏中,让池中的舞者迷醉、忘我,陷入一场短暂的幻梦。
舞厅仿佛一个巨大的造梦机器,白日里也营造出夜间的氛围,以本地居民为主。晚上则是外地人的天下,因此有了一群专门教外地人跳舞的师傅,带她们褪去土腥与俗俚,生出一点华丽的格调,体验一下迷醉的氛围。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教舞师傅中最脱颖而出的那个,名叫“瑟”的“老法师”。“老法师”在上海指的是精通某一行或智慧经验融会贯通的老人,小说中这位老法师更是给人一种世外高人之感,具有让舞者从生手一路升级至高手的高超能力。舞伴与他共舞,其他人只有屏息围观的份,酣畅淋漓一曲下来,仿佛黄粱一梦,游了一趟太虚仙境。
舞厅学员请其他师傅喝饮料,请他喝的却是各式洋酒,可见其地位超然。
然而,这部小说中最奇妙的人物,或许并非是瑟,而是另一个更为神秘的,只听其声而不见其人,有时从全知全能的角度评判众生,有时顺着人物的目光叙述稍加延展,使得读者所见所闻比人物更透亮一点,对他的生活个环境印象更深刻一点。大多数时候,她与人物贴得很近,甚至合二为一,大家共享第三者的有限视角,读者看不到的,她也假作看不到——这个奇妙的人物便是小说的叙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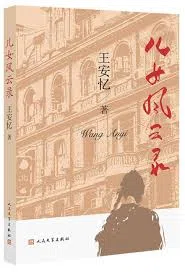
她(也可能是他)带着说书人腔调,感觉是个老上海,对市井弄堂里的生活所知甚为详尽,开口如数家珍,上海女人特有的密集语速,精明而犀利的语言。
小说开始了,叙述者话语间带有任何时代说书人惯有的狡黠,说一半藏一半。她絮絮叨叨地向读者交代小说世界的第一个场景,为主角的出场做了一系列精彩的铺垫。
主要人物瑟千呼万唤始出来,真容也只是舞池中露出了惊鸿一瞥,瞧见了,却又不清楚,且又在曲终人散灯光亮起之前遁走了,神龙见首不见尾地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欲罢不能的读者们只好在叙述者的提示下,紧赶慢赶地紧随瑟的脚步往外走,在华灯初上的光晕下,在不知哪里凑来的亮光一晃而过中,某个明眼人才幸运地瞥见了他的轮廓——外国人!
把之前的零星印象拼凑起来,瘦长的体形,一张脸白而立体,眼窝、鼻凹、下颏中间中间的小坑,可不是一个外国人?
一副外国皮囊的上海老法师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何他少年时又该何等的英俊倜傥,众多好奇与期待一下子便勾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
小说便从瑟的身份之谜展开,以他的人生经历作为小说的主线,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叙述了他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他与身边的人复杂矛盾的恩怨情仇,分分合合如同定在三生石上的缘分与情义。
小说的时空并非只局限于上海滩一处,瑟数次离开上海,去到天南海北,最长的一次长达十八年,远至地球的另一端,没想到最后又宿命般回到上海,藏身于尚未拆除的几间石库门里弄之中。
自成一格老上海文化
《长恨歌》和《儿女风云录》都是以魔都上海作为主题,通过讲述生活其中的个体的命运,反映出时代变迁下中西交融自成一格的老上海文化,海派市民们对生活自身意义的追求与热情,以及能够留住旧时光优雅格调的具有魔幻色彩的上海弄堂。
两部小说前后相隔三十年,小说创建的上海文学世界不仅相通,而且互为补充与延伸,人物具备可比性。
通读之下,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作者王安忆的成长,她对于相同的题材立意构思,在文学表达上所用技巧的差别。
王安忆是出了名的高产作家,除了家学渊源,自身勤勉创作之外,大量阅读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学习借鉴国外优秀小说则是她成功的关键。
王安忆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198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她在里面所虚构的高举“仁义”之名的小村庄,便是受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名作《百年孤独》中所虚构的象征百年拉丁美洲的小镇马孔多的启发。
《长恨歌》的创作,则是借鉴了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开篇前四个章节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与“鸽子”(让人想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笔下的巴黎,而上海曾被称为东方巴黎),以华丽恢宏语言描绘出的城市景观作为小说的开篇,显现出作家创作出杰作的气势与决心。
城市画卷展开之后,上海弄堂中小市民的女儿王琦瑶,一个仿佛自张爱玲文学世界中漫步而出的倾城美人,才正式出场。王琦瑶初时只是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女学生,后来通过同学引介才慢慢进入社交界,引起众人的注目。
作者通过拍电影和拍照等情节有层次地将王琦瑶独特的美丽气质一层层地烘托展现,既让她渐渐显露出的光彩映入众人眼中,又为她接下来当选上海小姐一朝成名做铺垫,使她年纪轻轻便达到人生的顶峰,为而后遭逢大变埋下伏笔,个人的悲剧才就此展开。
在大变故之后,王琦瑶重新回到弄堂之中,命运注定天生丽质的她生活无法平静,一个又一个欣赏爱慕她的人物进入她的生命,挑动往昔的幽梦与情欲,不久都缘尽离去,且大多一去不回。她被动地居于弄堂的一隅,对感情看破却无法看透,对一段段缘分欲拒还迎,不舍放手,最后心灰意冷,遭逢厄运,落得美玉磕碎在瓦当的悲剧下场。
小说《长恨歌》发展按照时间的顺序,个人命运的悲歌和着时代变迁的奏鸣曲,弄堂里飘动旧时代典雅浮华的气息,小说线性叙述的章节结构十分清晰。
《长恨歌》中的关于时代和城市的描述是从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进行的,带有一种不可质疑的宏大叙事语气,而对主要人物王琦瑶却是张爱玲式女性视角叙述,一种敏锐纤细的感性叙事,藏身于深巷旧时光中的美人形象与时代变迁下的城市象征之间存在“契合度”的问题,以至于小说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的结合出现裂隙。
叙事方式更复杂
相比之下,小说《儿女风云录》的叙事方式有着很大的变化,它非是按照时代变化的时间线,而是使用一种复杂的叙事方式,非线性的,打乱时空,从多个视角以不同的方式转换,这是现代小说的写法。
《儿女风云录》故事线索不止一条,除了主要人物的故事线,还有次要的人物的故事线,主要人物的视角,次要人物的视角,以及叙述者的视角,不同线索与视角交织,艺术品般的精巧结构。城市的景观,生活的气息,人物的命运,巧妙地配合在一起,让小说有了丰富立体的层次感。
《儿女风云录》不再出现长篇大论似的宏大叙事,作者将它们切割成碎片,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更为巧妙的结合起来,如地砖与缝隙之间的镶边,完成这项高难度工作的,则是小说中的叙述者。
小说的行进在不同时空闪回、跳转,可读起来并不感烦乱。在时空切换时,王安忆巧妙地使用了叙述者说书人的口吻,她说家常般谈论瑟,谈论身边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似的,说起他工作、生活、家人和朋友,话题围绕着熟人的生活转,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变故,切换便顺滑而自然起来,不会有突兀与割裂之感,更巧妙地避开了小说中第三人称人物受限视角的难题。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对主要人物形象设计之精巧,是《长恨歌》所不曾见的。
比如血统,瑟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的,他的亲生父母却是道地的上海人,他们的相像是隐秘的。这种外国基因外显的情况听起来不可思议,可在人口迁徙流动大,血缘混交,遗传纷杂的沿海地区,是可能的。
在上海,这个中西交融、文化自成一家的地方,这样形容体貌非我族类的人物才能得到更宽容的接纳,找到适合他的生长空间。当然,能够容纳瑟的地方,自然是上海的弄堂。
再比如姓名,作者巧妙利用双关给主要人物瑟取名,瑟通英文sir,暗喻了他外国血缘与受人尊敬的身份;同时,瑟也是古代类似古筝的乐器(《锦瑟》李商隐),暗示了瑟与生俱来的那种纯真、不谙世事的艺术家气质,而他的全名卢瑟通英文的loser,又在暗示读者,他人眼中高高在上的老法师,或许是生活上一个废柴般的失败者。
从种种细节可以看出作者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塑造,这样的人物能显现一种效果:人物的个体形象,个人的遭遇与其所生活的环境,环境在时代中的变化,是契合的,能引发共鸣的。
灵魂人物美玉光彩
两部小说中的灵魂人物王琦瑶和瑟,在各自的生活中散发出美的光彩,代表着上海文化中所孕育的两种极致的可能性。
王琦瑶是旧上海繁华世界所遗落下的一块美玉,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她和身边的人(多是当年的中产)栖身于弄堂,那里收纳旧日的时光与幻梦,让人虚实难分,望见她的容颜仪态,人们仿佛望见了昔日繁华气象。
瑟出身破落的中产家庭,生活市井之中,却未染上铜臭与俗气。他相貌虽像外国人,形象与气质更让人想到古典文学中玉树临风的贵公子,落了难,对人生的牵挂变得淡然,不谙世事,却遇到有情有义的小市民(阿郭、阿陆头)相助,屡屡渡过难关,让他有勇气在俗世红尘中前行。
瑶与瑟这两个人物的身上,从他们的性情与灵魂中,还可看到王安忆另一脉文学传承,那便是张爱玲的小说,及对张有很大影响的《红楼梦》。
他们生于市井弄堂之中,没有对权力与物质的雄心壮志,对生活保持一丝清醒与淡然,窥见了生命的虚无,却又不至于跳脱红尘,大彻大悟。
这就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