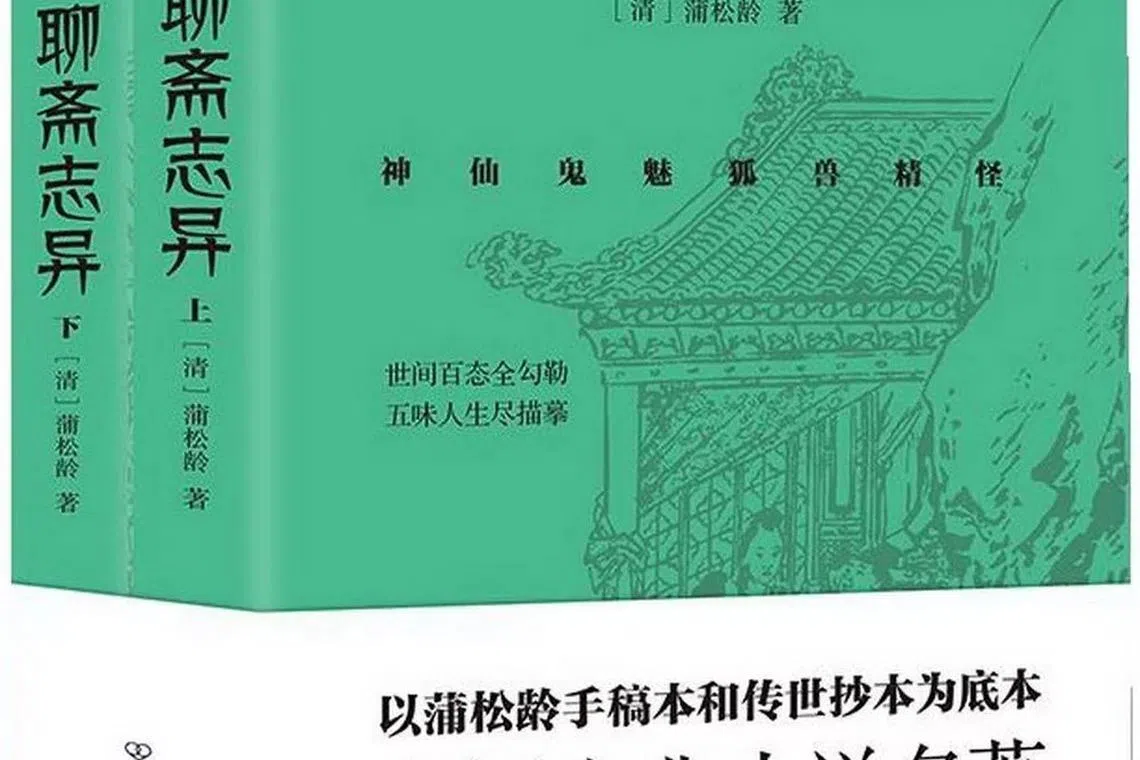经典永不过时,只会以新的方式重生,因经典故事的价值在于其跨越时空的永恒普世价值,能使不同时代的读者受益。中国古典文学历经千百年沉淀,如今在艺术舞台上绽放出别样光彩——当古老语词化作跃动音符,当无声文本被赋予新活演绎,人们听到看到的不仅是艺术瑰宝的传承,更是文化神髓的延续。那些被改编为舞台、音乐的名著片段,以独特方式诉说传统与时代的对话,体现古典文学的璀璨生命力。
本文撷取三部中国古典名著中的片段,探寻它们从书页到舞台、流行音乐等现代艺文媒介的蜕变,在老故事中挖掘新意义。
昆曲《驴鸣》:大哉生死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原创昆曲《世说新语》之“大哉生死”系列,2025年开启新一轮巡演,由《驴鸣》《索衣》《开匣》《访戴》四折缀连而成,取材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展示魏晋名士风度与情感,探讨魏晋世人“死生亦大矣”的生命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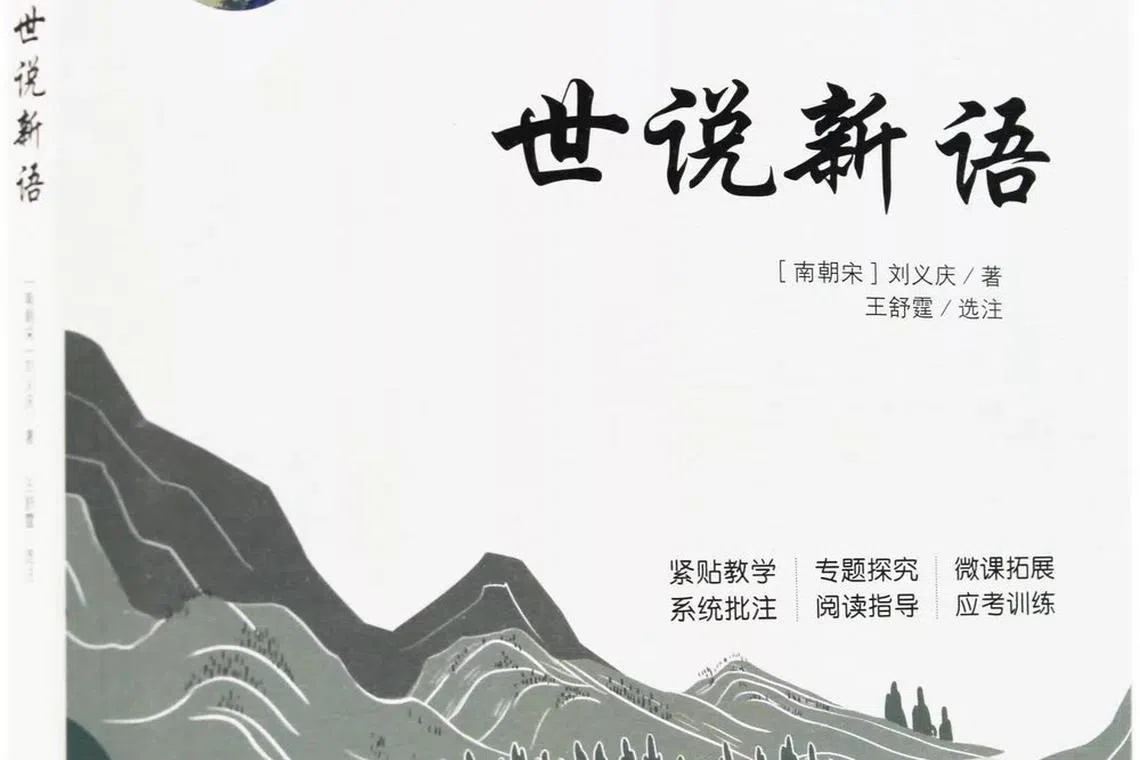
四个故事中,有评论认为取材自《世说新语·伤逝》的《驴鸣》,作为“大哉生死”主题代表作,将三十几个字的简短记载转化为一场充满戏剧张力与人文深度的演绎,成功重构并新解。
原文如斯简练:“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改编后,《驴鸣》对整个故事有了拓展:王粲逝后,好友曹丕、曹植前往致祭。谋士贾诩奉曹操之命,窥探二人高下,决定谁有资格继位。得曹操喜爱的幼子曹植风流机智善于应对,几番交锋后曹丕相形见绌,可出乎贾诩与曹植意外的是,因王粲生前最爱听驴叫声,曹丕最后甘愿放下身段、不顾姿态,跪地模仿驴鸣,竟哀鸣出一番情真意切。
笔者看来,曹丕这一声声驴鸣,祭奠的不仅是老友,其实也是自己,还有兄弟之情,甚至是逼迫他们骨肉相残的父亲。曹丕躬身为驴,又在驴鸣中化人,昭示最纯粹最可贵的人性,并试图点醒那些听不懂驴鸣的人,包括曹植。曹丕说:“此粗鄙之声,实不该出曹丕之口,更不可出世子之口,尤不可出来日魏王之口,是也不是?”
更耐人寻味的是,以王粲最爱的驴叫相祭之际,曹丕问曹植:“敢问子建(曹植)可知我之所好?”胜负欲极强的曹植并不老实回答,处处反诘,曹丕伏在曹植耳边说:“我所爱者,甘蔗与葡萄耳。”意思是说:“日后祭奠我时记得带甘蔗与葡萄……”曹丕此言为感化,还是戏弄,甚至刺痛曹植,都任人解读。
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成为魏文帝的是曹丕。曹丕驴鸣是真情还是计谋,是豁达还是阴险,不得而知。从史书包括曹丕个人的著作中看,曹丕是一个既有情又毒辣,既宽厚又残酷的人,曹丕终究未对曹植下手,若《世说新语》所记为实,那么曹丕可能记得驴鸣和耳语,对自己、对弟弟的内心震撼。
但有史学家指,《世说新语》属志人小说范畴,事实真伪并不可靠,而现代戏剧构作并不拘囿于探真,将小故事加工提炼出令今人共感反思的新作,这已是高妙解读。
舞剧《山月》:心理异变人化虎
同样是人与动物的类比,2023年受“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郑杰舞蹈剧场创作的舞蹈剧场《训诫三则·山月》,取材自张读所撰晚唐传奇《人虎传》。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作家中岛敦的《山月记》也扩写自李征化虎的故事。
青年才俊李征高中进士后,因性格清高,不愿屈就低职而辞官回乡,生活所迫又无奈出任地方小官,倍感压抑的他突发疾病发疯,化作一头老虎遁入森林。化虎的他仍然保持人性,托付友人袁傪代为照顾妻儿,并把自己的诗传承给子孙。这个故事直诉许多唐朝文人怀才不遇、仕隐之心,探讨的是人性与命运、现实与理想的关联,如果与现代人的思维相证,还有对自我意识过剩与自我认知失调的指涉,李征“突发狂疾”,甚至可视为心理疾病所致。
《山月》编舞、导演与主演郑杰认为,古传奇警训着今人的可为与不可为,他以小人物的背景和经历而提炼出一个巨大的中式哲学思想。他受访时说:“我觉得现代人追求对自我内心的观察和满足,人的匮乏之处表现于依然会问自己:‘我是谁’‘我如何遵循自己内心真实的一面去做自己?’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很好理解,但设问确实可起到警醒作用。”
如李征般个体的求而不得,无论古今,都是一种普遍心灵困境或性格悲剧,意识到它的本源存在只是起始,人化虎虽为文学处理,可心理产生异变,现实中却并不罕见,因此直面疑难并与之和解,甚至消解,才是经典阅读或任何阅读后最重要的接续动作。
中岛敦在《山月记》中借李征之口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徐建雄译)
人与虎、玉与砾,或许原非二元对立,这跟认命和破命是同样道理:人,既要审时度势机宜权衡,也得锲而不舍上下求索;另外,如无法撼动大局,改变情势,至少可以尝试改变自己,允许心灵在沉寂中蓄力,等待或另觅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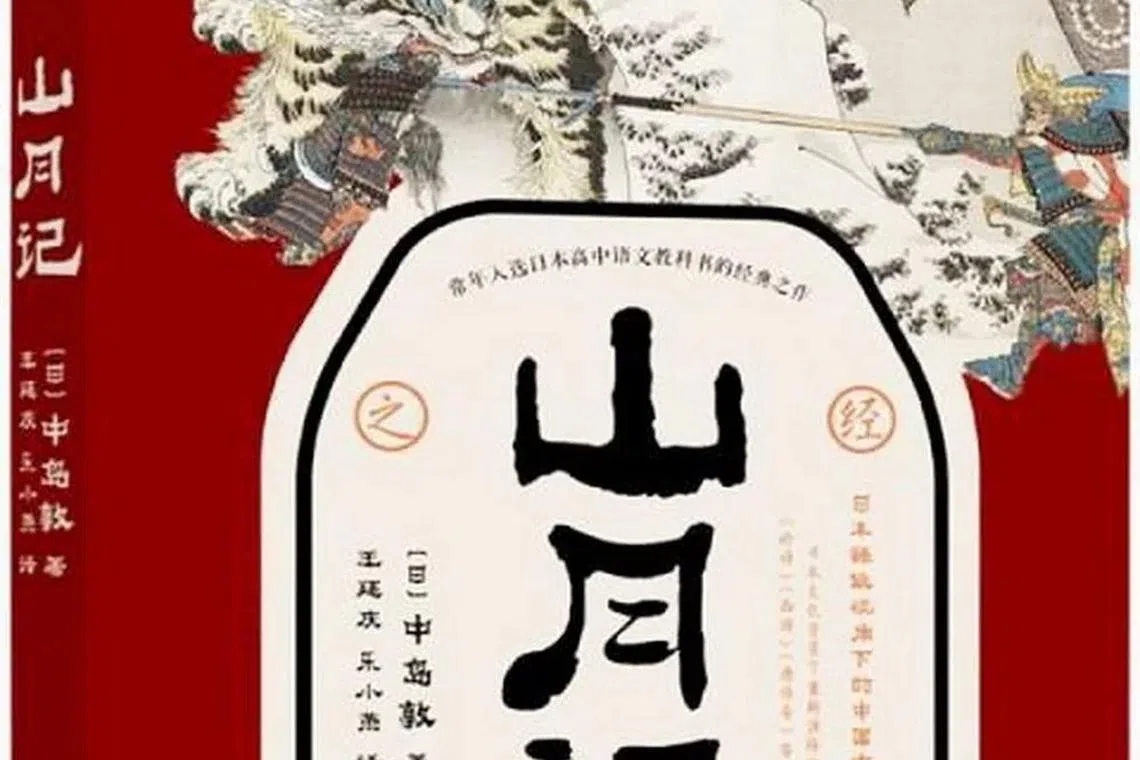
聊斋《翩翩》“戏腔”翻唱
说到沉寂蓄力,不得不提暌违公众视线已久的刀郎,2023年携专辑《山歌寥哉》归来,专辑此刻仍话题热度不坠,被不断探讨和翻唱。专辑创作底色为对山歌和民间曲牌的讴咏,并且是一张聊斋概念的作品,连辑名“寥哉”都是“聊斋”谐音,所有歌曲的歌名和歌词大多取材蒲松龄文本。
最近中国甬剧演员、宁波市甬剧团副团长苏醒对《山歌寥哉》中一首《翩翩》的“戏腔”翻唱,令这首歌翩然飘散又一层古色古香的韵味。
聊斋《翩翩》讲述浪荡子罗子浮身染恶疮,被仙女翩翩领入深山洞府治愈,后返回尘世探亲,重寻山洞,却已不见翩翩和温柔乡踪影。
刀郎在歌词中重述《翩翩》:“她也曾是越过了银河万里的荒原/他也曾是划破了绚烂流落在人间/唯有那不眠的凭栏与情仇依舍/是云摇是雨散都在同一个摇篮。”笔者认为,这几句歌词是对原著既诗意又哲学的解读:仙子凡人结缡,毕竟无以偕老;攀临空中楼阁,终将人间流离。望眼欲穿凭栏无尽,只剩难分难舍的情思可依;云摇雨散往复循环,诞生总与轮回一同发生。
词藻间似乎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荒诞,但若说《翩翩》意在劝诫世人否定世俗意义,免于尘世痴缠,恐怕亦不尽然,倒不如说给了虚无主义者一剂良方:以“翩翩”之姿,在虚实间寻找兴味、创造意义。
经典如同涌动之河,新解是活水长流的必要支流。古典文学解读,应既揭示普遍人性价值,又燃亮其不可复制的历史光彩,这种张力恰恰是人文精神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