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猛暑的日子里到大阪和京都旅游,或许不会是很多人的首选吧?“猛暑日”是个日本气象厅从2007年起就采用的气象新名词,特指单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的极端高温天气。记得毛丹青老师在他的随笔集《感悟日本》一书中,谈到大阪人时曾说:“根据《国际交通安全学会》的报告,整个日本唯有大阪人的步行速度最快,每秒速度达1.6米,东京1.56米,屈居第二位。”当时的天气,是否已经属于猛暑日,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那是2008年他在文中的描述和感悟,转眼间那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
毛老师后来还有《狂走日本》的新作,书中的第二章“文事清流003”里,曾提及川端康成先生和大画家东山魁夷有很深厚的交谊。好几年前,我在长野旅游时曾机缘巧合地去了善光寺附近的城山公园,还参观了公园一隅的东山魁夷馆,看到东山魁夷的《白马之森》《夕静寂》以及夏普AQUOS的电视广告节目中使用的《绿响》等代表作。后来,每次到关西旅行都会途经大阪,但多为短暂逗留,京都才是想去的目的地。如今大阪人和外国游客在酷暑似火的2025世博热潮里,会否步伐走得更快、更匆忙,但上班族更渴望的或许是能早点躲进冷气办公大楼里和闪入舒服凉快的购物中心吧?
去箕面瀑布健行的那天早上,气温尚未高达35度,从箕面站虽然得步行大约2.6公里、40分钟才能到达瀑布,但仍不失为一趟体味绿水青山的逸乐之行,因为快慢徐疾,全由自己拿捏。次日一早,云天朗朗,思绪仍沉浸在前一天愉悦的瀑布之旅。从茨木市JR总持寺站北口出来后,一路上见到的行人都没有大阪市那样的行色匆匆。那些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步道上的男女老少,远远看到我们两老时都主动放慢了车速,大家“礼尚往来”地共用着行人步道。走过一爿小超市(FamilyMart)的门前后,慢慢爬上了一个小斜坡。哦,原来是上了一座叫西河原新桥。桥下流水潺潺,有条叫安威川的河川,谷歌地图上标示的洋名是“Ai River”,听起来更讨人喜欢。如若译成“爱河”,岂不更能增添几分浪漫的诗情画意?

瞧,铁道旁和行人步道之间围起来的那块小小田地里,串串翠绿的稻穗已经靓丽初长成,若无台风登陆的肆虐和摧残,秋收时的金黄应该不算是“人间的奢望”吧?不禁想,儿时的川端康成,他上学途中可曾因为稻穗金黄随风摇,而驻足凝视了好一阵子才离去呢?他应该也有要好的童年友伴吧?1906年,七岁的川端就读于丰川寻常小学,即现在茨木市立丰川小学校。那年的九月,川端的祖母撒手人寰后,他就和爷爷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了。

慢步前行,过了桥来到十字路口前,那间历史悠久的豆腐店——伏见屋,已在视线范围内了。阳光融融,过了红绿灯后,看到前方两层楼的伏见屋工场前,停了好几辆取货的营销车。隔邻的门市店还未开门营业,但侧面的木板墙上那块白底黑字、像颗大蚕豆的招牌上“伏见屋”三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透出几分艺匠之气,墙下还摆放了两张长椅供人歇息。在伏见屋的拐角处左转后朝前走,不远处有条短短的小隧道,头顶上其实就是火车穿越的铁轨桥。出了隧道来到前面不远的分叉路口右拐,是一条绿荫夹道、舒坦笔直的红砖步道。哦,川端康成文学馆,已经近在咫尺了……

踏进文学馆后,察觉里头恰好正在举办“川端康成の小中学校時代”的主题展,但馆里并无其他访客。接待处的女士一见到我们,脸上露出了笑容,起身欢迎我们的到访,并递上文学馆的介绍小册子。从她胸口挂着的名牌得知她是小林女士。她礼貌地提醒我们馆内不能拍照或录像,但又补上一句说等会儿我们参观完后,她会过来打开川端先生的书斋,让我们进去拍照留念。我不禁感到有点纳罕和惊讶,怎么反倒是在先生的书斋可以进去摆拍存照。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两岁多时就因父母相继去世而成了孤儿的川端康成,他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他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在他跨进了文学艺术的最高殿堂后,又为何选择了自杀。
随着指示顺路参观,发觉馆里还收藏了川端的父亲荣吉先生的照片和资料。哦,是位文质彬彬且对汉诗文和文人画有着浓厚兴趣的开业医生。可叹的是,川端两岁时,父亲就因结核病而离世,如此想来,他对父亲的印象,应该是模糊又朦胧的吧?展出的文物里,还包括川端小学生时练写过的字、誊清本子、日记、手稿和信件等。倏地,忆起自己当年在会馆承办的小学校念书时,每周也得写大小楷的作业。当时念高年级的二姐每次见我写得愁眉苦脸、“一塌糊涂”时,总会及时给我鼓励和示范,说写字要用心,握笔要专注,沉住气地不要胡思乱想。如今那所位于克里门梭路的小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二姐也已离开人世好几年了。
世事无常,当悉心照顾川端的祖母离世后,只剩下他和患眼疾的祖父相依为命,想必先生的童年或是颇为孤独和寂寞的吧?但或也未必如此,你看,他在《故园》文中就道出他有过的欢愉时刻,“小学时代,我几乎每天都在院子里的木斛树上看书。祖父最喜欢院子里的老松树,其次就是这棵老木斛树……盛夏时的午觉,要数院子里那棵硕大的榉树下的阴凉处最舒服……”这些描述,让我忆起了儿时住过的亚答屋,屋前有棵高高的菠萝蜜树,炎炎夏日,抬头望着硕果累累,听着阵阵蝉鸣,那不也是我儿时的乐趣?如今这些都已成了褪色的记忆……
参观了几个展示橱窗后,小林女士也正好拎着钥匙走过来。帮我们开了那个复制和重现了川端先生寓居镰仓时的书斋后,还给了我一张文学馆特制的大稿纸,说是可以用钢笔在稿纸上书写,体会一下当作家的感觉。进入那颇为逼仄的书斋后,我端坐案前,摊开了稿纸,脑袋里浮现出许多陈年旧事,而近日来踟蹰与探问的步履,就如同电影画面般串流过一个又一个的空格子。但我终究决定就让那张稿纸留白,毕竟自己已来到了杜甫在《曲江二首》所言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又何求绚丽多彩的记忆呢?哦,就在我沉思冥想的瞬间,老伴或已用手机给我立此存照了,但这并非我此来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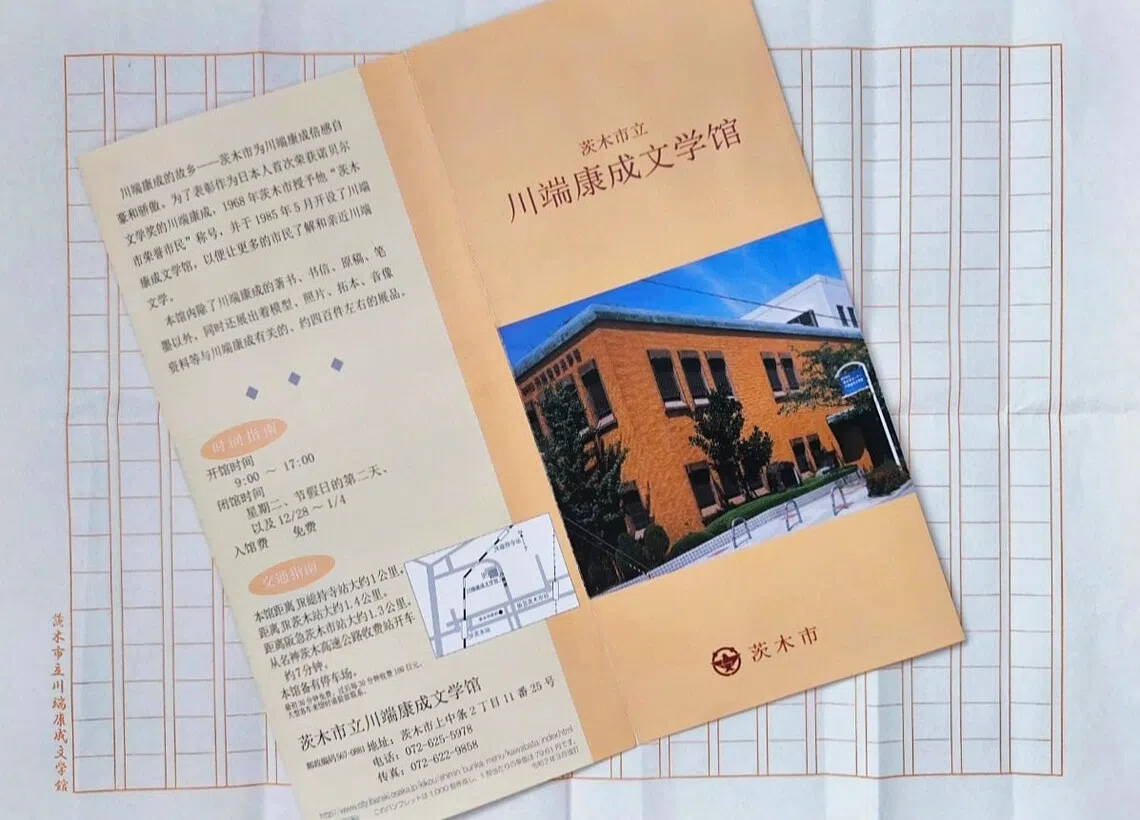
出了书斋,来到柜台附近,见小桌上摆放不少川端先生的名著,如《伊豆舞女》《雪国》《古都》《千羽鹤》等,就是没看到他在战后1948和49年间发表的短篇小说《反桥》《しぐれ》(时雨)、《住吉》等合编的小集子。请小林女士帮忙查找了电脑库存资料后,确定文学馆没有收藏和贩卖这本小集子。但她信心满满地说或许到大阪和梅田的大书店或古书屋探问,应该会有库存或新刊印。离开了文学馆,走在行人稀疏的小路上,路边的行道树既不是木斛树也没有老松树,而是翠绿宜人的日本扁柏。就在那青葱飘逸的枝叶间,有许多状似小星星的白色小花,朵朵紧密相依地绽放着。白灿灿的小星星,犹如一个个引人遐想的小说物语,也似乎在提醒我们要抓紧时间,早点走进川端《反桥》的文本和场景里。

斜阳灼灼,从古趣盎然的阪堺路面电车出站后,过了马路就是住吉大社的入口了。漫步来到住吉大社的反桥(太鼓桥)前,见桥下有条潺潺小河流过,似乎为我们匆匆的步履,频添了几分的惬意。绕到稍远的另一座石桥上,眺望这著名的“反桥”在水中清晰如画的倒影,想起川端先生在这篇同名的小说里,描述了他大约是5岁时,母亲曾带他来到住吉大社参拜。那高高拱起犹如一个陡坡的太鼓桥,似乎笼罩且逼迫着他小小的心灵。当时,母亲以比平时更温柔和慰藉的口吻对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一定能放心走过大桥。如果你跨过了这座桥,我就告诉你一桩极其重要的事。年幼的川端当时问道,是个哀伤的故事吗?嗯,嗯,是哀伤又悲凉的事。后来他终于站在高高的桥顶上,觉得反桥并不可怕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可是,母亲接着就告诉他,她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是她姐姐的孩子,而他的生母已离开了人世间……
入夜之后 ,我终于在阪急三番街的纪伊国屋书店的梅田本店,买到那本川端的短篇集子,是讲谈社文芸文库今年4月11日再版发行的第13刷。翻开了集子,排在前面的三篇是《反桥》《しぐれ》和《住吉》,发觉每一篇的开头和结尾,川端先生都问了相同的一句话:“你在哪里呢?”(あなたはどこにおいでなのでしょうか)。嗯,嗯,这是经历了战败后的川端先生,在目睹了周遭凋敝不堪的市井人间时,对未来曾有过的迷茫与失落,更对亲生母亲愈发思念而发出的悲凉和绝望的探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