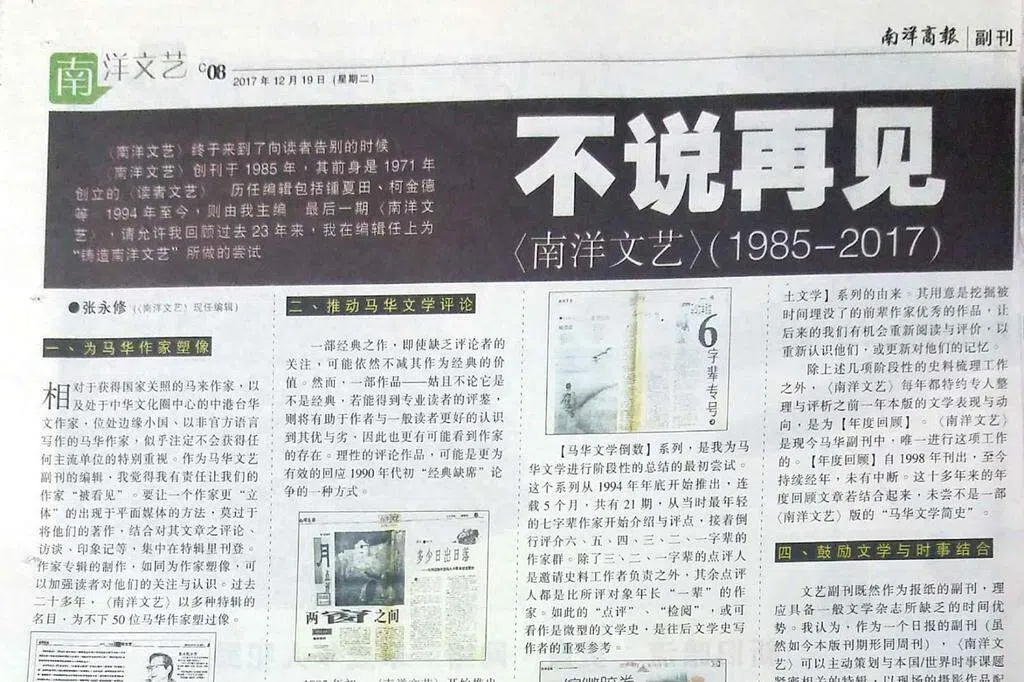2023年,本报曾发问:“新马华文副刊还有影响力吗?”结论是副刊与华文写作社群“唇亡齿寒”,仍发挥文化传承的余热。
两年过去,《联合早报》副刊主任胡文雁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教部主任曾翎龙,齐聚新加坡作家节,共话新马华文副刊与华文文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给出资深报人的现场观察。
从抗战副刊到大副刊
要读懂副刊的今天,需要看清它的来路。
胡文雁为早报读者爬梳副刊的三次角色转换:“战前至新加坡独立前,比如郁达夫主持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承载着南来文人的文化使命;新加坡独立后至80年代,副刊转向建构本土认同,推动‘侨民文学’向‘在地文学’的蜕变;而今天,副刊已从纯文艺阵地,扩展为涵盖生活各面向的‘大副刊’。”
但文艺板块仍然坚守岗位。胡文雁指出,过去10年,《联合早报·副刊》平均每年刊登四百多篇作品,诗歌最多,其次是散文、小说。疫情两年甚至催生了值得讨论的“抗疫文学”。
曾翎龙也回应“大副刊”的概念,并认为在新闻时效性被网络超越的今天,副刊反而变得更重要。他透露,“副刊的独特性和自由度,让它能做更深度的报道和专题,成为真正的‘生活指南’。”
副刊为华文文学保留重要版图
翻开新马华文报业史,《联合早报》和《星洲日报》本是一家人。历经新马分家和报界震荡,1983年,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成为《联合早报》。两份报纸如今在各自的土地上,为华文文学保留着重要版图。
《联合早报》至今保持每周两大版《文艺城》,一版介绍文学作品、报道作家动态的《阅读》,以及物色选刊名家文章的《名采》、发表专栏文章的《四方八面》等“文艺版”。胡文雁形容这份资源投入,“比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报章,仍是一面高举的旗帜。”
《星洲日报》则是每周两版《文艺春秋》,一版《读家》,大众读者投稿园地《星云版》,更是每周发布六天。除了维护作品发表的平台,两份报纸也都积极推广华文文学,关注年轻世代的华文阅读。
早报前后出版了10本《文字现象》,举办了多届书选,并投入资源培养年轻写作族群“字食族”,协办大专文学奖。早报文学节并与华文媒体集团举办的阅读节合并,以便让文学和阅读能够更深入人心。
星洲创办花踪文学奖,建构校园文学系统如《小星星》《星星学堂》《学海》,协办仁华大专文学奖,更与马来西亚作家协会合作推出“好读马华”版位,供华文教师作教材使用。
面临新时代三重挑战
然而,副刊仍面临新时代考验。曾翎龙兼营有人出版社二十余年,他从媒体与出版双重视角,分析文学作品遇到的挑战:一是碎片化阅读,读者转向荧屏手机,深度文本被视频肢解;二是购买方式迁移,疫情后更多人网络购书。
《星洲日报》的应对策略是“两条腿走路”:纸媒与电子报、网络经营并行。《联合早报》则推出《开卷》播客,经由赏析和作家上节目访谈,让文学进入有声的多元媒介。
另一个变量则是AI技术突飞猛进。
曾翎龙现阶段拒收AI稿件,他提出,作为创作者,AI代笔违背写作本意,但作为读者,“AI作品如果能引发同等共鸣,阅读的目的就已经达成”。因此,编辑的当下使命是,尽力确保每篇刊登作品胜过AI。
未来合作推动新马文学发展
今年,两报合作在花踪文学奖设立微型小说奖。曾翎龙考量到,微型小说篇幅短,易推广,两地均有专精作家与文学资源,是理想切入点。

胡文雁希望两报接下来有更多合作,一起推动新马文学发展。她坦言,如今文学发表园地已多元,不限于报章,但早报仍在发挥余力,如与阅文集团合作“全球华文小说创作大赛”,将文学辐射东南亚乃至全球。
谈起未来,曾翎龙认为现在的星洲已经接近理想状态,但他仍憧憬最具影响力的副刊,每天推荐一物——书、影、歌、地、人,读者信任“这肯定是好东西”,副刊发挥绝对文化领导力。胡文雁则在思考副刊可以如何跟上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之余,坚持人文品格,发挥自身特色和价值,更好地和新闻配合,做到新闻招客,副刊留客。
▲新马华文副刊与文学的共生关系
主讲人:胡文雁、曾翎龙
主持人:曾昭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时间:11月8日(星期六)傍晚7时至8时30分
地点: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
报名链接:bit.ly/4hLwy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