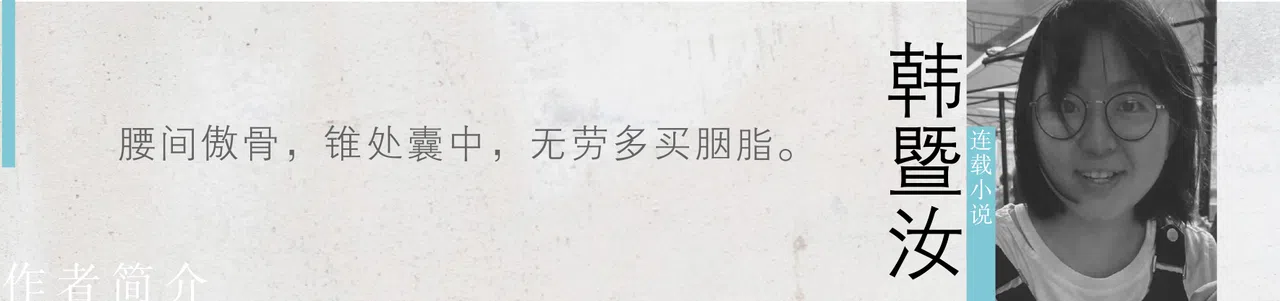故事简介:大约几万或十几万年以后,世界依旧被化分成许许多多个小个体,那怎么会没有流血漂橹、兵戈扰攘呢?高树所生活的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的腐败与权力争夺的混乱,外敌入侵时求生存的抵抗。而他所处其中,自然有了许多思考,也难免面临着种种艰难的选择,比如沉默或是反抗,适应或是改变,生或是死。有时他希望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局面,追求他心中最理想的社会;有时他又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他是太过渺小的存在。你权当在哪里拾到了他的日记,看看他的一生。
(十七)
从没有过感情上的造诣,这也怪不得他了。尤其是战事吃紧的那几年,也就是他刚刚调回去的时候。事实上,外敌的步步紧逼很早就有苗头了,再往北些,更加民不聊生,只是上面要求绥靖,他虽存疑,但断然不会公然反驳,如今却已到了不得不反抗的田地了。古往今来,外患似乎总能将涣散人心凝起来,使得人人都深觉此事与自身息息相关。
岌岌可危的经济、频频失守的驻地、纷至沓来的轰炸自不必说,单是偶尔几声枪声炮火都叫人心惶惶。有位理论家曾经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既然如此,政治上的洽谈可否避免战争的发生?如果两国政治的罅隙延伸成鸿沟,那么战争是否又是不可挽回的必然?
高树若是能给自身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便不是他了。他也无暇去想了。他着重分析了失守的几个原因,器械与训练不能与时俱进,敌众我寡须得逐步整调,军队的地方性意味着士气极大程度上倚靠长官个人的调动,而非为了整体的、家国的概念。对于这一点,他能做的只有尽力宣传“必死之决心”,不过后来苏州河一带的战事之悲壮的确使得本来涣散的人心变得更为紧凑,外患面前,人们对于“内团体”的观念不再是地域性的,而转为更宏大的意义,可是这些爱国忧民之情感能切实转化成行动吗?多半会的?面对逃兵问题,他也踟蹰着,到底应该严苛地处置,还是应该体恤个人的难言之隐。最终他还是根据上面的指向,效仿破釜沉舟的气节,于是枪毙逃兵成了几日便上演一次的戏码,但是他鲜少亲自动手,仿佛这样便可以减少深重的罪孽。
临近的驻地在立冬前后还是失守了。上面竟然亲自从南边赶来,照例开了会,讲了些’“不可拥兵自重”的话,处决了擅自撤退的将领,又匆匆地走了。
高树的脸上竟也添上了些忧愁的神色了。有一次,他与陈桐城在路上相遇,会议前日刚刚终了。高树打趣地说道:“好久不见。” 两人的距离明明很近,却无暇时常说话了。
陈桐城笑着点头,似乎感受到了他郁结的情绪,问道:“最近休息不好?”
高树休息尚佳,仍做扼腕叹息状,半开玩笑地回答:“自然是‘惟将终夜长开眼’了!”
再过半年,他又问他这句话。这次他却是真的夜不能寐了。
邻省的驻地接连失守,敌人南下的势头愈发强劲。对于高树而言,这几乎是危急存亡的关头了。 早在春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炸毁堤坝,以水的滔滔之势来阻断交通枢纽,使敌人隔绝在外。自然有人觉着不可行,水火无情,又不能专淹对方,那么沿河必定民不聊生,疏散百姓又势必是个大工程,炸哪处堤坝本身亦是难以断绝之事。商量了不足两月,本省的城也失守了。
(每星期五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