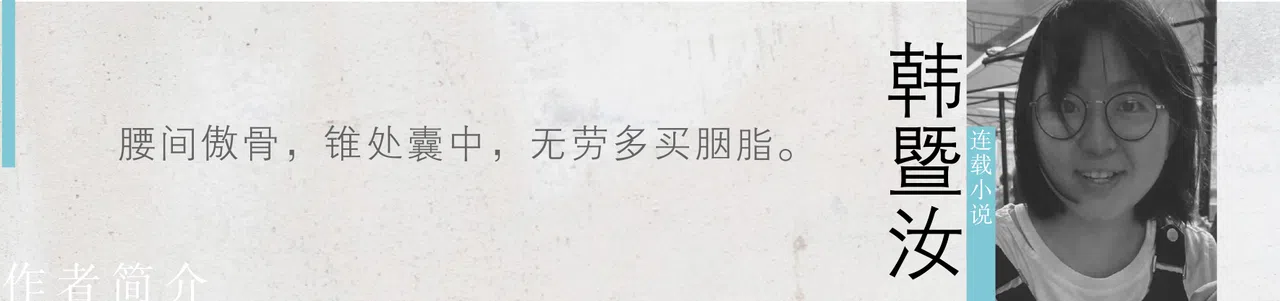故事简介:大约几万或十几万年以后,世界依旧被化分成许许多多个小个体,那怎么会没有流血漂橹、兵戈扰攘呢?高树所生活的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的腐败与权力争夺的混乱,外敌入侵时求生存的抵抗。而他所处其中,自然有了许多思考,也难免面临着种种艰难的选择,比如沉默或是反抗,适应或是改变,生或是死。有时他希望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局面,追求他心中最理想的社会;有时他又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他是太过渺小的存在。你权当在哪里拾到了他的日记,看看他的一生。
(十八)
当上面真匆匆发来炸毁桓河支流堤坝的指令,高树感到了平静的震恸。他先去见了自己的师长。
“这样做,余心中有愧,恐怕百姓……”
师长打断他:“你以为只有你忧心民生,其他人都蠢,都是些王八蛋?”
高树叫人反将一军,愣了半晌,方才说:“王八蛋不王八蛋的,百姓叫水淹了,怨声载道,咱们就都得是王八蛋,到时候外患没解决,内忧倒先来了——里外不是人!”
师长嫌他不开窍似地睨他一眼:“哪个说是我们炸的?是敌人炸的!真是些王八蛋!”
高树欲拍案而起,但悬崖勒马,强笑了笑,转身走了。他与这位师长并不相熟,本来应当是他的位子,现在却叫这人捷足先登,他本身就有些怨恨,以至于不屑与之争执了。
以他一贯的性格,事已至此,是放弃的号角与笙歌了。他顶多写一篇檄文抨击之。你若在时间的河流里将自己放得无限小,那么顺水而行,所有不平事终归会过去的。
回去的路上,他又与陈桐城迎着走,两个人仍旧打了照面。陈桐城忽然问他:“最近休息不好?”一样的神情,相同的问题,让他几乎有些恍惚了。
他应付般地答着“尚好”,即将与他擦肩而过时,他忽然想,若是自身再一次避而不谈,会否今后都睡不安稳了?他觉着自己是深陷在淤滩里的船,将纤绳深深刻痕在纤夫的肩膀上,方可逃离深渊的泥泞。
“决堤一事,你想必听说了……你怎么想?”高树忽然转过身。
“我自然是反对。”陈桐城也停下来,没有躲闪地回应他。
高树本以为以他的性格,断然又要讲一些模棱两可之言,哪承想他竟直接予以回复。高树心底蓦然腾升起一丝希望,若是反对者积累至一定数量,恐怕可以使得上面幡然悔悟,或许还可效仿古人,写下篇《罪己诏》呢。他想,陈桐城反对之意如此明晰,想必赵远山一定也有此意,他有些讶异,不过这仍处于情理之中。
“他也这样想?”
陈桐城自然明晰高树所指,垂下头:“只是我这样想。”
高树认为,自己是赵远山旧部,虽在调回后许久不曾有私下的交集,却仍可以试着说服他,这样便得到了一位有力的同盟,下一步虽远不及如履平地,但容易不少。他刚在自己师长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如今却愈挫愈勇起来。
陈桐城首先进去,不知对赵远山说了些什么,又出来示意高树可以进了。
高树好久未和他单独坐着,仔细看看,他倒是没什么变化,似乎时间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从他生命经过。高树先讲了些天气、时局一类的事情意在寒暄,果然被他打断:“高副师长究竟想说什么?”
高树也正候着这句话,由此转向自己心中困惑之事,方才不显唐突:“河口决堤,实在荒唐。会否抵御外敌仍未可知;然民不聊生是必然发生之事。古人有鲧禹治水,十余载三过家门而不入,如今我们岂不是逆其道而行吗?”
赵远山或许早就预见到了他会如此想,平平静静地说道:“若是不这样做,就不会民不聊生了吗?你有什么双全法?”
高树预先想过这一问题,却仍是被他问住了,世间的确难寻双全法,若不这样做,敌人势如破竹,一路南下,不仅沿河一带民不聊生,更为重要的政治枢纽亦会受制于人,到时不真亡国了!亡了国,便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敌人以往屠城、烧杀抢掠之事不在少数。除非他有十足把握,不必决堤,亦能使敌人鸣金收兵。水患淹死病死几多人,更为直接的战乱又平添多少冤魂,欲判孰轻孰重,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