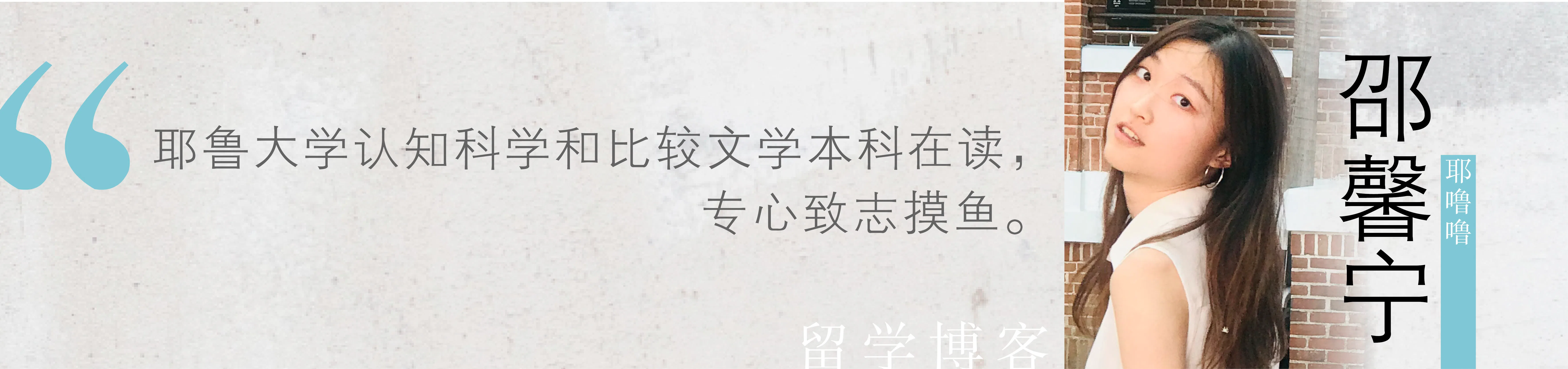我抱着一盆兰花,站在来旧金山所有人都会告诉你要避开的街区Tenderloin,等公交车。说不上怕还是不怕,毕竟因为计划失误,人已经在那里了。谷歌地图想让我体验一些真实的生活,我也没办法。目光范围内大概十几个或坐或躺或晃悠或发疯大叫唱歌的大哥们,没几个人注意到弱不禁风的我和弱不禁风的我的花。除了其中一个穿着荧光背心的大哥,看不出来他是某地工作人员,还是捡某地工作人员不要的背心,因为背心看起来像是有人穿着它在泥地里睡过觉的样子。他盯着我, 我盯着他。他咧嘴一笑,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朝我走过来,我无处可走。
我已经做好了打他一拳或者戳他眼睛或者立马把手机钱包,以及他想要的任何东西掏出来给他的准备。
他朝我伸出手说:“这花是给我的吧?”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像听不懂英语一样继续盯着他。可是他并没有更靠近我,或者做出其他任何动作的意思,只是伸着手,很无辜很期待地看着我。
最后我说:“啊,不好意思,不是。” 感觉自己像一个没接住梗的脱口秀演员。
他摆出一个很委屈的表情,走掉了。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大哥走过来,作势要接过我的花,说谢谢你哦谢谢你。有了刚才的经验,我朝他嘿嘿一笑,没给他。他也朝我嘿嘿一笑,也走掉了。后来我跟我妈说今天的遭遇,我妈说,这帮人还挺萌啊。
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不一样的美国街头大哥们。比如半夜和另外一个比我还弱不禁风的姐妹在街上走,街边躺着的大哥朝我们叽里咕噜地喊。街头躺着的大哥们似乎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因为我几乎永远听不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但这位大哥中间口齿忽然变清晰,他是在骂我们两个白人如何如何。单眼皮的我和我的单眼皮亚裔朋友对视一眼,我朋友耸耸肩说,天黑了,大哥眼神不大好。
比如在纽约地铁里,有大哥拎着一堆行李和一个巨大的音响,从站台边缘像走钢丝一样走过。我跟着音乐晃了两下,他转过头来,朝我端端正正地竖起了中指。
比如有本来在街边躺得好好的大哥,我们都以为他睡着了,结果我们路过的时候,他忽然跳起来指着我的新加坡华裔朋友说,滚回中国。朋友哭笑不得,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他解释说,你骂得不太对,但是也有点对。大哥此时已经一溜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有蹲在街边的大哥,和每个过路的人都说“good morning ma’am, good morning sir, have a good day ma’am, god bless you sir”。他一直仰着头、一直笑着,像个被人遗弃的小动物,面前也不摆收钱用的帽子或者纸盒子。有人回应他,多数人只是脚步匆匆走过,都似乎有点怕他。
有一天晚上8点多我打车回来,有一个人侧卧在已经拉了卷帘门的商店门口,头顶上一盏惨白的灯牌,只亮了一半。他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手却僵硬地撑在一边。只是车窗外一闪而过,我却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上一定有哪里很疼,非常疼,疼到看不见东西动也动不了,才会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另外一天晚上我也打车回来,车停在一个路口等红灯。路边的垃圾桶旁边,有一个人正不断地拾起地上的一坨什么东西,又马上再不断地把它狠狠摔到地上,仿佛自己手上沾了什么无比恶心的东西,每次丢出去他都踉跄着抡圆了胳膊、用着全身的力气。我看着那个长得像一只橙子的东西从圆到塌再到扁再到稀烂,绿灯,车开走了。
大家都说以后不要住在你现在的区域,离Tenderloin太近,我说确实,但是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能让我这么强烈地感觉到生命是一件多么神奇的、搞笑的、悲伤的事情。我刚搬进来的第一天,早上起床,一拉开窗帘发现对面楼下有个大哥横躺在人行道和马路的交界处,一条腿都搭在机动车道上,但他还完好无损。有人过去戳戳他,他动了一下,我松了口气。第二天,他还在。第三天,他还在。第四天,他不见了,我只希望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