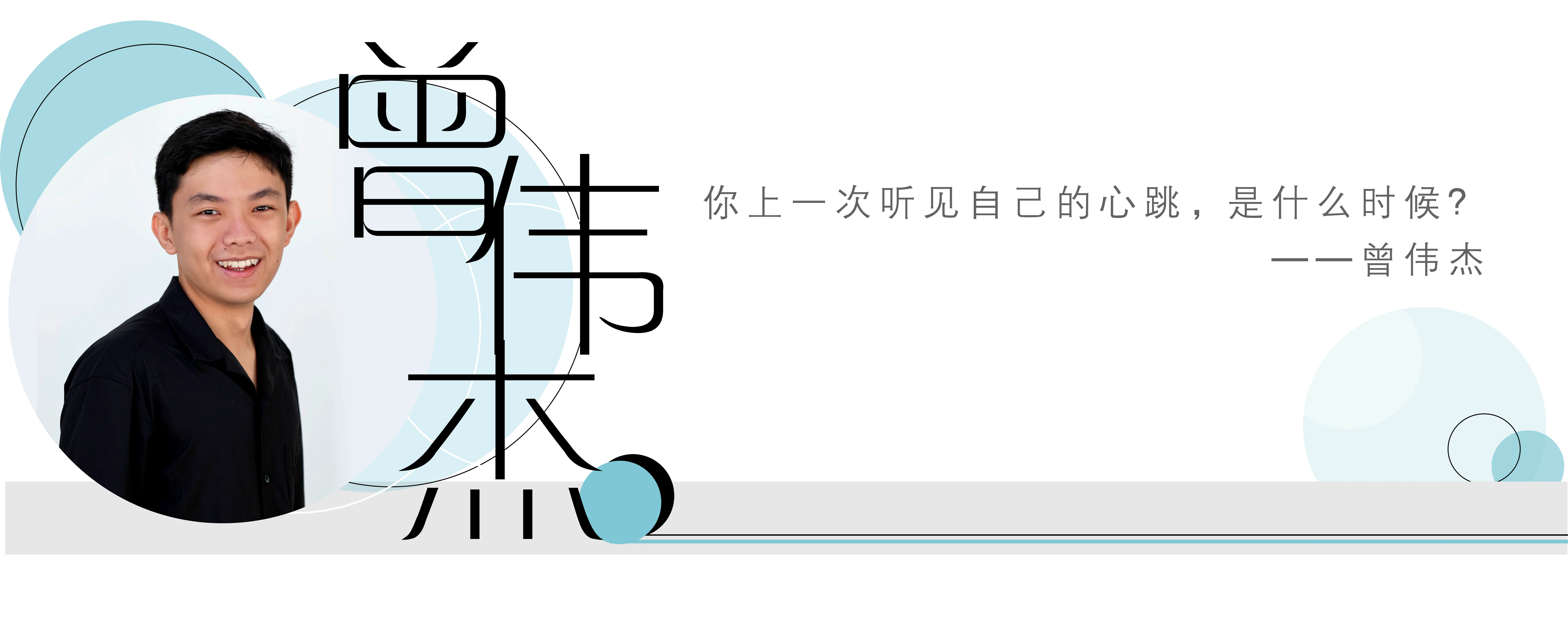空啤酒瓶静静地立在桌上,曾经覆盖瓶身的凝珠已顺着玻璃滑落,积在桌面,再流到桌沿,一滴一滴地,往地上滴落。
“先生,需要再来一瓶吗?”啤酒女问道。
男子的目光依旧停留在瓶子上,仿佛瓶子也在回望他,模糊的倒影隐约可见。
“先生?”
他摇了摇头,站起身,脚步有些踉跄,随后慢慢地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哐哧……哐哧……”
嘉乐从家乡到这座城市来,成功地在一家药品生产公司找了份工作,听起来挺高大上的一件事。但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却不过是在药水生产线的最前端,负责把新的空玻璃瓶从包装中拆开,然后拿起来对着头顶上的白炽灯检查是否有裂痕。如果玻璃瓶完好无损,他就把这些玻璃瓶放在一个旋转的大圆盘里。大圆盘上有一支金属杆,金属杆会把瓶子一个个引导到传输带上,传输带再将瓶子送到下一道生产环节去。
八个小时,至少八个小时。一星期六天,工资不过2000元多一点。
头顶的冷气出口呼呼地吹着,凉得彻骨。嘉乐的手指已被冻得麻木不堪,失去了知觉。有时候嘉乐会想象自己的手是一根精确而稳定的机械臂,不知疲倦地把玻璃瓶夹起、放下、夹起、放下……
“哐哧……哐哧……”
因为工作单调,嘉乐经常让自己的大脑飞转着。大圆盘上的玻璃瓶经过一番推挤,一个个便站到了传输带上。传输带上的玻璃瓶个个映照着嘉乐的脸庞,并且因为机器的震动,而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常常想象着这些玻璃瓶就是一个个的自己,那微微的颤抖看上去就像是走路时的身体起伏,而这些瓶子一直往前走着,一步一步地成为对人类有用的药品。
车间里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交流,工人们各自分布在生产线的不同环节,离嘉乐最近的同事少说也有10米远。玻璃瓶再往下会被机器贴上标签,灌装药水,然后封瓶。在这些不同岗位上,大家干的事其实都一样——把瑕疵品挑出来丢掉。
在车间里,每个人都戴着头套、口罩、手套和穿防尘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所有人看上去都差不多,连口罩的颜色都一模一样。但是,这层层防护下藏着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烦恼孩子教育的秀姐,爱钓鱼的老林,以及热衷赌马的黄叔。只要离开车间,同事们便会变得鲜活起来。
嘉乐发现,除了上班,自己在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哐哧……哐哧……”
偶尔,车间的主管会从他那小小的,用石膏板隔出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巡视一番。
每当面对着主管的注视,嘉乐的眼神总会不由自主地飘移。而今天,嘉乐瞟见了那些有了裂缝的,被自己搁在角落的玻璃瓶。
嘉乐突然发现,它们在灯光下竟也映照着自己的身影!
他赶忙把目光收回,继续把玻璃瓶夹起放下,夹起放下,不想去想自己刚刚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景象。
“哐哧……哐当!”
机器突然停了下来,车间里瞬间陷入死寂。嘉乐愣了几秒,手里还拿着三四个玻璃瓶。同事走上前拍了拍嘉乐的肩膀:“吃饭啦!”
他这才回过神来,放下手中的瓶子,跟着同事走出了车间。同事大约50多岁,平时是个话多的人,在工作时没人和他说话,所以每次休息时,他的嘴巴总是闲不下来。嘉乐看着他嘴上口罩的起伏,耳边却只响起机器运转的声音。
“哐哧……哐哧……”
机器的声音回荡在嘉乐的耳中,仿佛永远不会停下。嘉乐发现,自己的脚步和心跳,逐渐融入了这单调而重复的节奏中。那几个有裂痕的玻璃瓶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长长的裂痕斜穿过玻璃瓶上的身影,像是把自己斩成两段。嘉乐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想要把那影像赶出去。
“你干吗?做工做傻了哦?”同事摘下口罩问,是黄叔。
“好像是吧,哈哈。”嘉乐干笑着,也摘下了自己的口罩。
“有烦恼?反正今天周六,下班后一起去喝杯酒怎么样啊?听说过那位啤酒西施了没?我带你去看看!”黄叔看嘉乐脸色不好,提议道。
“好啊!我请你!”提到酒精和女人,嘉乐放声大笑,似乎找回了一些活着的感觉。他和黄叔肩并肩,开始有说有笑地往食堂的方向走去。
“哐哧……哐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