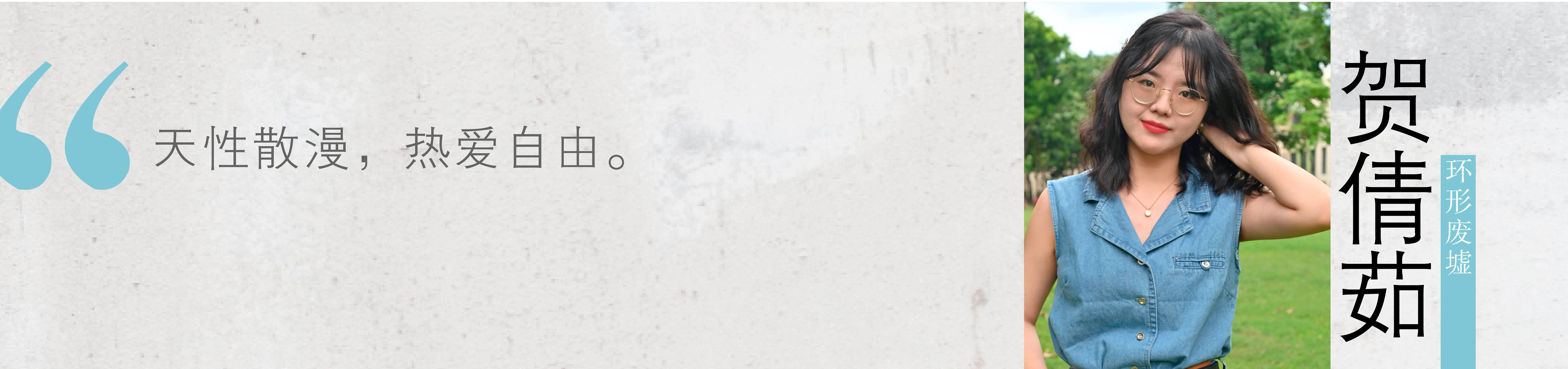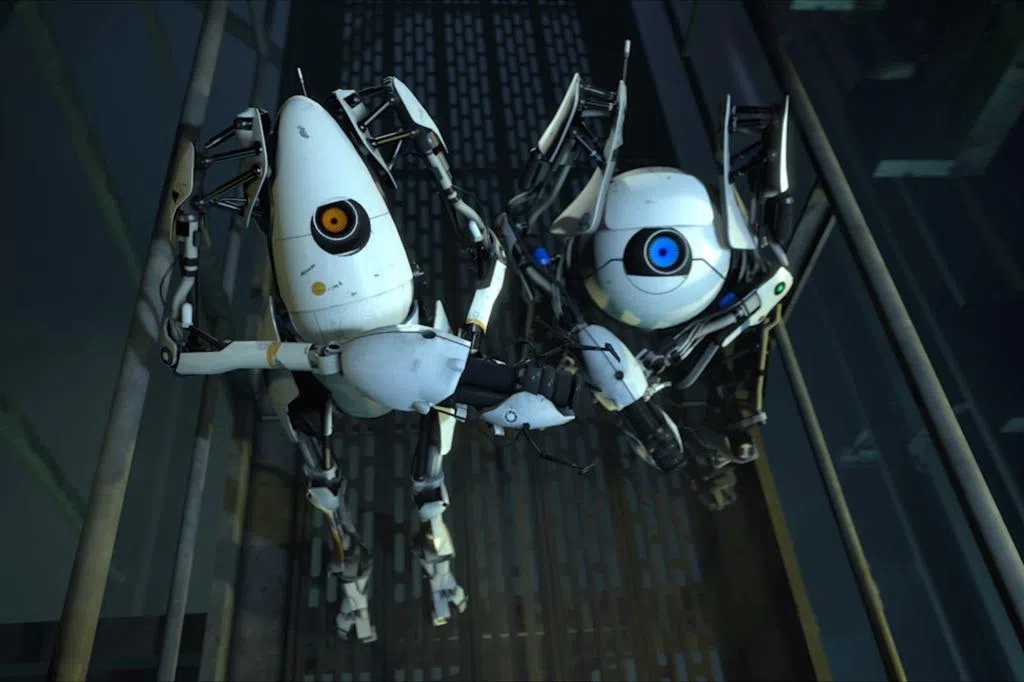我在某个电影播客中听过一个极端的观点,播客说:“杨德昌和侯孝贤是华语电影的两座高峰,一个是彻底的社会批判,一个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其余的华语电影不过都是居于其间的作品。”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的确可以当作进入两位导演电影世界的一把钥匙。
前段时间的某个星期天晚上,我和B在家里煮火锅,本打算看《索拉里斯》,但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还要一边看苏联电影,确实有些为难大脑的工作能力,我提议还是换一部华语或英语的电影,于是B打开了《恐怖分子》。
B问:“你猜是哪一部?”
我答:“杨德昌。”
B说这部电影一直在待看列表里,但没有找到时间看,我也是。
杨德昌的电影是不应该拿来下饭的。我和B一边吃火锅,一边对着杨导的电影指指点点。电影开始出现的人物太多,又没有细致的人物介绍,三条故事线直接铺开,信息量太大,又没有高设定的悬念,后续节奏散漫又克制,让人很难入戏。
B说:“把三条故事线串起来的点太过偶然。”
我说:“杨德昌的镜头语言和转场剪辑好像很平实。”
该死!两个没有认真看电影的观众,点评也没办法精确。
B吃完饭就回学校宿舍了,房间里变得安静,只剩我一个人。
我坐在电脑前,开始让电影剧情和画面涌回我的脑中。为小说创作苦恼的妻子,盼望早日升职的丈夫,恶作剧的少女,沉默的母亲,热爱摄影的少年。散落的人物、故事、画面,在安静的空间里开始被重新组织和思考。
人物是充满象征的,淡漠疏离弥漫在关系之中,夫妻、母女和恋人都逃脱不了。女主角说的“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不会懂”,每一段关系里的人好像都想说给对方听。
故事是复杂精妙的,从平常的早晨一声枪响开始,让三组平行的人物产生了微妙的关系,同时以一声枪响结束,巧妙地形成了一种回环结构。而故事的每一个节点,每一句台词,都好像一个浓缩的寓言,在城市生活的你,会在人生的某一刻照见自己,一如杨德昌的其他电影。
画面是被细致设计的,虽然没有《梦之安魂曲》《红辣椒》炫技式的快节奏和匹配剪辑,但杨德昌非常擅长利用封闭空间中的调度、光线和道具,来呈现人物关系与情感状态。门框、玻璃、百叶窗、格子间、层层叠叠的大厦,杨德昌用镜头展示被困在钢筋水泥的方框中的人,他们在其中疏离,或若即若离、孤独、困苦,找不到出路。
1986年,周郁芬在《恐怖分子》里振振有词:“当初结婚,以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那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为的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但1985年的阿隆已经在《青梅竹马》里回答过:“不要想美国了,美国也不是万灵丹。跟结婚一样,只是短暂的希望。让你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一种幻觉。”
杨德昌织了一张细密回环的网,人在都市和社会的框架里,角色在故事、镜头、画面的框架里,观众在杨德昌的寓言之网里。
电影里演到,丈夫在妻子离开前从未读过她写的小说。
B说:我好像也没有看过你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