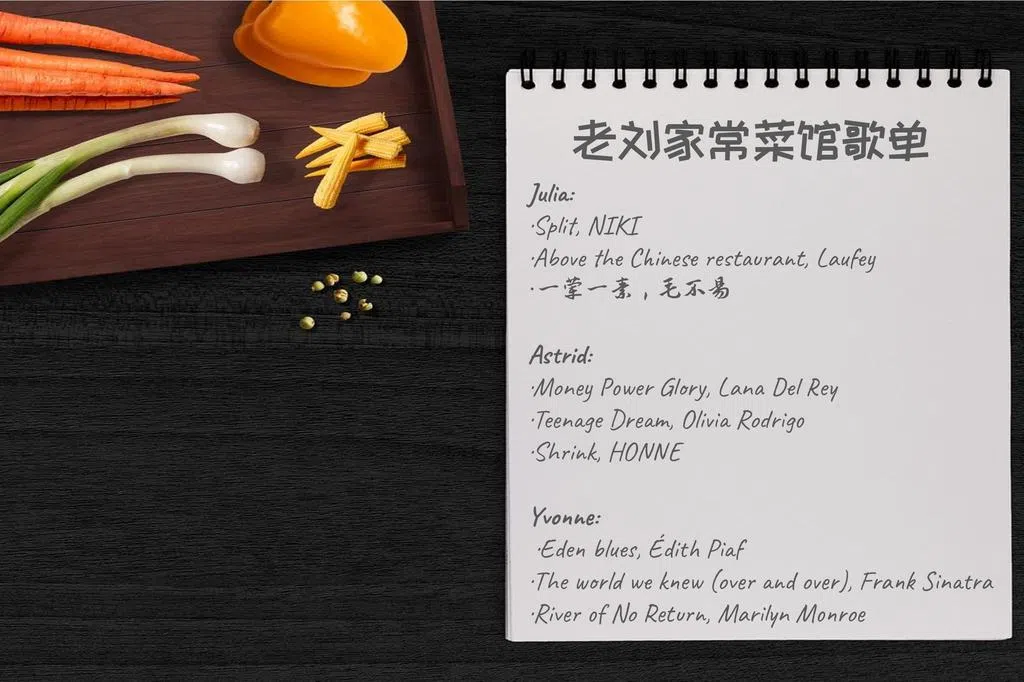佛罗伦萨的夏日宛如一场不愿醒来的梦境。拉斐拉,伯爵唯一的女儿,如今失踪了。她的长裙拖在尘土间,白色的衣摆已沾满泥垢。她的眼神迷离,空洞得像一座废弃的花园。唯有那句反复低喃的“Ciao, amore”仍在她唇间盘旋,仿佛是遗落在时光中的咒语。
拉斐拉的丈夫是个面目狰狞的暴君。在那绯红的地毯和阴森的烛光下,丈夫的怒吼和拳脚如同狂风骤雨般袭来。她的身体承受着皮肉的苦痛,而心灵却如空虚的杯盏,渐渐被无尽的黑暗灌满。她的脑海中浮现的,是丈夫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扭曲的面孔,是每一个“Ciao, amore”在恐惧与屈辱中挤出的微笑。
夜里,拉斐拉常常看见圣母的画像在墙壁上冷冷注视。她的目光似乎在嘲讽拉斐拉对神的无力祈求。黑暗中,拉斐拉感到有一双隐形的手抚过她的头发,轻声低语着安慰,却又令人不寒而栗。那些触感是陌生的,但也带着某种致命的吸引。绝望的她开始怀疑那并非上帝的恩赐。
“Ciao, amore”。那晚,一个闪电撕裂天幕,暴雨如狂暴的怒潮般冲刷着古城的石墙。拉斐拉在地上挣扎。丈夫挥动着拳头,咒骂夹杂在雷声中劈头盖脸地砸向她。她看见蜡烛摇曳的火光映在丈夫狰狞的脸上。拉斐拉手中紧握的花瓶在片刻的恍惚中砸了下去。玻璃碎裂声在她耳边炸响,血液飞溅而出,溅到了她身后的十字架上。“Ciao, amore”。她早已分不清是丈夫的叫喊,还是她内心深处的呼唤。
“Ciao, amore”。她明白了,她的祈祷正在悄然地向黑影敞开。拉斐拉并不清楚从何时开始,她的恐惧与怨恨在无尽的屈辱中,演变成了某种病态的依赖。它没有面孔,也没有名字。它只是一个错觉。鲜血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看见丈夫挣扎的身体和痛苦扭曲的脸庞,却仿佛与自己毫无关联。急促的低语在她耳畔缠绵,交织着难以言喻的欲望与怜悯。它徘徊在拉斐拉的梦境边缘,像情人般抚摸着她的灵魂,将她从人世间的痛苦中剥离出来。
次日,拉斐拉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她停在那家Gelato店前,挑选那最鲜艳的颜色。冰凉的甜意在她舌尖化开,犹如她曾经深爱的温度。她舀起一勺又一勺,啃食着某种无法摆脱的负罪感。拉斐拉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什么,甜美又粘稠的味道是否真的存在。
“Ciao, amore”。拉斐拉看见自己穿着那件绣满花瓣的白裙,在厨房中忙碌着,为丈夫准备他最爱的玉米糕。阳光透过花窗洒了进去,暖黄的光芒包围着他们。丈夫总是带着笑意走近她,从背后轻轻搂住她的腰,将下巴搁在她的肩头,低声说:“Ciao, amore,” 那声音柔和得如同教堂里的轻声祷告。美酒下肚,他们一起驱车前往托斯卡纳的田野。一朵雏菊别在她的发间,微风轻轻掀动花瓣。丈夫微笑着注视她,目光温柔得像一片无垠的海洋。他靠近她,带着阳光的味道,指尖轻柔地掠过她的颈侧。他的唇轻轻贴上她的,柔软而轻巧。拉斐拉闭上眼睛,感受着他温暖的气息并沉醉其中。
一种冰凉滑腻的触感猛然袭来,瞬间打破了她的迷梦。她低头看去,才发现一滴融化的Gelato滴落在她的手上。顺着指缝滑下,凉意瞬间刺透她的皮肤。拉斐拉感到那句“Ciao, amore”在她的喉咙间苦涩地回荡。
后来,拉斐拉去教堂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教堂的每一处角落都充满了肃穆的神圣,但拉斐拉却感受到一丝隐秘的甜蜜。拉斐拉跪在冰冷的石地上,双手合十,眼神迷离而空洞。她的祷告在那些肃静的夜晚变得模糊不清,仿佛并不是为了求得救赎,而是为了满足内心无尽的贪恋。那欲望如同黑暗中的藤蔓,无声无息地攀附着她的灵魂。拉斐拉渴望着与那双熟悉的手一同追逐着那片被夕阳涂抹的血色光晕。她知道它是短暂的,是灼痛的。可那是她唯一的救赎,是她最深的沉沦。
白昼与黑夜的交替,对拉斐拉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她穿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耳边别着一朵小小的雏菊。纯白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颤抖,似乎还残留着晨露的湿润。那白色的裙子与她苍白的肤色相映成辉,让她看上去既圣洁又虚幻。步入店内,拉斐拉的目光很快就停在了最亮的一款Gelato上,鲜艳得像是方才滴落的血珠。冰凉的液体沿着她的指尖滴落,犹如鲜血般滑腻。她舔舐着最后的残留,甜美中夹杂着丝丝铁锈的苦涩。拉斐拉的笑容在阳光下,透露着难以言喻的幸福。
拉斐拉的意识在混沌中徘徊。每日清晨,她睁开眼,怀里便是丈夫冰冷的躯体。她蜷缩在丈夫凝固的血海中,稀罕的液体还是染红了她的白裙。那一刻,她终于再次感受到那熟悉炙热的触碰。它像佛罗伦萨午夜的风,优柔寡断。手指沿着她的脊背滑落,轻柔如羽。拉斐拉闭上了双眼,接受了这场无声的洗礼。在这诡异的缠绵中彼此侵蚀,恶魔则彻底占据了她无暇的灵魂。
后来,那家Gelato店不知了去向。拉斐拉再也没去教堂,她甚至再也没有出现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
后来,人们都说,伯爵女儿疯了。她吃了她的丈夫的尸体,然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