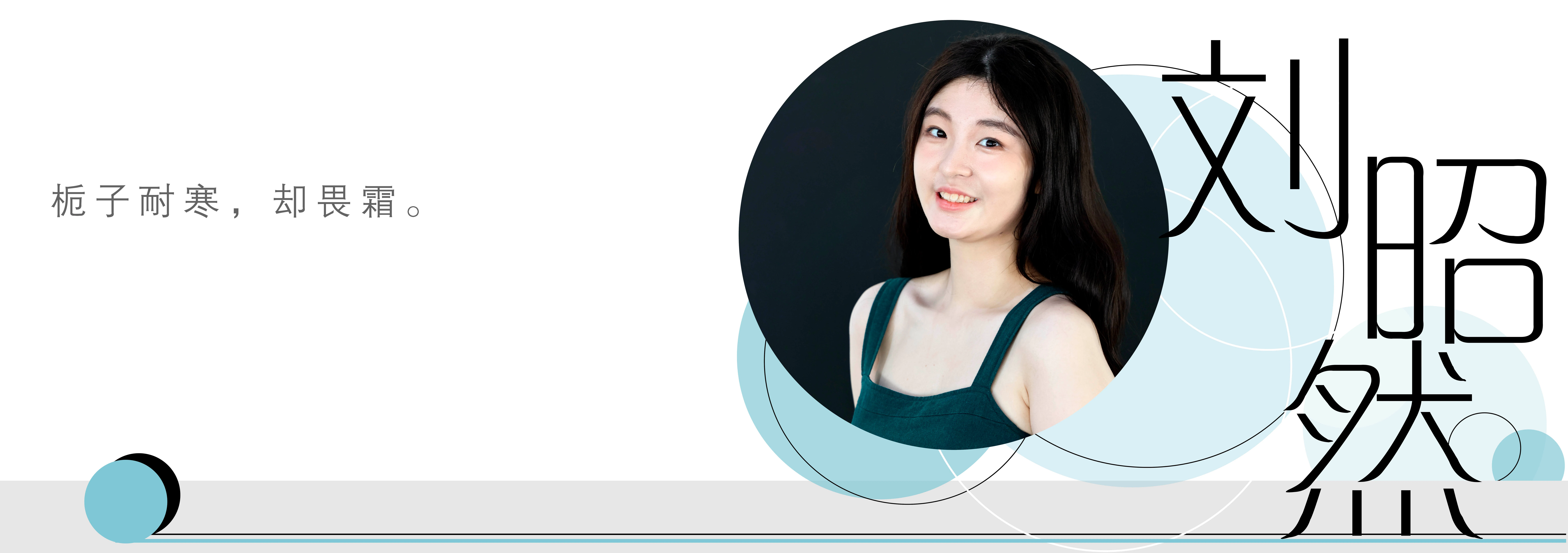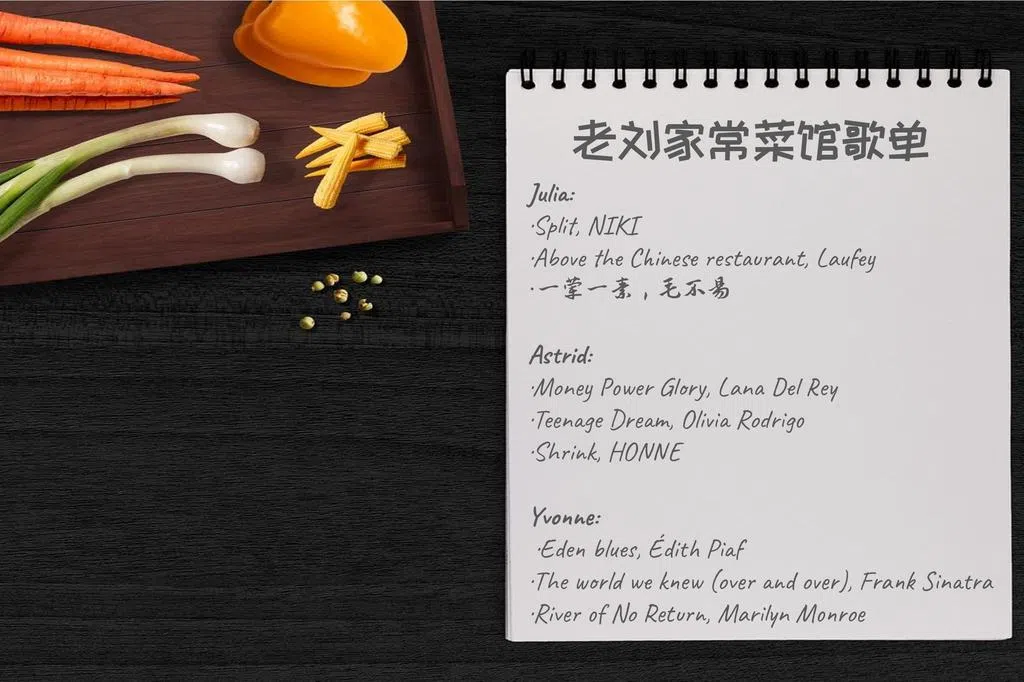冬天的阳光总是带着一种惺忪的倦意。下午四点半,太阳像一盏将熄未熄的灯笼,光线柔得像刚刚醒来的梦。车窗外的风景一晃而过,山丘的影子则被拖得老长。那一树栀子花是姥姥种的,就长在她小院的门口。每年这个时候,满树洁白的花开得繁盛。
其实,我舍不得摘它。花离了枝桠,像是失去了某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可姥姥却执意地笑着劝我:“花开过了,今年开的就今天带走吧。让它跟着你一起吹吹北方的海风。”
我将那一束栀子花轻轻插入矿泉水瓶中。瓶身虽简陋,却因水波微漾而多了一层朴素的灵动。花朵安然无恙地伫立着,仿佛连火车的颠簸也无法扰乱它纤薄的美。那花香轻柔,像一缕无法捕捉的幽梦,在车厢里悄然弥散。它织成一道无形的结界,将喧嚣和疲倦隔在外头。栀子花的香,既不如玫瑰那般浓烈,也不似茉莉那般馥郁。它的气息,是一种孤独的温柔,像一首婉转却未出口的情歌,徘徊在舌尖,不肯散去。
火车穿行隧道,光影明灭交错。每当光线洒下时,花瓣便泛起一层通透的莹润。我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将鼻尖贴近那片洁白,深吸一口。转瞬间,冬日带着一丝不可名状的暖意,在花香里化开了。香气牵引着记忆,带我穿过隧道,回到姥姥的小院。那儿依然是阳光斜照,栀子花正开得烂漫。
抵达老火车站时,天已微暗。站台上的蓝色栏杆依旧矗立。它如记忆中那样,表面已经被时间磨得斑驳。我沿着栏杆走向海边,冷冽的海风扑面而来,卷杂着咸腥的气息,直入肺腑。那束栀子花被风吹得微微颤动,香气却似乎愈发鲜明,像是在与腥咸的海风争夺我的注意。海的气息,总是沉重而绵长,仿佛从深海深处带来的某种不朽的记忆,将人牢牢攫住。可栀子花的香却轻柔得几近虚无。它似乎不属于这里,却又固执地在腥咸的空气里留下一抹独特的清甜。它如同一束微光,短暂却真切。
海浪在不远处拍打着沙滩,节奏像是深沉的絮语。浪头翻卷着白色的泡沫,扑向礁石的瞬间,碎裂成无数的水珠,仿佛一场微型的烟火。那声音低沉而持续,带着某种让人心安的韵律。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栀子花的香味与海风的腥咸交织在一起。转瞬间,是花、是浪、是风,都统统不重要。
几年后,解封后的某个冬日,我再度奔向海边。第二海水浴场的风依旧咸涩,海浪依旧低吟。我站在沙滩上,望着灰蓝色的海面,熟悉的腥味在鼻尖盘旋,却再也无法捕捉到那一抹花香的清甜。我呆呆地倚在栏杆上,感觉自己与海浪和风声隔得太远,太远,还是太远了。连同那些逐渐模糊的记忆,慢慢溶进了潮湿的空气中。转瞬间,栀子花香早已隐没在时光的褶皱里。
栀子花的香,或许留在了那个冬天的车厢里,留在了海风轻抚蓝色栏杆的那个傍晚。我的记忆则像被稀释的墨迹,颜色愈发淡薄。我唯一能依赖的,是那股咸腥的海风。每当它轻轻拂过,我就知道,海还在,栀子花也还在。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世事更迭,而留存的,往往只是味道。但,曾经的味道早已被时光稀释了。留下的,又只有一个无声的空白。转瞬间,海风无眠。
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姥姥的小院子,那一树一树的栀子花,以及她递花时和蔼可亲的模样。转瞬间,她轻声说道:“花不必贪恋枝头,它有它的归宿。”闭上眼,曾经隐约飘过的花香,再次轻轻拂过我的脸颊。它像是微风带来的呢喃,悄无声息地溜走了。隔着海风,冬日的余温缓缓吹过。是花,是浪,是风?我想是我快疯了。因为一旦睁开眼,映入眼帘的只有无尽的海浪和风声。
或许,栀子花依旧。只是,它早已等不到下一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