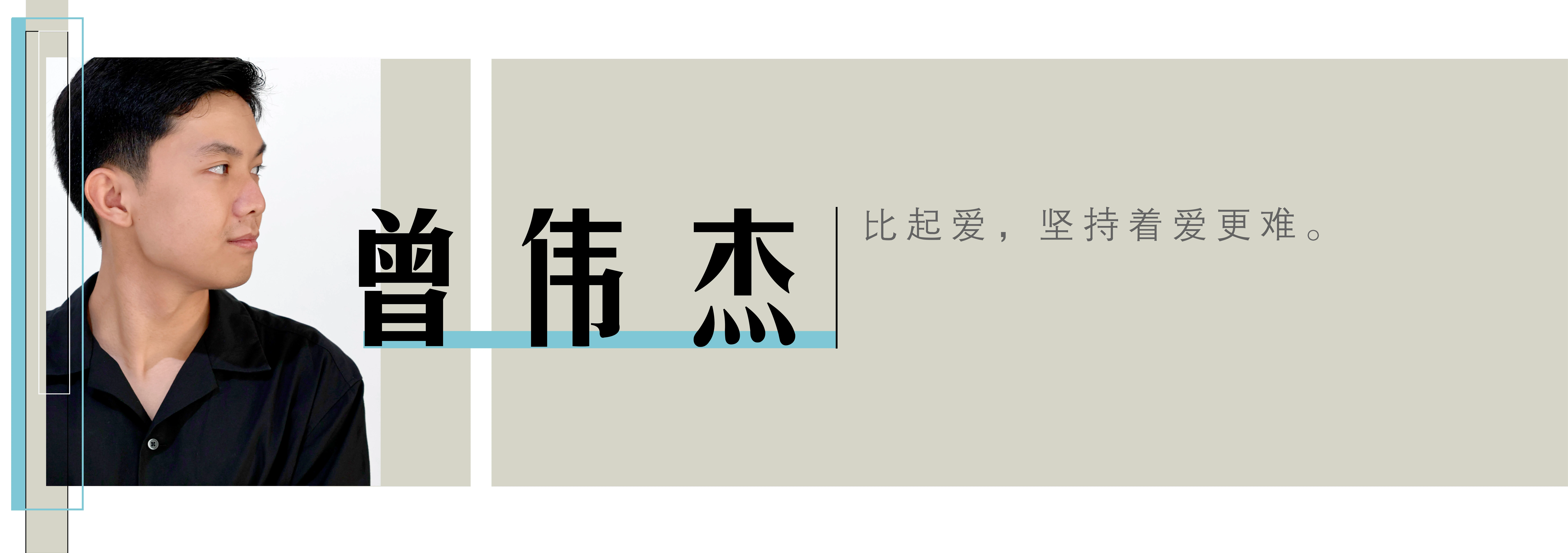周五晚高峰,加上周一公共假日,再加这场从早下到晚的雨,无论关卡人员如何努力做减法,仍无法改变长堤变成一座大型海上停车场的既定现实。巴士、罗厘、汽车、摩托,将窄窄的一公里塞得犹如暴饮暴食者的一段心血管。
雨滴沿着玻璃滑落,长堤上不时也有赶时间的行人冒雨前行。国华看着人从左边走到右边——不知已经走过了几个——他没有数,只觉得自己方才急急忙忙跳上巴士真是死蠢。
国华打开手机,荧幕上显示着妻子打给他的通话记录。有七秒长。接到妻子的电话时,国华正忙着用叉车将货物装上集装箱。
挂掉电话,他立刻请了假。搭巴士,转地铁,再转巴士,过了一道关卡,再跳上巴士。他的身体在高峰时段的人潮中挤来挤去,等到他发现自己搭的巴士,正困在车龙中寸步难行时,已经是两小时以后的事。
来到半途,他忽然有些不确定了,妻子电话里那句“Father不行了”,会不会是听错了呢?
司机放下手刹,将车往前挪了几米,又猛地刹住。车里的人随着惯性按同个节奏在车里摇晃。有人低声嘟哝,有人大力吐气,引擎隆隆作响,车厢内像积蓄着某种能量,缓缓地烹煮着所有人,却又无处可逃。
万一真是听错了呢?国华想。
车上人挤人的,国华觉得胸口有些闷。他不敢打回家再确认,他想起儿子曾说过的关于那只老外的猫的故事:猫既是死的,也是活的,直到有人打开盒子为止。
虽然Father不是猫,但现在的状况,好像也有些雷同。但不管怎样都不重要了。假也已经请好,现在也只能往家里去。
“到了再说吧。”他这样安慰自己。
巴士又再挪动了几米。国华回忆起过去几年家里的情景:Father躺在床上,意识模糊,大小便也已不能自理,但每当全家赶回来围在床边守着,他却又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能喝几口粥,说几句话,随后又沉沉睡去。
事实上,因为父亲身体情况的反复,夫妻二人早已安排好办理后事的准备。报警、联络殡仪馆、找报馆发讣告……所有重要的电话号码,全都已写在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放在书桌的抽屉里。
雨水顺着车窗滑落,划出一道道不规则的轨迹。其他的东西开始在国华的心中涌动。他想起妻子,想起这些年来她为Father擦身、量血压、喂药、把屎把尿的情景。
国华有时问她累不累,她总是淡淡地说:“谁叫我嫁给你,又有什么办法。”国华听了心里五味杂陈。是啊,自己不过是个埋头做工的工人,一个月才赚两千多新币,上有老下有小,哪来的其他办法?
于是,这一切便只能由妻子来承担。这样的日子,她从未抱怨,也从未显露过一丝一毫不耐烦。可妻子越是任劳任怨,国华就越是不知所措,越是感到亏欠。
国华想到工厂里的一位同事。那同事曾为了照顾糖尿病的父亲和妻子大吵一架,甚至好几天不回家,干脆在厂里打地铺。同事听闻国华的情况,说:“晒命啦你!似我就死咯”。国华只能苦笑,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巴士缓慢前行,终于来到长堤的中段。远处,雨雾笼罩,踏在不知是属于哪一国的水面上,国华觉得一切的事情仿佛都还没有落下成为现实。
他听说过“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父亲刚病,他不以为然,后来才明白它的分量。国华发现,Father卧床后,他们的交谈越来越少,彼此间的距离也随着时间越拉越远。当父子关系的全部被压缩到一张病床上时,哪怕感情再深也难以维系。
也许他早点离开去找Mother团聚,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好一些吧。他曾不止一次这样想。
国华身后的乘客看着不远处那道笼罩在雨雾中的高架桥,与同伴滔滔不绝地聊起地铁通车后新柔两地发展的宏大愿景。国华听着,思绪被牵走了一阵。
等到它通车了,或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吧。国华想。
“铃铃铃……”手机忽然响起。是妻子打来的。国华怔住,深吸一口气才积攒接起电话的勇气。
“喂,阿华,你在哪里?”电话那头传来妻子的声音,略显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