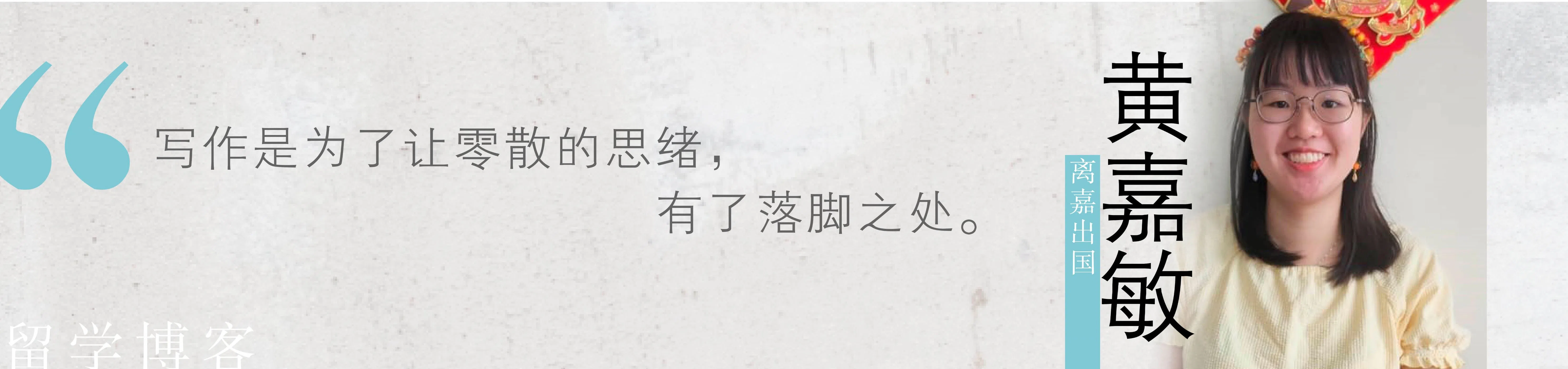在抵达北京的第三天,我后悔了。没人告诉我离开家以后的生活会这么困难。
意料之外的问题如海啸般接二连三地涌进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吞噬,内心留下一个刺眼的问题:我离开家乡大老远来到北京交换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朋友们眼中,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毕竟占满我整个青春的偶像来自中国,在追星最疯狂的那几年,我甚至萌生去中国读大学的念头。但只有我知道,我特别不适合出国留学:没住过宿舍,从未离开家超过一个月,生活技能几乎为零——这份清单上的每一条都与出国留学所需的独立和抗压能力格格不入。所以我努力让自己准备迎接离乡的日子,比如向学长学姐了解交换的细节,上自身防卫课,承包家里各种家务。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我天真地以为,提升生活技能便足以应对交换生活中的一切。我天真地觉得,交换生活会如想象中明媚与热烈。我甚至天真地相信,踏上交换之路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做出的理智决定。只是我忽略了一个最基础的点:我所做的准备都基于“我选择出国交换”这个最根本的决定,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切的起点,本就是不理智的。
我内心还住着那个15岁整日迷恋偶像的小女孩。我始终想见一见在我青春里留下无数刻骨铭心的回忆的少年们,即使见不到,我也希望能够去他们生活过的北京住一段时间。这颗在青春埋下的种子,早已悄无声息地萌芽,如藤蔓般缠绕心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我对北京的向往最终以“清华大学交换生”的形式实现。
可这一切,终究是带着我的幻想与滤镜。模糊且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很脆弱的,所以当现实狠狠地将其碾碎,只会留下一片狼藉,以及血淋淋的真实世界。我曾在网上看过故宫的雪,覆盖着红墙金瓦,勾勒出一幅浪漫的雪景。可现实却是,我始终没能等到一场期待已久的雪。北京刺骨的冷风猛灌进身体里,也渗进了心底,把原本孤独的心灵披上一件凉透了的外套。现实与幻想中的画面重叠,却又处处不同。我对北京所谓的“理想”,或许更多源于青春的情感投射。那些在散文里被我诗意化的向往,不过是自己编织的一场美梦。抛开滤镜后,我才恍然发现,我根本没有实在的理想支撑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
交换的第一个星期有父亲陪我安顿下来。某一晚吃火锅,父亲说起了他决定陪我来到这里的真实原因。他20岁的时候来到新加坡成家立业,所以在我爷爷过世前,他们错过了一场父子单独的旅行。他为此感到惋惜,便不愿让我留下同样的遗憾。他说若干年后,这趟旅行必定成为我心中难以忘怀的部分。接着,如同电影情节一样,店里播放了父亲最喜欢的《千千阙歌》,我的眼泪瞬间不受控制地滑落。
几天后,我经过清华二校门时看到中国各方的人,男女老少,三代同堂,排成长龙站在二校门合影。互相打闹的小孩不明白为何周末非要来到大学参观,但这或许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和爷爷奶奶把理想传递给下一代的方式。当我告诉亲戚和认识好几年的中国朋友,我在清华大学交换,他们纷纷恭喜我踏入了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他们的祝贺化成了我留在这里的底气,让我继续珍惜在清华短暂却精彩的四个月。
此刻,他人的理想与我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碰撞。面对这微妙的对比,我开始思考“理想”的意义。它可以是一个多年奋斗的目标,一个家庭的期盼,同时也是流淌在生活中平凡且珍贵的细水长流。无论是远方的理想,还是为自己不留遗憾过上的理想生活,“理想”的意义,或许就是让我们在追逐它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在抵达北京的第20天,从新加坡带来的洗发水用完了。我依然想家,但仍买了一款陌生的洗发水,这应该足够我用上两个月吧。我开始期待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每周去超市时,会挑选哪种水果?今天又会在清华的哪一间食堂尝到怎样的味道?周末,我又会去北京的哪一个角落,遇见怎样的风景?
离乡的路固然孤独,但至少我在寻找理想的途中,慢慢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北京的冬天依然吹着刺骨的冷风,但每当我伸出藏在羽绒服袖子里的手,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逐渐变暖的阳光,它把那件凉透了的外套一点一点地晒干,我的内心也随之温暖起来。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