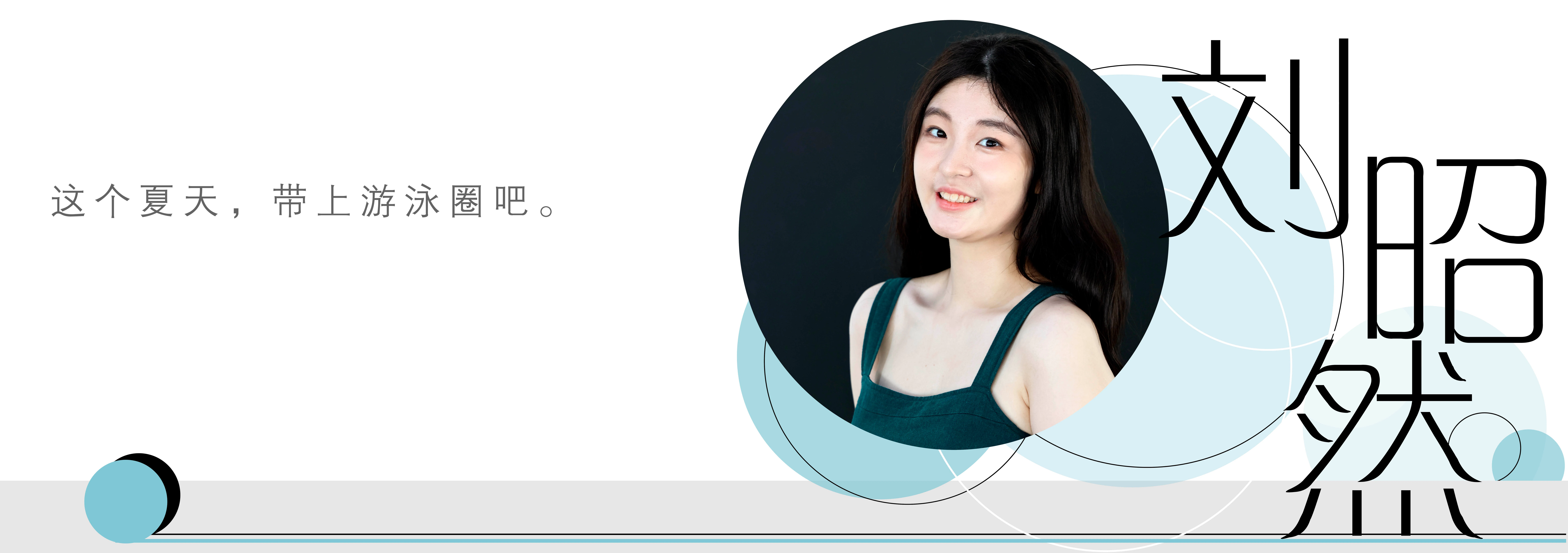渤海湾的风,总是咸的。咸得发苦,如泪坠凡尘,如血染浪痕。
雯站在栏杆边,手里捧着那个青花瓷的骨灰盒。盒身上绘着几枝瘦梅,枝干扭曲,如她此刻紧绷的表情。父亲站在三步开外,手里夹着烟,烟灰簌簌落在水泥地上,像一场微型雪。
“撒海里得了,赶紧撒了,我没钱给她买块儿地。”
雯的手指在颤抖。骨灰盒的盖子打开时,一阵风掠过,卷起几缕灰白的粉末,扑在她的校服上。她低头看着那些粉末,恍惚间觉得那是母亲的手在抚摸她。母亲的手总是凉的,像冬天的海。
“妈……”她唤了一声,声音被海风撕碎。骨灰自指缝间流泻,如一场逆行的雨,洒落向深不见底的海。她想起母亲生前最爱的那首诗:“The sadness of my soul is her bride’s veil. It waits to be lifted in the night.”
海浪拍打礁石,回声空旷。远处的渔船拖着长长的尾迹,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雯的眼泪滴落在栏杆上,碎成细小的水珠。她想起母亲临终时瘦成骨架的身影,胸膛剧烈起伏,嘴里呢喃着不成句的诗句。
“雯,你知道吗?那首诗,是我写的。”母亲的眼睛亮得吓人,“等你长大了,我再告诉你它的意思。”
-
我几乎忘了,她姓什么。只记得她不许别人叫她全名,甚至连父亲的姓氏都不愿承认。同学们给她起过很多外号,但最后还是她自己说:“叫我雯吧,那是我妈妈的名字。”
转校生总是带着格格不入的气息,仿佛一道突兀的裂痕,强行嵌入陌生的集体。然而,雯却是个例外。她轻而易举地融入了班级,像一阵风,吹过每个人的身旁,却偏偏停在了我身边。
我们开始一起上下学,渐渐形影不离。雯是第一个向我敞开内心世界的人,她的世界像一本未完成的诗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的追忆与依恋。她常常提起母亲,说她是个写诗的人,精通几门外语。然而,雯与母亲的见面却寥寥无几,那份依恋像月食前的余光,渐渐被阴影吞噬。
-
雯对诗歌的痴迷近乎偏执。她常常在课间独自坐在窗边,手中捧着一本泛黄的诗集,眼神游离在字句之间,仿佛那些诗句是她与母亲之间唯一的桥梁。她的手指轻轻抚过书页,像是在抚摸某种即将消逝的东西。我总觉得,她的生命与诗歌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静静看着她,心中没有波澜。
我知道,雯硬生生地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她的生命仿佛不是由血肉构成,而是由飘渺的意象、断裂的韵律和无法诉说的情感编织而成。她与诗歌之间有一种近乎扭曲的联结,仿佛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首诗:短暂、易逝。
-
“雯,你抄得太明显了吧?”英文老师将作文本拍在桌上,语气里藏不住讥讽,“《飞鸟集》整段抄袭,你当我是瞎的吗?”
教室里爆发出哄笑。笑声像风暴,撕裂她最后一丝体面。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在阳光下缩成一团的影子,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那是我妈妈写的。”她嗫嚅道。
“你妈还能穿越回19世纪?”
笑声更大了,像锋利的浪花,一遍遍拍打她的心脏。她想起母亲临终前的眼神,那份执拗得近乎绝望的神情。她忽然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可怜女人的自我欺骗。
-
渤海湾的黄昏总是来得特别快。雯坐在长满苔藓的台阶上,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海风卷着腥咸的味道,从发梢钻入骨缝。她的手指反复摩挲校服上的灰烬痕迹,仿佛这样就能触碰母亲残留的温度。
“小苑,我明天就走了。”她盯着海平线,语气轻得像梦呓,“我要去找她,好好问问,她到底为什么骗我。”
在我眼里,雯的生命与春天何其相似,短暂而美丽,却注定流失。花开得再绚烂,也逃不过凋零;她的存在再耀眼,也终将归于虚无。而我,早已接受了这种短暂。这不过是春天结束后的必然,不过是诗歌写完后的句点。而我,只是静静看着,心中没有波澜。
-
翌日清晨,渤海湾格外平静。雯想起母亲最后的话:“veil,也可以是盖头的意思。”
-
我想了起雯的模样。
闭上眼,她的身影渐渐模糊,仿佛一幅被水浸湿的水墨画。线条晕开,轮廓消散,最终融进那片无垠的深蓝。
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礁石,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在吟诵她母亲未竟的诗句。那些诗句,像是从海底深处浮上来的叹息,随着潮起潮落,回荡在空旷的海天之间。
而我,终究再也等不到那个敞亮如阳光的雯。她的笑声,她的眼神,都像被海风带走的细沙,从我的指缝间悄然流逝。海依旧在眼前翻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可我知道,那片深蓝里,已多了一首无人读懂的诗。
-
多年后,我翻开字典,找到“veil”的释义:面纱,掩饰。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页上,晕开浅金色的光晕。我又想起了雯的模样。推开窗,我看见海浪一遍遍冲刷礁石,像在低声吟诵母亲未竟的诗句。
-
渤海湾的风,依旧咸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