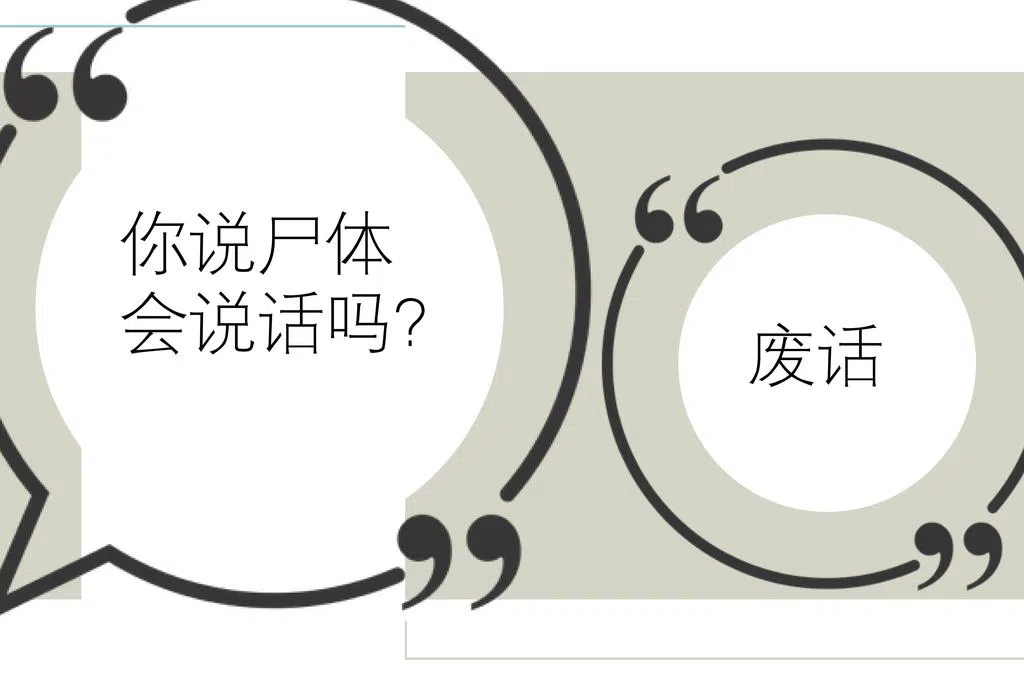狗,是人们的朋友,人们都是这么说的。
在记忆里的很久以前,街上常会看到的狗是哈巴狗,或又高又瘦的斑点狗。在我那场分不清真假虚实的幼时噩梦里,在电瓶车后,追着我裤腿咬的便是哈巴狗。而如今,城市里的养狗人养的都是萨摩耶,和阿拉斯加。
我模糊地记着,我老家以前也养过一只狗,一只斑点狗。似乎是我外公,或是我舅舅从外头随手捡回来的幼犬。捡回来后也不精心照料,直接丢给了家里的外婆。而外婆她向来不是一个会轻易喜欢猫猫狗狗的人,她只喜欢她后院里的那群大鹅与老母鸡。那只斑点狗在我家过得并不好,但是要真说多不好,其实也并没有太不好,毕竟那时的狗,都这么过 ——吃点主人家的剩饭剩菜,家里来人了必须嚷几声,以表它尽忠职守的职业态度。
它吃饭时很安静,不像别的狗那样狼吞虎咽。它总是先嗅一嗅,再慢条斯理地舔食盆的边缘,最后才吃正中的“乱炖”。他们有时会蹲在旁边看它进食,或是搬个板凳坐它旁边点烟。再后来那只高瘦的斑点狗离家出走了,没人知道它跑哪儿乱晃去了,抑或是落哪家狗肉店手里了。
再后来,我养了一只自己的小狗,一只有着圆圆耳朵的小型犬。医生说它肠胃弱,所以我学会了挑肉里的筋膜,把鸡胸肉撕成细丝,煮得刚好软烂。有时我会加一点南瓜,蒸熟后捣成泥,混在狗粮里。它低头吃的时候,耳朵会轻轻晃动,像两片柔软的树叶。我蹲在厨房瓷砖上看它吃饭。鸡胸肉要撕成细丝,南瓜得蒸到筷子一戳就烂。这些活我干得比给自己做饭还仔细。有时候肉丝掉在地上,它立刻就会舔起来。它的舌头粗糙温热,像块会动的砂纸。我给它买的碗是不锈钢的,沉甸甸的,不会轻易被拱翻。它的水盆也是,每天换两次水,确保没有浮尘。
它不知道这些。它只知道今天的肉比昨天的香,或者水盆里的水又凉又甜。它不会知道,我曾在超市的货架前站了十分钟,比较哪种狗粮的蛋白质含量更高。它也不会知道,我凌晨3点醒来,只是因为担心它会不会冷。
它只是吃,吃完就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尾巴轻轻摇。
有时候,它会叼着玩具来找我,那是一只褪色的橡胶鸭子,咬下去会吱吱响。它喜欢把鸭子放在我脚边,然后趴下,下巴贴着地板,等我捡起来丢出去。我丢得不远,它跑几步就叼回来,再放下,再等。
我们就这样玩,直到小鸭子身上布满了牙印,伤痕累累,它依然最喜欢小鸭子。
它的窝是棉布的,里面垫了旧毛衣。我偶尔半夜醒来,会伸手摸摸它,确认它的呼吸是否均匀。它睡得很熟,有时会做梦,腿轻轻抽动,像在奔跑。我数着它的呼吸。有时候,我会把它的小爪子捧在手里闻一闻。它的爪子有一股臭臭的小狗味,混着草地和阳光的味道。我把它搂在怀里,蹭它的脑袋,说:“宝宝,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宝宝。”它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它会舔我的脸,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望着它,想起小时候养过的一只鸟。那只鸟关在笼子里,我每天喂它小米和水,但它总是不快乐。有一天,它死了,我把它埋在院子里的树下,没有哭。
现在,我养了一只狗。它比鸟活得久,也比鸟幸福。它不用被关在笼子里,它可以跑,可以叫,可以在我回家时扑上来舔我的手。
它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它只是活着,快乐地、简单地活着。
而我,看着它,偶尔会想——
如果当年也有人这样看着那只小鸟,该多好。
现在它又在我脚边睡着了,肚皮随着呼吸轻轻起伏。我数着它的呼吸,一下,两下,三下。数到第100下的时候,我的眼泪突然掉在了它白绒绒的毛发上。它抖了抖耳朵,但没醒。
要是当年也有人这样数过那只斑点狗的呼吸,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