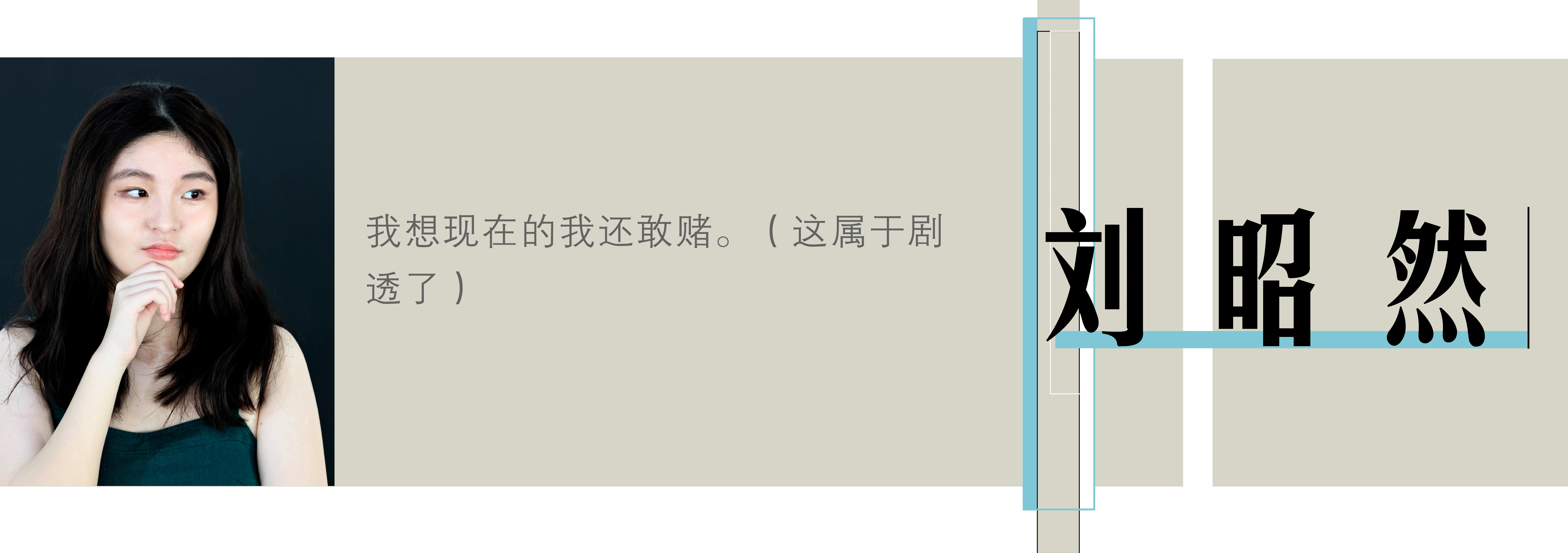小面包
我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九岁的冬天被锁在这张铁架床上,右腿绑着厚厚的绷带,像裹了层石膏的玩偶。护士说那是为了保护“小面包”。她们总爱给可怕的东西起可爱的名字。肿瘤就叫“小面包”,好像换个称呼就能把疼痛也变成过家家了。
梁主任查房时,白大褂总会带进一股冷风。他手指按在我膝盖上方三寸的位置,那里凸起一个硬块。“建议尽快……”他说话时眼睛看着病历本。医生们总是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词汇,渐渐我走了神。不过,却发现走神的不止我一个,站在床尾的爸爸不停地搓着手指,搓得关节发白。
等梁主任一走,他立刻钻进隔壁空病房。淡蓝色帘子晃了晃,我听见打火机“咔嗒”的声响,接着是消防警报尖锐的嘶叫。天花板突然下起雨来,爸爸顶着一头水珠冲出来,衬衫贴在后背上,像块半透明的糯米纸。
妈妈把他拽到走廊。透过门上的玻璃窗,我看见她的嘴型在说“肌瘤”和“女儿”,手指在空气中戳出一个个小洞。爸爸的背越驼越低,最后变成一团模糊的灰色影子。
“要是爸爸能戒烟,我的腿就会好。”这个念头冒了出来。但随即又自己否定了。姑姑常说爸爸一个卖烟的,烟瘾比买烟的还大。
-
我闻到姑姑带来的橙子香气里混着陌生的味道。不是烟味,倒像是薄荷掺了消毒水。她用沾着橙汁的手摸我额头,说:“你爸这回真豁出去了,你妈吵了十几年都没用。”
妈妈坐在床边削苹果,果皮连成一条长长的螺旋。刀尖突然顿了一下,在指腹上留下一道白印。我想,我和妈妈从来都不抽烟(除了被迫吸爸爸的二手烟)。那为什么姑姑不夸我们呢?但止痛药的药效上来了,这些话像泡泡一样,咕嘟咕嘟沉了下去。
冬泳
冬天,水面被斜阳晒得温热。可一潜下去,刺骨的寒意立刻漫了上来。贝贝倒喜欢这种温度差,一蹬腿就游了出去。
海水轻轻托着身体,不知不觉间,岸上的人声都听不见了。她回头才发现已经游出这么远。突然,贝贝的右腿猛地一抽,整条小腿不可控的僵住。四下空荡荡的,只有海水晃动的声音,和越来越远的岸。
小青蛙
爸爸怕我闷,从医院外的小鱼店带回三只青蛙。它们蹲在水缸底时像三块圆润的鹅卵石,眼睛总是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
我把不爱吃的剩菜全都用细线绑着,轻轻垂进水缸里。手指一抖,线头就跟着颤动。青蛙以为是蚯蚓,猛地一跳,嘴巴一张,一口吞下“蚯蚓”。它们傻乎乎的,每次都上当。
后来,我突然想:“如果这三只青蛙能生出一只小青蛙,我是不是也能好起来?”
可我不敢真的赌。万一它们全是公的呢?万一它们根本不会生呢?我盯着它们看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爸爸惊奇地凑过来,指着水缸说:“快看,青蛙下蛋了!”
水底黏着一团团透明的胶状物,里面裹着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我的心头一跳:“之前下的注应该算数吧?”
于是,我悄悄修改了赌局的条件:如果有几个蛋能变成蝌蚪,我就能康复。
倒数
夜里的海像一块黑色的铁,又冷又硬。
贝贝拼命蹬着腿,让身体不至于沉下去。冬天死在海里的都不是淹死的,而是冻死的。她的腿越来越重,像灌了铅。呼吸变成白雾,又迅速被海风扯碎。贝贝咬着牙,默念道:如果我能看见渔船的光,我就能活下来。
海水灌进耳朵,周遭变得格外安静,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像在倒数。
远处,真的亮起了一点光。它很小,很弱。贝贝眨了眨眼,怕那是幻觉。可它还在,晃动着,越来越近。
小屁孩
护士推门进来,哗啦一声拉开窗帘。阳光扑了进来,刺得我眯起眼。
“贝贝家属是吧?给孩子通通风,别老闷着。”
梁主任抽了抽鼻子,眉头一皱,目光钉在爸爸身上:“医院里电子烟也不能抽。”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不是说你不抽纸烟改抽电子烟就行了哈。”
爸爸讪讪地摸了摸鼻子,没说话。
窗台上的小水缸里,三只青蛙静静浮着,肚皮朝上,像几片泡发的茶叶。不过,缸底那些透明的卵,也早已变成了蝌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