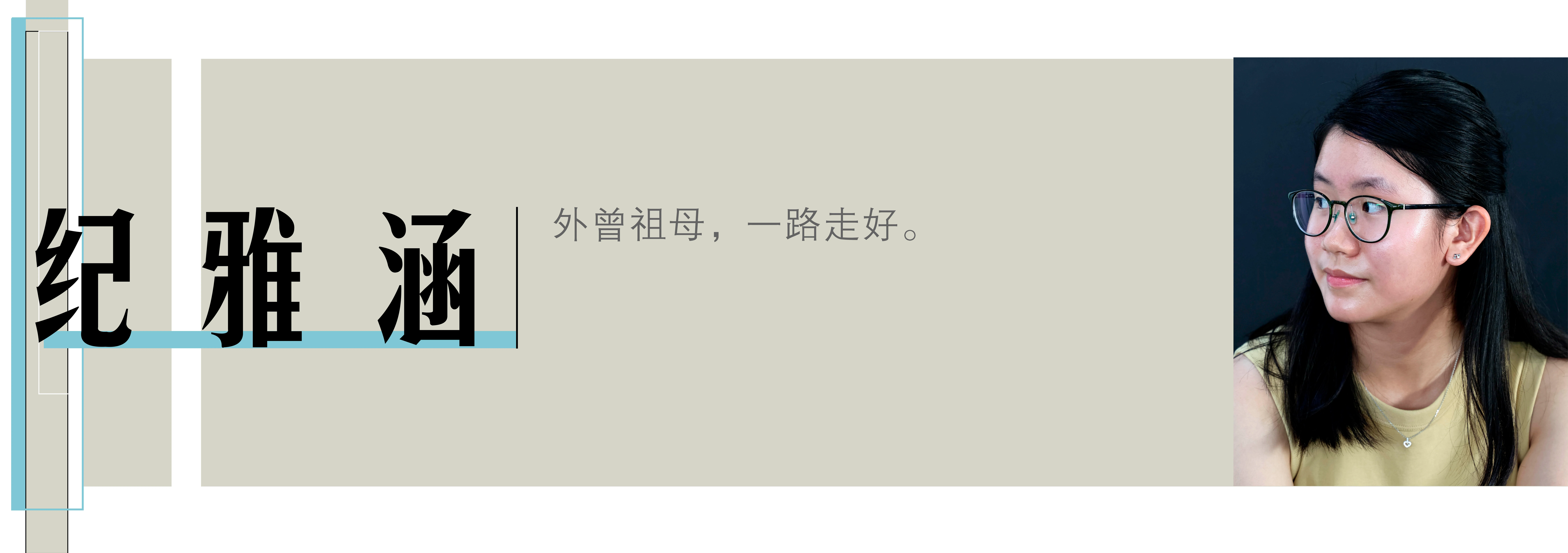我对她的记忆只停留在她高龄九十的时候。外曾祖母90岁之前,应该过着一个五彩缤纷的生活吧。
我和爸爸坐在椅子上,正对面摆着外曾祖母的遗照。这灵堂里面应该属我们最“外”了吧。我们一家常年住在新加坡,很少见到这些住在马来西亚的亲戚,每一年回马来西亚也不一定会见到。我在记忆中寻找着这一位位亲戚的踪迹,可有些还是十分面生。
即使不曾联系,大家都有默契地穿上一样的颜色。无论老少,无论辈分,大家都穿着红色的衣服。放眼望去,我们就像是一片红色田野,也像嫣红、紫红、橘红的炮竹。如果我不在灵堂,而是路人,一定会觉得这些人应该是迷路了。
在传统白事文化里,不同辈分的家属穿着代表性的服色来守丧,儿女辈穿白衣黑裤,孙子辈穿蓝衣蓝裤,曾孙辈穿青色,玄孙辈黄色,第五代穿红色。不同的是,外曾祖母是100岁的人瑞,所以丧事是依照笑丧的形式。子孙后代裹着红色的衣裳,象征生命延续、后代繁盛。
我从来没听过红色有这样的象征。红色在新年代表喜庆,在爱情里代表热情,在传统戏曲中红色代表忠诚、英勇和正义。生命的色彩如果是红色,这一生应该过得挺快乐逍遥、挺淋漓尽致的。
走出灵堂,去用餐时,有一位卖饼的阿姨见我们都身穿红色就恭贺我们,老长辈这么长寿。毕竟,能穿红色守丧的人应该不多。有多少人能活到100岁,又有多少人还和后代们有联系,能够号召数十人从世界各地来送自己最后一程。想来,真的不容易。
我从不曾觉得红色是那么稀有那么幸运。在我看来,最漂亮最独特的颜色所在多有,不只红色一个。况且,在科学上,颜色并不存在,只是大脑对不同光线波长的解读。
红色的波长却是最长的,浪漫地化做了生命力延绵的绒线,而这些绒线编织成一条红色的生命布条,作为我们的画布。
所以,生命本来就是红色的。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从母亲的红色血液中开始,白色病床床单上的一片红告知大家一个婴儿的出世。从牙牙班到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我们遇见许多一样流着红色血液的同侪,一起经历不同的故事。红色随着多姿多彩的经历变浅,和其他颜色拌在一起,逐渐变得更像其他的颜色,不再是红的。
红色一直是生命的底色,只是生活压力的灰色,对于未来不安的蓝色,在乎别人想法的青色,一点一点地把本来鲜艳的红色遮盖起来。在命运齿轮的操纵之下,我们不曾停下脚步查看自己的变化,只为学业、工作、家庭不停奔波劳碌。当我们身体逐渐衰老退化,并终于离开社会的轨道,其他颜色便悄悄褪去。像一幅油画,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后,底色早已被尘埃和岁月封印起来。直到有一天,世人找到这幅画,开始了还原工作。
一层一层卡在油画缝隙和表面的尘和灰被清除后,底色终于重现了。
不是神奇魔幻的紫色,也不是闪闪发光的金色,显现的应该是生命最存粹最初时的样貌——那抹红色。
我们总是期待白发苍苍,退休之际,能够重新寻获自己。到那时候,我们相信会有充裕的时间了解真实的自己。可是真正拨开层层装饰,找到那个红色的终点,需要多长时间呢?是否要活到100岁才能找到?
活到100岁的外曾祖母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红色画布。她把布条取下,分给了她的下一代,由她的子孙传给他们的后代。完成了工作,她便安详地睡去,长眠于大地。
回到新加坡,我打开平板电脑,开设新的谷歌文件,命名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