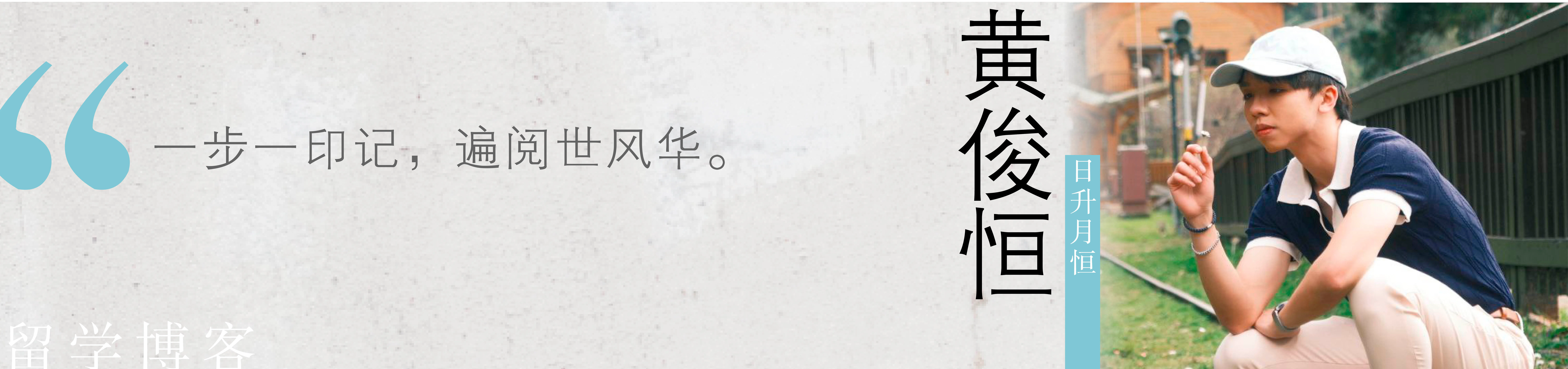6月中旬考试结束,我作为“大一新生”的身份也正式画上句号。在中国的第一年留学生活里,我经历了许多跳出舒适区的挑战,也在神州大地留下了不少足迹。趁着暑假短暂回家的空档,在实习和新学年的忙碌节奏到来之前,我决定前往一个心系许久的地方,放慢脚步,好好放松一下。其实这一趟旅行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在心中成形——目的地,正是彩云之南的云南。我的三位好友也特地从新加坡飞来,与我会合。
抵达昆明时已接近深夜,但机场依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当我踏出抵达大厅时,立刻在人群中看见一位显眼的男子,手举写有我名字的接机牌,手中还握着一束玫瑰,四处张望着我的身影。上车后,司机大哥便热情地滔滔不绝,给我们介绍起云南和昆明的旅游攻略。他自豪地说,自己15年前就来到昆明,是看着这座城市一步步发展,最终成为拥有中国第三大机场的大都市。
他看起来不过比我年长几岁,却在言语之间透出岁月的沉淀与人生的起伏。闲聊之下才知道,他来自中缅边境的瑞丽,初一时因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来到昆明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当保安,月薪还不到1000元。后来在朋友介绍下转行做了私人司机,生活渐渐稳定下来,也有能力寄钱回家补贴家用。
昆明确实为他提供了家乡难以企及的机会,但也让他在最年少轻狂的几年里,尝尽了大城市的纸醉金迷。他说,攒下点积蓄后,经常下班就去夜店蹦迪,虽然不爱喝酒,却会为了炫耀而豪掷上万元买下洋酒开台,甚至只是为了倒掉一整瓶。那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存下的钱也所剩无几。直到有一次在夜场得罪了人,差点被带进公安局,他才如梦初醒。
司机大哥坦言自己书读得不多,但对世界始终怀有好奇。从前,他觉得大城市的莺歌燕舞令人神往;如今,他更享受与来自各国的游客交流,聆听那些他一辈子可能无法亲自去探索的地方与故事。这份对世界的探索欲,曾一度让他误入歧途,如今却成了支撑他热爱工作与生活的动力。
此行的第二站是风景如画的大理,同样令人着迷。在洱海边,我们乘着马车穿梭于田野之间,看到当地农民赤着脚在地里劳作,弯腰插秧、松土、施肥……与一旁衣着光鲜、忙着打卡拍照、悠然自得的游客形成了鲜明对比。
偶然与一位农民攀谈,才惊讶地得知,他竟是马车游览服务的合伙老板之一。他告诉我们,虽然这里是热门的游客观光区,却依然是当地居民真实生活的地方。云南的旅游业发达,全面开发旅游资源、优化土地使用的确能大幅提升收入,但他这些年始终坚持下地耕作,自给自足,马车载客只是副业,而耕作才是他的正职生活。

同样坚守传统、延续祖辈生活方式的,还有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纳西族小部落。这个仅有82户人家的村子,位于云南通往西藏的唯一一条道路上。接待我们的是村中少数会说普通话的村民之一,也兼任导游。
纳西族是典型的母系社会,女性主外,承担养家糊口和体力劳动;男性则主内,学习琴棋书画、抚养子女。这个村子在1996年大地震前几乎没有与外界或汉族有任何接触。地震后接受援助,展开灾后重建,从而开启了缓慢的“汉化”进程。即便如此,村民仍保留着本族文字和传统文化,也依旧只与藏族通婚,不与其他外族联姻。
值得一提的是,村民几乎从不外出求医。生病时,他们会前往村中的东巴师父处就诊,按其医嘱上山采药、自行治疗。在外人眼中,这个村落或许显得闭塞落后,村民也可能被误解为不信科学。但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们的纯真质朴,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文化传承的坚守。
我一向不太喜欢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更希望能从普通人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地方真正的风土与人情。无论是昆明健谈的司机大哥,大理朴实的农民,还是丽江坚守传统的纳西族人,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所信原则的坚守。每一段旅程的收获都各不相同,而这次云南之行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求知之下,更重要的是认清内心真正渴望的方向。唯有不被外界定义,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在人生的奔波中,觅得心灵的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