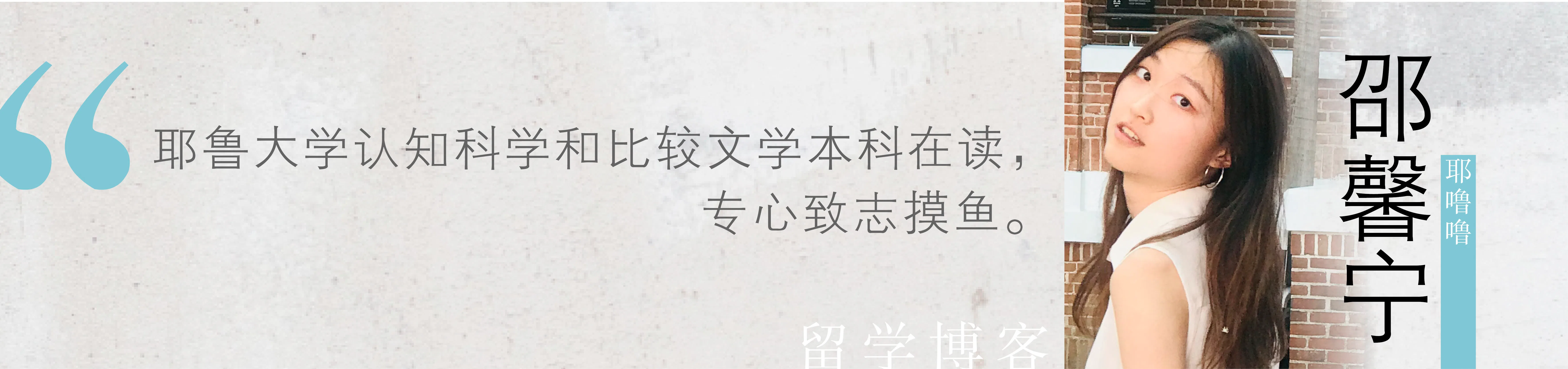在日本宇多津港口,我和朋友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装置:一个小盒子,装着摄像头和喷头,它叫“回声的气流”。岛上其他地方安装着传感麦克风,有人对麦克风呼吸,我们这里就会冒出泡泡。
我俩好奇地围在摄像头旁边,忽然喷头里咕噜噜冒出了一串肥皂水泡泡。对面有人!我们两个对着摄像头手舞足蹈和对方打招呼,没过多久,又有一串泡泡冒出。我们两个在不知来由的彩虹泡泡中,莫名觉得无比快乐。
后来在一家唱片店里,我们找到了麦克风。我对着它用力呼吸,一开始屏幕上没有人,只看到我自己吐出的泡泡。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短发女孩,她探过头来。我更卖力地呼吸,又吐出很长一串泡泡,她笑了,举起双臂,也卖力地朝我挥手,仿佛我不是藏在她面前的摄像机里,而是站在离她很远、隔着峡谷的山头上。
这样的游戏持续了一会儿,我呼吸,她挥手,我再呼吸。我忽然意识到,不管我是想说“谢谢你陪我玩”还是“很高兴见到你”,它们都只能变成一串长短不一的泡泡,她不会知道我想说什么,我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只能看到她模糊的表情。如果我要离开这场游戏,我没有任何方式和她道别。她会明白,一个短短的泡泡,就是“再见”的意思吗?
我跟朋友说,这个装置好悲伤啊。朋友翻了个白眼说,你好矫情。
确实,我们在的濑户内艺术祭并不是一个悲伤的地方。这周围都是小小的港口城镇和小小的岛屿。上午,在一座叫“本岛”的,人口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岛上,我和朋友惊喜地发现这里路上的猫都无比友好。一只奶牛猫横卧在马路中央舔毛,它抬头发现我们,先是一头栽下去露出肚皮,再哒哒哒跑过来在我们身边蹭蹭。可当朋友要伸出手摸摸它时,它在我们脚下打了个滚儿,站起来抖抖毛,径自走开了。
我很羡慕它的背影,悠闲的,头也不回的。我以为我自己最难以接受的只是不告而别,后来才发现,任何的“别”我都不太擅长。傍晚离开本岛时,当地居民举着应援牌,朝轮渡热闹地挥舞着:thank - you - see - you - again,最后是一个圆圆的可爱惊叹号。本来是亲切又喜庆的场面,我却只能怔怔地看着。按照朋友的话说,这非常像属兔的,她说小时候去宠物店,店员不允许任何人抱兔子,因为一抱它,它就会对人产生依赖性,人一走它就生病发蔫,上吐下泻。我说我觉得我这两年在外面呆得已经好多了,我现在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当代清醒都市青年。朋友说,是吗,那半年前我们在首尔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你在公交站——我赶紧打断她,别说了。
我当然没有在公交站哭。那天晚上我们乱逛到午夜,路边打烊的花店老板正在把剩下的花朵分发给路人,我们一人举着一支深红的玫瑰,走到公交站。她说,那我走了啊。我说好,到酒店跟我说一声。她走了,可是我实际想说的是,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我会想你的,我好想来东京找你,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但我还是会想你的,我好开心遇到你,哼歌我唱上句你就能接上下句——这个时候她从后面出现,拍我说,诶,我发现我耳机还在你包里。你举着花在这傻站着干吗?这是什么痴汉剧情?诶你不是要哭吧?不至于吧?
当然不至于,只是飞机里程数越积越多,脸上的晒斑越来越重,我不断地拾起什么,也被迫丢掉什么,像是站在一个漩涡中,有人来了,有人走了。在这一切流动之中,我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那个不知通向哪里的麦克风,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呼吸,看自己内心所有的语言变成一串泡泡,飘浮向陌生的街。我必须相信对面会有人发现这一串语无伦次的透明符号而出现在我面前,因为好奇,因为孤独。哪怕我们总是无法说再见。
还好,这些我们为彼此停留的时刻,总有回声。我真的来了东京。我正窝在朋友小小公寓的小小沙发里,等她下班回家。今天是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