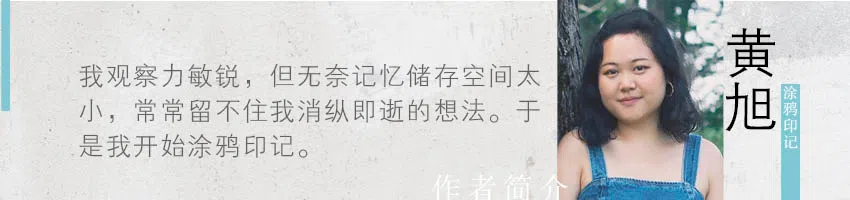
室友跟我说,去年有一阵子她在靠近高速那条路上,看见过一只被车撞倒碾压的浣熊。因为车辆在那个地点几乎无法安全停下来,那一个多月里,她看着那只死去的浣熊慢慢腐烂。越来越扁,像被城市吸收了,直到完全消失在水泥路上。
这个事件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巴尔的摩的山路上,我第一次看到被撞倒的一头鹿。查了查才发现,北美鹿与车辆碰撞是很常发生的事情,每年约有150万到210万起鹿车事件,受伤的鹿、人和车无数。
所以特别是夜里,我开车经过小路的时候总会小心翼翼,随时准备为一只突然冲出来想要过马路的小动物及时停车。不只是车,城市里也能经常看到因为撞上高楼玻璃而坠落的小鸟,它们的尸体散落在建筑旁边。见到的话,我会小心翼翼把它移到树下,或挖个洞,或用叶子轻轻盖着它。
这些逝去的生命很具象,让我感受到了人类在大范围改变环境。我们修路、筑墙、建高楼、铺光。这些行为是文明的象征,但是不是也在无形中重绘了其他生命的选择。当飞机缓缓降落,地平线上人类建筑的大规模几何图案很壮观。像鲸身上的藤壶,只是更方正、更密集,这是人类在地表的附着与占据。在被人类文明大范围覆盖的地上,动物们依然迁徙、穿越、筑巢。只是路径不一定通往森林了。它们在人类的居所里,成了城市的隐形居民。
我们常说要与自然共生,但是否这种共生更多是以人类为中心的“选择性共存”。我们允许树存在于街道中央,但不允许它挡路。不允许……挡路。山挡路了,于是我们把山挖开,做成隧道。
我深刻知道我是人类文明便利的受益者。我搭乘穿过无数山洞隧道的动车,从一个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到达另一座城市。城市的暴力往往是无意的,人类是否在重新定义“生物可以出现的方式”?
没有人想要撞死一只鹿,杀死一只鸟,但是交通、建筑、照明的系统本身是否意味着暴力的延续?是否是人类文明结构性失明?看见,就是抵抗。我随时停车为一只小动物让路;或将小鸟安顿。这些微小的举动,是我拒绝麻木的方式。
动物的死亡也在提醒我时间的速度差,对人类来说一瞬间的意外,对那具身体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消失过程。城市的时间很快速,而腐烂的时间却以自然的节奏缓慢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