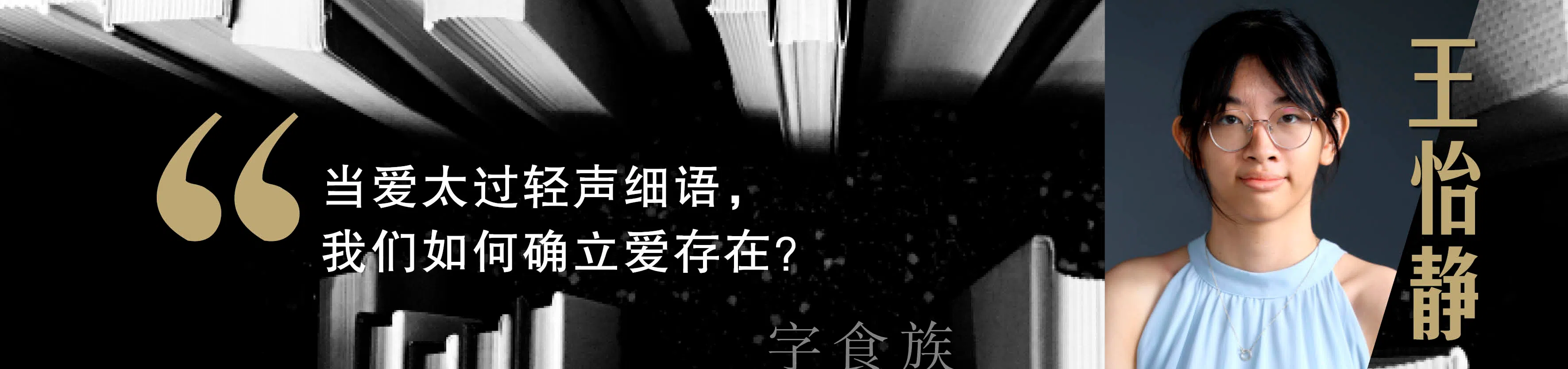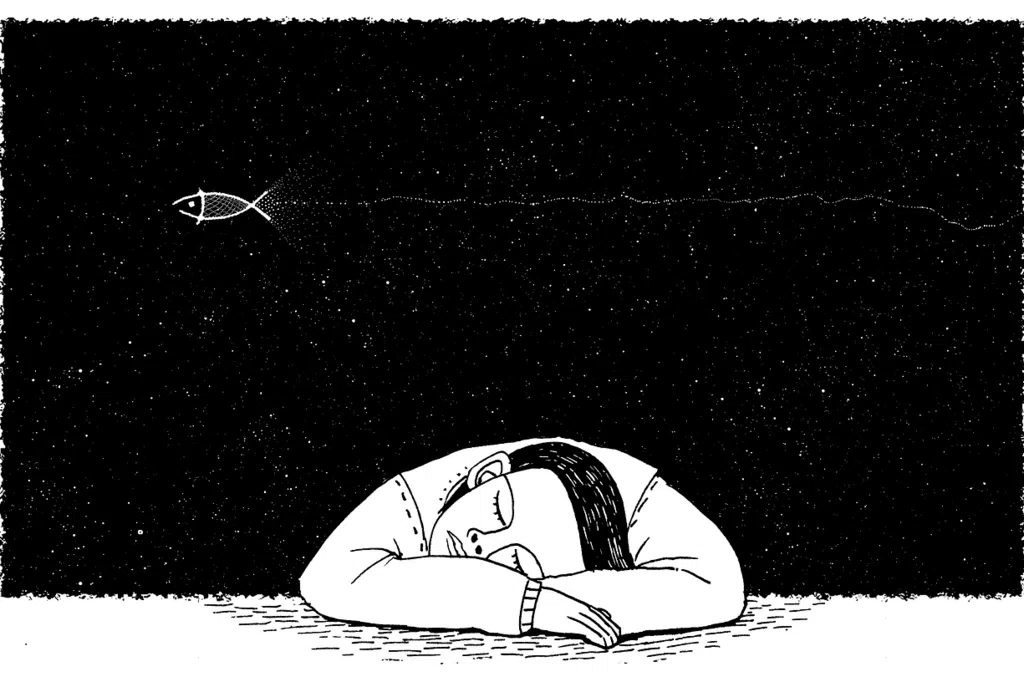她抱膝坐在床上,侧着脸看向窗外,那是一片死寂的黑、沉甸甸的黑,少数几道光亮像是酒瓶的反光。对面组屋仍有几户还亮着灯,暖色灯光中依稀可见一对夫妇正陪孩子看电视,播的是《小猪佩奇》,那粉色大吹风机的角色实在太有辨识度。脑补着他们的欢声笑语,她也不禁失笑出声,将头埋进双腿之间,身体缩成了一个三角立方体,似是想平静下来,毕竟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砰——”木门被推到墙上的声响,使夜晚彻底归于平静。只一瞬,房外骤然响起男人带着浓重沙哑的怒吼声。她像是被按下了静止键,环绕在胸前的双手颤抖着掐上手臂,留下一道道红痕。独自僵持了几秒,她扯过被子将自己掩上,把音乐声量调高,直到客厅的喧嚣变得模糊。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还迷失在路上
向另一个国度眺望
想重新活一场”
随着旋律的流淌,她的唇瓣一张一翕,“我要讨厌他。”她如此对自己叮嘱。屋外女人对男人卑微的祈求与隐隐啜泣仍此起彼伏。
隔天醒来,客厅中是扑面而来的酒味,稀稀拉拉的酒罐被随意地丢置在桌上、柜子、地台。男人熟睡着,打着鼾还偶尔骂街几句。女人仍是照常准备好标配早餐,一杯美禄配上几个自制的馒头,只是红肿的眼周与青黑的眼底还是昭示着,昨晚的一切并非梦魇作怪。她应声坐下,女人则随意地掏出塑料袋,沉默着到客厅拾掇。那天的白炽灯很亮,格外亮,照得她眼睛发涩。
那天的晚餐,女人依旧发着信息问男人会不会来吃,她默然地扒着饭,筷子在碗底打着圈,想为疑惑寻求一个答案:为什么仅仅过了十几个小时,每个人都会像无事发生一样照常生活,照常地爱着?是否只有失神了一天的她,才是那个异类?
当相同的戏码再次上演,又是为了莫名其妙的事,就在她中学升学考试开始前的两个月。她在书桌前坐着,看着眼前的数学试卷呆愣着,客厅震耳欲聋的污言秽语喧嚣着,将她脑中的三角图形篡改成圆形。
也许是年岁渐长后成熟了,她没有哭,握着笔的手也没有颤抖,偏偏,偏偏……
女人敲门而入,将她搂进怀中,“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女人拍着她的背,语调悲伤得像是常年被痛苦浸透。她奋力摇着趴在女人肩上的头,是想说“没关系”,还是“不是你的错”,她忘记了,可能二者皆有吧。她本不想哭的,可是不知不觉,女人背上的衣料依然被洇湿一片。
那晚,她与女人一同哼着歌,拥着彼此入睡:
“我的眼泪
止不住地淌
是因为快忘了家的模样”
“我讨厌他”,她如是对自己肯定。
大学毕业时,她身形已颀长,长发及腰,她与男人的关系却无半分好转,真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她曾尝试过与他坐下来,敞开心扉沟通,换来的却是一句“我带给你的苦难可能反而令你成长,说不定以后还要来感谢我”。
“失望透顶”,她在日记本上评价道。
“我不想爱你,我无法原谅你,因为那样曾经痛苦的我就真的孤立无援了。
我想讨厌你,我想恨你,可是,可是”
笔锋一顿,白色的纸张旋转着变换,浮现出男人年轻时托举着她大笑的画面,专门跑了两三条街买大白兔奶糖的回忆重现。画面一闪,男人为了她的毕业典礼,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出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在学校笨拙地从口袋掏出几颗毕业礼物递给她。合照时,相机闪光定格在男人望着她的那双,泛着闪光的眼眸。
“可是,我依然难以控制地心疼你,正如我心疼她的软弱。”
笔墨在纸上晕开,她不解,为什么男人佝偻的身躯会那般刺目,为什么他不会用网购软件而局促的样子如此可怜,为什么会觉得他在工地磨砺出的老茧和黝黑的皮肤如此令人安定。
是为什么呢?
“可是,我依然难以控制地讨厌你,正如我厌讨厌她的软弱。”
是为什么呢?
“是对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