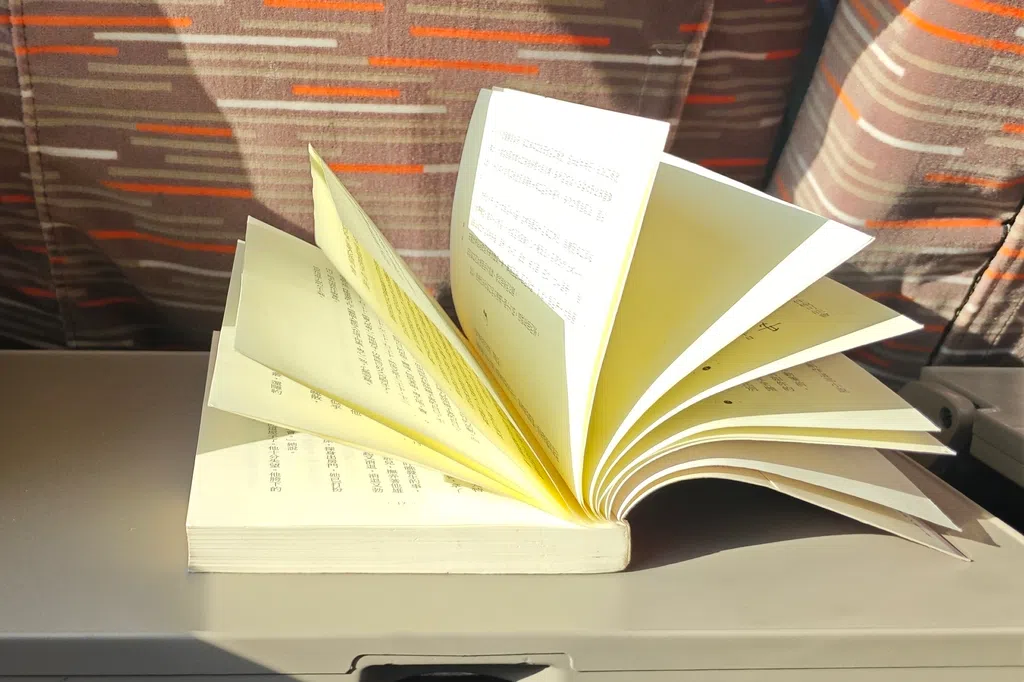我自知自己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并不可避免成为了一个浮躁的人。我无法抵抗流媒体算法精准投喂的那些不需要咀嚼的信息,在工作之外,看着不用费脑的综艺节目和没有什么深刻意义的电视剧。我很难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打开需要深度思考的内容,即使打开,也会很快被社交媒体分散注意力,然后卷入新的信息流。
但我并没有彻底放弃抵抗。
当本地影院有艺术影展的活动时,我会努力把自己关进电影院,让自己沉下心来观看那些难以被简化理解的艺术电影。
前段时间,得知附近电影院的即将放映《蓝白红三部曲之白》,我立刻购买了电影票。《蓝白红三部曲》是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在1993至1994年间执导的经典电影三部曲。我久仰其名。
三部曲以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命名,分别对应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白》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将“平等”这个宏大的政治命题,寄寓在一桩跨国婚姻的权力失衡中。电影开头,波兰理发师卡罗尔在法国的法庭接受离婚审判,他不会法语,无力地为自己婚后的性功能障碍辩解。离婚让他失去财产也失去身份,漫无目的流浪在法国街头。
艺术电影,常常不屑于如商业电影般调动人性的精准节奏和感官刺激。我感受到左右两边的观众,在这样沉闷缓慢的节奏中有些坐立不安。
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时,右边观众的手机响了。我没有想到,她竟接起来,还交谈了几句。或许是用这样的行为表达对电影的不满。
卡罗尔无暇顾及观众的情绪,人在低谷的时候无法同情他人。他历尽艰辛回到波兰,通过一系列计谋积累财富后,他制造了一场假死,以诱前妻多米尼克从法国来到波兰继承自己的巨额遗产。他在自己的“葬礼”后出现在前妻入住的酒店,以春宵一度证明自己并非无能,是平等的法国让他感受不到平等。他消失在了与前妻重逢的第二天,如此,波兰警方便会将卡罗尔的“死”与前妻联系在一起。她会被当作头号嫌疑人,会在波兰语的反复拷问中感受法语的无力,然后被关进监狱。
卡罗尔精心策划了一场对前妻的复仇,以颠倒的权利关系,争夺、证明和确认。右边的观众评价:“老登的临终幻想。”我以为她是在和同行的朋友吐槽,只是一时没控制好音量,便忍下了不适。
电影的最后,卡罗尔透过监狱栏杆,看着窗内的多米尼克,她用手语告诉他:出狱后,让我们重新在一起。也许他们初遇时就是如此,他们没有在法国,也没有在波兰,没有法语和波兰语之间的巴别塔,用质朴真诚的肢体比划着对彼此的欣赏和爱。也许这一切的确是卡罗尔的幻想,手语中的情感是幻想,真正的平等也是幻想。
散场时,右边的观众仿佛一刻也不愿多待,立刻独自起身离开影院,只留下一句:“妈的,和陈思诚有什么区别,都是男的在自恋。”
看来,她并非结伴而来,不知她的这些言论都是表演给谁看。
当今对文艺作品的讨论似乎陷入了这种极端,性别叙事成为唯一的批判维度,由男性主导的艺术被简化为“男性凝视”的产物,而所有女性批评又被反击为“女权过度”。
可是艺术不应该被简化,叙事不应该被简化,批判不应该被简化,关系不应该被简化,情绪不应该被简化。既然给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时间,看基耶斯洛夫斯基如何将浓缩的概念铺陈开来,为什么要在简化的批评里匆匆离开。
为什么不带上在电影院获得的一切力量,保持更丰富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