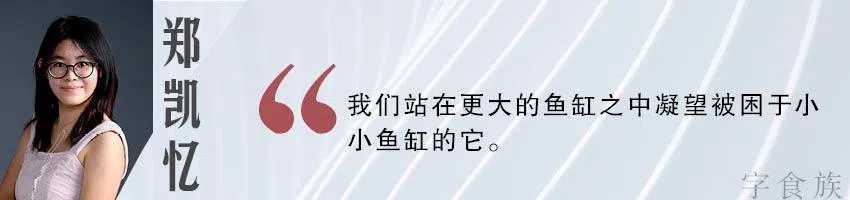小的时候,对于女孩来说,蓝色是一种特别的颜色。内心有一道不知名的推力,促使我偏偏不选择象征“标准答案”的粉色作为最喜欢的颜色。反而对与之相对的蓝色,抱持着一种连自己也不理解的痴迷和执着,好像喜欢它便能使自己令人敬佩。我喜欢任何一种蓝色。水、泡泡、鱼、梦——除了水族馆,它曾经大大地辜负了我的期望。当我满心欢喜地进去参观时,它让我十分失望。
我意识到那里虽然充满了蓝色,但都是骗人的,只有浑浊的水和劣质的蓝色灯光,无处不在。它使鱼缸中的水和空气里糜烂的蓝色一样,欺骗眼睛让人误以为我们与鱼没有距离。有一瞬间,我也有过恍惚,以为自己可以在水里面用肺呼吸,生活得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和它们作伴。但我们始终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它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N型鱼缸里,充满欺骗与不信任,好在鱼没有思想,不懂什么信与不信。
我将脸贴在廉价的玻璃上,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条鱼,是一条好傻气的红狮头金鱼。它贴得玻璃很近,我们之间只有一个倒影的距离。是我的倒影。我在水里看到了我自己。我看见我们以几乎同样的侧脸,面对对面同样深邃的另一块玻璃。同样微凸的眼球,死死以同样近乎完美的角度卡进眼眶骨里,是为了在某些允许松动的时刻,流入同样的蓝又流出同样的蓝。它继续游啊游,离我越来越远,然后越来越近,我知道它一直会在这几十平方米内为我停留。
等这里的灯愈发暗淡,眼泪慢慢溢了出来。是鲸鱼在我们头顶游动,庞大的身子随着它移动的每一寸吞噬阳光。水族馆短暂地陷进了微小的黑暗之中,依靠走廊边微弱的蓝色灯带,才能勉强看清周遭不真实的一切。本质上明与暗没有什么不同,黑暗带来盲目,而光明带来无知。太阳光到达地球大约需要8分20秒,大气层之下的人眼所见,其实永远带着时间差与偏差。为什么太阳光每一次折射出来的,似乎都只有七种颜色?有谁能证明它的真假,在它从太阳这个大球体出发的那一刻,在它穿过这个星球的层层空气和粒子交织成的大气层之前,有谁能高举右手大声证明它的真假?
周围的环境美好得如此不真实。刚刚好适合生存的温度和循环的水源,一个国家的孩子长不高的原因,难道要赖它被精心净化的空气吗?倒不如让原始的太阳用最直接的温度射穿我,在痛觉神经到达脑细胞之前,用你最真实的体温拥抱我,融化我,以及我身上堆叠的廉价塑料,哪怕这一切有可能让我走向死亡。我不在乎。像煎脆培根一样用滋滋冒烟的热气烫醒我,我不愿意沉睡。
我抬起头。鲸鱼早已不知踪迹。脚底涌来一股冰凉的湿意,鱼缸里黏糊糊的水不知为何淌到了脚边。之前那只好傻气的红狮头金鱼,不知何时在撞出了一枚洞,甚至跃了出来。它流了好多血,从它的脑袋流到了我的脚边,却仍然没有停止。它开始猛烈地跳动起来,用尾巴拍打着地面将自己腾起。眼球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快要溢出来的悲怨,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掉。小小的鱼而已,也会有自己的向往吗?或许它很好奇外面的河流和风景。或许它也想学习一门语言,也想从最基础的文字开始了解一些遥不可及的思想和事实。我的心底只是生出一股淡淡的无力感,我没有办法帮它。我们拥有着同样的命运,就连我呼吸的空气中,也漂浮着和它相同的蓝色。当我在外面看着它时,它又何尝不是在外面呆呆地望着我。
我不甘愿忍受这些,所以我真诚地求求你:让空气中的辐射不加修饰地到达我的肺部,使其像一棵野生大树一样枯萎;牵动着我的呼吸,带动思想与脉搏一同枯萎,再靠自己完成成长。我不惧怕它有毒,像一枚锋利的铅笔刀一样重塑我,使我可以刺穿任何一张空白的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