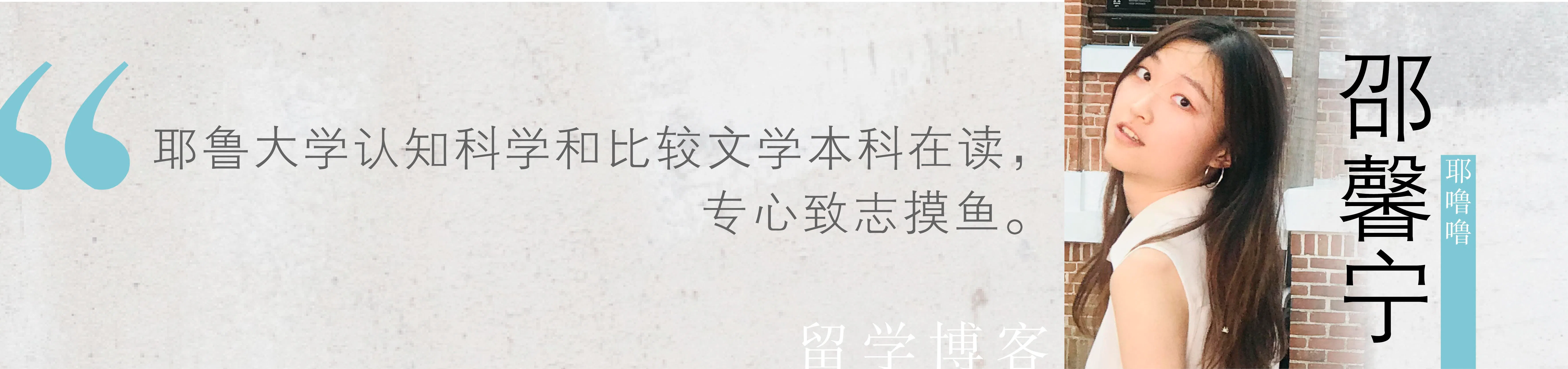时隔一年回到耶鲁,我一个人拖着行李,在寄宿学院门口吹着冷风站了很久。不是因为感伤,是因为一年前的门禁卡过期了,进不去了。
在学校认识的人已经不多了,找了一个朋友过来帮我从储藏室里搬箱子,他笑呵呵地来了,40分钟后,他哭丧着脸走了。在零下一度的天气里,把一个一米八的秘鲁精神小伙累得满头大汗,我抱歉地表示,我以为我的东西算是少的。他看了看堆满了纸箱、行李箱、小冰箱、置物架,以至于让人无从落脚的屋子,冷笑。
他问,我只想知道你那些箱子里到底都是什么?我很老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都是垃圾。我没敢告诉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回去之后累得诅咒我来着,第二天,我打开行李箱的时候,一个小黑盒子掉出来,精准砸到我的右脚脚背某条筋络上,剧烈的酸疼直冲脑门。我咬着牙把盒子打开,最先掉出来的是杭州某连锁超市的购物小票,2021年3月17日下午13:29。我再一晃箱子,哗啦啦掉出来一大堆:大一室友歪歪扭扭写的粉色便利贴:“给你买了泰诺和橙汁,我先去上课啦,你好好休息。” 一张已经褪色、认不出字只能看出是韩文的收银条。百老汇Our Town话剧的票根。迈阿密某酒店的房卡,拿起来之后下面带着一撮已经干枯的树叶碎末。
我掏出手机问ChatGPT:怎么说服自己丢掉没用还占地方的怀旧垃圾?
“如果你把每一个过去都物理化保存,你会没有空间让新的东西发生,”它说。我觉得它说的很对。我抓起一摊零落的纸条、卡片,塞进垃圾袋。很爽。最后一个学期,我要洒脱一点。不要总是拖着回忆长长的尾巴。我这样愉快地想着,拎着袋子下楼。学院的大垃圾桶朝我张着黑洞洞的大嘴,迫不及待替我消化不舍得放下的过去。
然后我拎着垃圾袋回房间,又把它们掏出来放回了盒子。
揠苗助长失败。没办法。也不是舍不得,只是丢不掉,下不去手。我跟我妈在视频电话里这样说。我妈在那边东北中午的大太阳底下散步,顶着呼呼的风声,说:丢不了就丢不了呗,过一会儿再丢。我很苦恼,说,那要是过一会儿也丢不了呢?我妈说,那就等你啥时候彻底拿不动了,再丢。
因为身体是不会骗人的。就像在首尔和一个朋友最后一次见面,分开的时候,她让我先走,我让她先走,两个人在地铁站入口对峙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走了,因为站累了。12月离开首尔的那个初雪夜有些仓促,于是这次回美国时特意转机回去待了两天,我想,要好好地再去看一眼所有熟悉的地方。结果第一天早上起来,刚在熟悉的菜市场带着忧伤而感恩的微笑徜徉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灰溜溜躲进咖啡店了。太冷了,把我忧伤而感恩的微笑冻在脸上变得僵硬又做作。我抱着温热的杯子瑟瑟发抖,看见墙上写着一句摘抄:“那些曾经拥抱我的时节,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可是我确实也还会在纽黑文一个晴朗的周日午后想起它们,想起离开首尔前一天晚上到朋友打工的便利店去找他玩,我透过一玻璃柜金黄的热狗、鸡肉串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一个满脸疲惫的中年男人进来,很认真地在糖果货架挑了很久,最后拿着三盒手指饼干、六袋软糖来了收银台,一袋香蕉味的,两袋草莓味的,三袋芒果味的。半夜11点,他下班了,我们出门,我想到还要处理我那些极有可能超重的行李,头疼。他说,哎呀,明天早上我陪你去机场弄,你赶紧回去睡觉吧,明天见,不对,一会儿见。
直到我转身,走到公交站,才想起来:这是我在首尔的最后一晚,也只是普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