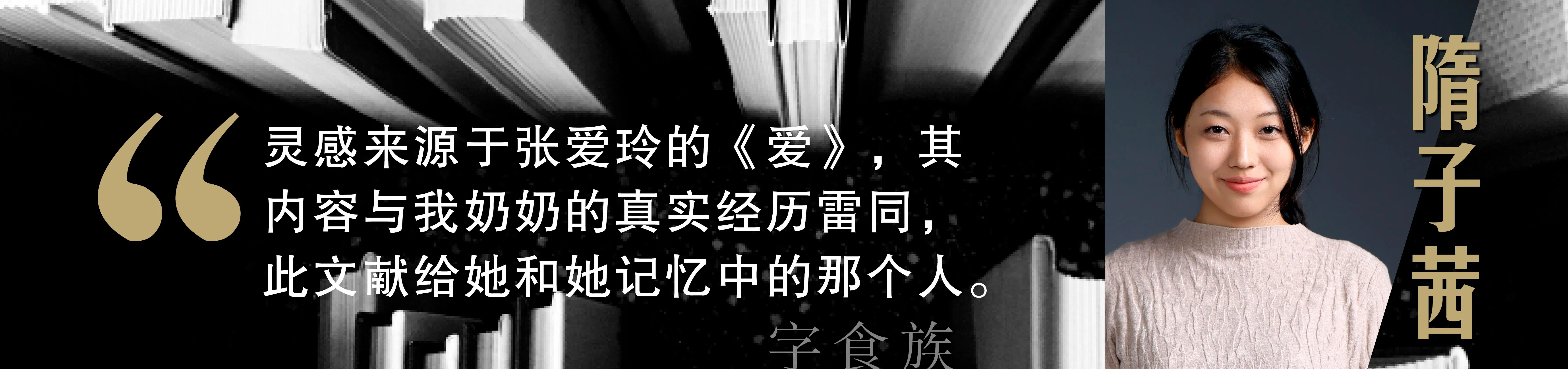女孩家所在的村庄叫山东大院。建国前,闯关东过去的人就都住在里面了,预备“再闯一次”。
村里就这么几个女青年,她最小,那年她十五,上学、打理家,闲暇之余和姐妹坐在台阶上望村里为数不多的“名人”。
男人二十出头,常着中山装,蓄长发,走路头发会飘,怀里总夹着几本书,那男人是已被录取的大学生。
女孩家,娘和后爹架吵得火热,口水溢出家门。一开始大家兴趣盎然,纷纷上前,劝阻的劝阻,围观的围观。后发现再怎样还要干正事,就把他们家事留给茶余饭后。到最后路过她家大门时,必要皱起眉头加快脚步。谁在外撞见女孩,包括她的姐妹花,都要先呆滞望上她几秒,再各自重塑表情语言。
在炕上,女孩和家人头顶头地睡,这两人互丢完碗盘还睡同一被窝。稀疏的发在后爹的头顶上盘成一个旋,随呼噜一起蠕动,月光把他的秃头照得油腻,女孩睡不着。
是不是所有男人最终都会变成这样,秃子矮子疯子二椅子。
这个地方,冬天要靠熬,而夏天是个好时节,这么穷脏差的,满地的土疙瘩。夏天一来,灰头土面的地方噗噗冒绿,挡都挡不住,要是再见到几株烂漫野花,心口的郁结也就自然消散了。
夜色浓厚,暑气渐褪,仗季节之势肆意疯长的杂草沙沙作响,早早酝酿晨晓的露珠。女孩被柳絮牵引着来到柳下。
男人远远地看到她就朝她走过来了,在这之前,他俩遵循村里铁律,只看,从未打过招呼。
“啊,你也在这儿吗?”
男人轻轻问道,嘴角微翘,但平时偷看他好像也经常带着笑。
女孩肃立,这是一个少有的让她觉得有尊严的时刻,命运好像突然很公平。
然后什么也没发生。那日晚梦伴随烧热的眼圈,蚊虫叮咬的瘙痒,朦朦胧胧。
次日父母骂战升级,不摔桌子不摔碗,改把襁褓的亲生小妹直接撇出屋外。女孩在一大堆眼睛下,一个人走出来又把小妹抱回家了。婴儿说不清为何哭得如此撕心裂肺,也好,女孩正挤不出眼泪。
这事儿像是个节点,从此空气中飘来什么东西,大家一同跌入一个坎。小学生回家帮忙炼铁,初中生去给人家贴大字报,大学生及以上的人,谁知道。这些个事儿到底有什么联系,一个接着一个的,剪不断理还乱,像猛地从河岸这边打个水漂,掀起一连串涟漪,甭管稳重踏实地掀,惊心动魄地掀,都沉不了底也碰不了岸。好宽的一条残忍的河。
她这种中专生,反而直接被分配进车间岗位,领固定工资。女孩第一次被爹娘一左一右牵着,昂首挺胸地送出大院,住进员工宿舍,和另一群算不算被命运眷顾的,面黄肌瘦的女孩睡在一起。
时间再也没有揪心的节点,早六点进厂,晚八点回房,月底给家里寄工资。剩下的大家凑凑,买来公用洗脸盆,下月买肥皂头,下下月买热水壶。凑着,拥挤的宿舍变得闹哄哄。
直到可以买一本小人书了,在女孩们磨起老茧的手中传阅,到她手里时,书上已到处都是手印。她百无聊赖地翻,巴掌大的书页飞速翻动,扑棱扑棱,书里寥寥几笔画出的小人物不得被迫跟上节奏,在指尖流动加速他们的剧本,猛地停在大结局的最后一页。女孩抬头,已正襟危坐在打理好的婚房里。
女子要有家就是嫁,这话她离开车间多年还在继续琢磨,镜中人早已褪去婴儿肥的脸上露出的疲惫,怎乍一看和娘还有些重合。
男人的结局不是秃子矮子疯子二椅子。哦,当然,他也没吃枪子。癌症,刚到三十。女孩躺床上奶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又能重上学堂的小妹坐在床边唠着家常。倏忽一个暌违十余年的名字,像外面任意一只无头苍蝇精准撞进耳蜗,刺得她疼,孩子咬得她也疼。
她还记得那一回事。有些话或许在嘴里含着捂着有段时日,也或许就那么顺着引力流落出来了。就那么牵扯出荡漾;就那么涟漪沾染着红晕,流不出河床;就流进急需养分的夏日下的土壤,助缘分在柳下生根,根茎无限延伸向你们。
然而谁都还对此尚不知情,生命的长河还未折磨得好叫人无语凝噎,只觉时间还长着,闷着,当下就这么偶然遇了,还是不要太轻浮了吧,唯有轻轻问候一句。
“啊,你也在这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