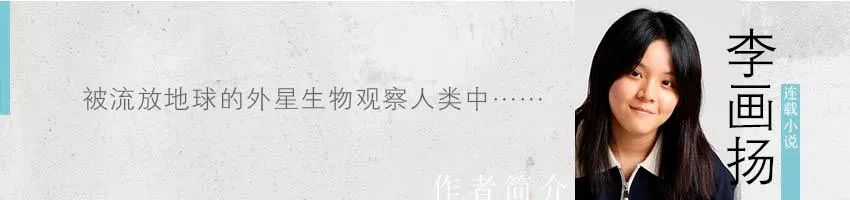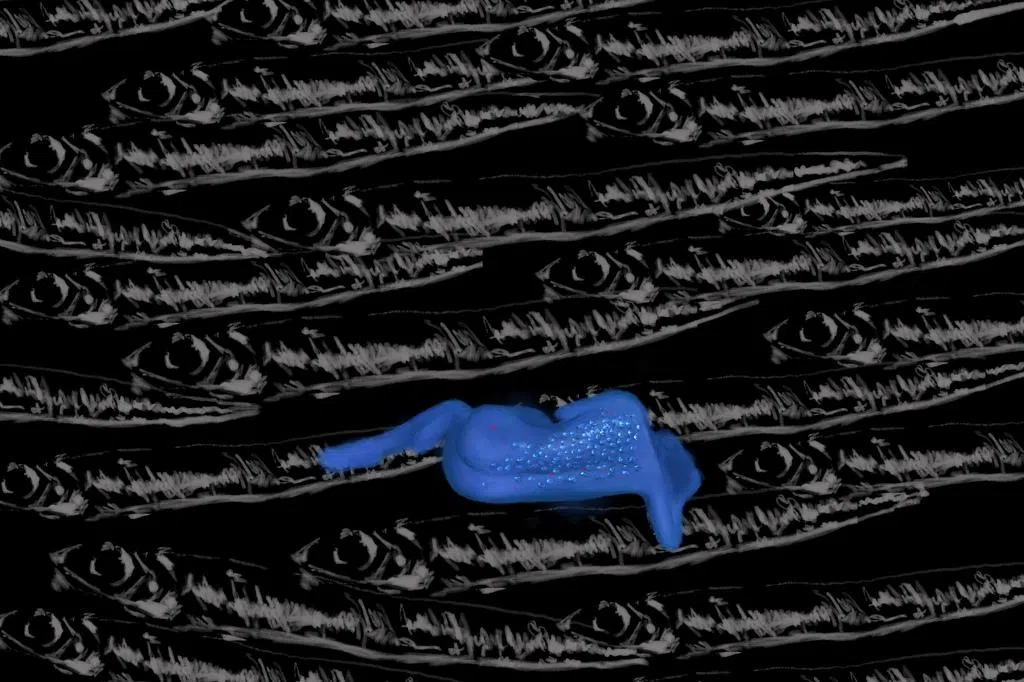4.
中一第三学期,我成为了张雅丽寄宿家庭里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从Jaden到许月见,后面几个月里陆陆续续加入了阿宝、小舒和Jessica。除了我和许月见外,要么是小萝卜头,要么是大点的小萝卜头。
阿宝,很调皮的小男孩。我记得最开始他年纪太小,当时女佣还要协助他洗澡。洗完后女佣走出来时,总是浑身湿透。他话又多又密,实在有些烦人。眼睛大大的,耳朵大大的,皮肤也很白。每周六他妈妈来接他时,总能看出他完全遗传了母亲的样貌。他妈妈是很温柔的一个女人,但面色总是苍白的。
小舒,是其他五个孩子里最后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她很安静,一个人看书、做题,存在感极低。又长又厚的刘海遮住额头,甚至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粉色的长方框眼镜。个子矮,皮肤黑,总是驼着背,脖子前倾,但也没有人去矫正。我从没见过她的家人,她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一直如此。
Jessica,对了,Jess。她很特别,她是台湾来的,和姐姐一起过来,但姐姐已经上了大学住宿舍,便只能让她来寄养家庭。她说话的语气很软糯,台湾腔很重。她开口跟我说第一句话时,我就知道她是哪儿人了。Jess是所有孩子中最活泼的,不是那种烦人的,而是总是积极的,带着笑的,像这间屋子里的太阳,被她照耀到的人都能感到暖意。她活泼又开朗,像一个小精灵。但我不喜欢她。要的话,就是我们大家一同安静,一同静默,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鲜活?这样明亮的人,才与我形成对比。太阳的光芒和炽热会灼烧我,而我或许只是一片过载的乌云。
我不排斥,但也不喜欢任何地方。出租屋、学校,或是张老师的家。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刚来到新加坡那几年,我总在幻想,若是我没有跟随母亲背井离乡,我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与文化截然不同,虽也有相似的地方,但终究差距还是很大。这里的学校没有裸露的红砖,厕所有门,设施完善。其实离开中国三四年后再回去时,原来的校园早已改头换面。原来的水泥地操场铺满了草皮和规范跑道,外墙重新粉刷,电梯也建了起来。若是我没有离开,那个环境或许也是好的。身边有一群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一同升上学校附属的中学,为高考拼搏。
到了新加坡,我才明白我或许不是活泼的人。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新的社会规则,一个孩子很难适应,而我又恰好只有自己的力量,于是这一切变得无比艰难。升上中学后更是如此。我上的学校不上不下,大多是本地学生为主,追着我不熟悉的热点,用着我不理解的缩写用词。因为我的学校离张老师家最近,我总是很早就抵达学校。早上六点半的校园,只有暖黄色的夜灯在清晨的风里飘摇,其他的只剩下沉寂与黑暗。这样的时刻,是我无法逃离,只能面对的。每一天在这样的清晨里,像刮骨疗伤,一点点剃去我原有的底色,逼我允许新的文明化作血肉。但可惜,我的身体依旧产生排异反应。我还能这样下去多久呢?热带的雨有时也像漂白剂,我什么时候才会完全褪色。但又为什么要变得洁白呢?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在想这些,但为何这份痛苦总是我独自消化?
是在这个时候,许月见感到了与我一样的悲伤。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或许,我们总是这样半褪色的孩子,总是孤立无援的孩子,才能看见对方也是一样的。她比我来得晚,她能怀念的资本比我更深厚。我们像两条混进热带鱼群的淡水鱼,游啊游,还是会呛水。
有好多事情,说起来真简单。多读英文书,多讲英语,多交新朋友,多出去玩一玩。真的可以这么简单吗?要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中一的课业并不繁重,大家都忙着竞选学生理事会的职位,或者在新社团里刷存在感。上课时打打闹闹,顺手做完不算难的功课。我最不喜欢新加坡学校的一点,就是有过多的小组活动。若是没有这些该死的小组活动,就没人会发现我其实是没有朋友的,而不是那个看起来高深莫测的人。道理我都懂,但为了合群去虚构一个不存在的自己,假装融入,真的很滑稽。
其实我也积极参加所有活动,好像那样就能褪去之前的皮,长出与其他人一样的皮。我更愿意待在学校里,总想尽办法留到最后,才不得不坐上张老师的车。寄宿家庭不是不好,但也说不上好。一回去,我们就做作业,吃晚餐,排队洗澡,整理第二天的书包准备校服,睡觉。每天都一样。只是很少有人说话,我们都保持安静,因为张老师总是有很多话要说。她关心家里发生的一切,大到为什么这个月水电费贵了,小到阿宝不会画的数学model。
相处几个月,我们并不了解彼此。我只跟许月见说话,其他孩子在我看来都太幼稚。她是第一个来的,隔断房建好后,她选了最贴近墙的地方。后面来的孩子陆陆续续占了那一排床,而我只能睡在竖着摆放的那一张床垫。我们和其他孩子的交流,只停留在生活日常上,比如教小学生做作业,或者争论谁先去洗澡刷牙。
而意外往往是不打招呼就来的。小舒的零用钱丢了。虽说平日的饮食起居都在张老师家,但在学校里总要吃饭买文具,这些零用钱张老师是不管的。小舒很确信自己没有乱花,也没有在学校里弄丢。因为她从来都把钱放在钱包里,而钱包也总是收在书包同一个夹层,她很少拿出来。于是,嫌疑人便只剩下我们五个人。
那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客厅里还没有装上监控摄像头,寻找“真凶”就像破案。那一晚没有晚餐,张老师只是说,在找到小偷之前,谁也不许吃饭。我们沉默地坐在没有食物的餐桌前,默默听训。等到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响了,还是没有人承认。张老师撂下话说,如果明天一早没有人认错,早餐和晚餐也不会准备。那一晚,谁都没睡着。灯熄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
“谁干的自己承认,不要连累其他人饿肚子。”许月见率先开口。她是这里最大的,又跟张老师有亲戚关系,平日她说话还有些威严,但此刻却没人接话。
“是我妈妈给我的两张十块钱。要是被我妈妈知道钱弄丢了,她会打我的。”小舒带着哭腔的声音在黑夜里响起,带着颤抖和慌张。她永远波澜不惊的表情,在今天也失效了。
“快点吧,到底是谁。早点认错早点解决,这也不是什么大错。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明天大家都有饭吃,行不行?”其实我对他们都不了解,只是我不喜欢饿肚子,不喜欢这样压抑的氛围。若是能早点结束,便万事大吉。
“不是我。”
“不是我。”
“也不是我。”
“难道钱自己长腿跑走了吗?不要再撒谎了,谁偷了就自己承认!”许月见控制不住拔高了声音。外面响起张老师的脚步声,她似是要来查看情况。我们连忙躺下,把被子裹紧。张老师开门的声音却迟迟没有响起。门口防盗门打开的声音传来,是张振川回来了,声音听着像是喝多了。两人在门口交谈起来,似乎是在吵架,但声音不大,推推搡搡地进了卧室。即使这样,我们也睡不着,每个人心中都各自打着算盘。
半夜十一点半,隔断房的门被敲响,是张振川。他只是象征性敲了敲,便推开了门。扑面而来的是浓重的酒气,混杂着胃里翻涌过的酸腐味。他轻声唤:“小舒,来,过来一下。”
小舒想要装作没听见,但客厅的灯光随着门打开照了进来,她颤抖的睫毛出卖了她还醒着。她只好揉揉眼睛,假装被吵醒的样子,迷迷糊糊地看向张振川,全身止不住地颤抖。张振川拿出两张十块钱,包住小舒的手,将钱放进她的手里:“这二十块,当作你自己的就好,拿好了,不要再弄丢了。”说完,他摸了摸她的头。那股难闻的酒气依然散不开,一直到他离开房间,也萦绕着。那一晚,我们都是伴着酒气入睡的。
不仅是小舒,我们谁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张振川要出来补上这“被偷走”的二十块钱。也因为如此,我们似乎永远都不会知道谁才是那个“小偷”。第二天起床时,张老师的脸很臭,她经常这样。她文过眼线的眼睛平时看上去就像在瞪人,本来就有些凶,刻意摆出臭脸时更是带着压迫感。但好在,早餐还是有的,哪怕依旧只是简单的面包牛奶。不知道她究竟是不满没抓到小偷,还是对张振川的行为有意见,抑或两者都不是。
偷钱事件之后,张老师总会提醒我们睡觉前把钱包收好,不要乱放。她还强调,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像这次那么简单了。
而我们六人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在这件事之后,也都默契地各做各的。只有年纪小的阿宝和开朗的Jess还会拉着其他人一起聊天打闹。空气里确实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但我们都装作若无其事。
(待续·每月第一个星期五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