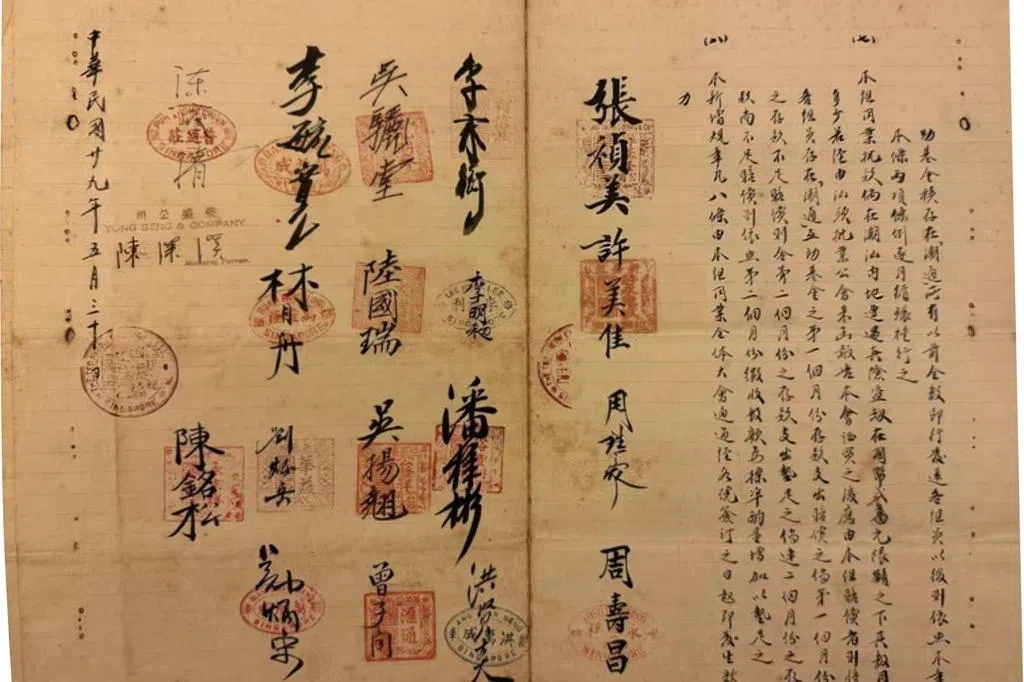俞肇斌(60岁,Uncle Tommy)剃光头发,只留下前额一撮。他笑说,因为常常要紧急出任务,没时间打理发型,但要让人看得出自己是有头发的。
这位长得有点“江湖味”的公益服务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娓娓道出自己如何从一名曾打算到乐龄中心挑衅的“红山混混”,一路转变为服务弱势群体的“红山孝子”。这段跨越40年的经历宛如一部长篇连续剧,他讲得生动,记者听得入神。
从上门警告变成守护者
俞肇斌和家人在1980年搬到红山。小时候他不爱念书,自嘲从小一到小五争着拿倒数第一或第二名,单单小学就读了九年。十出岁他就出来工作,当咖啡仔和木工学徒。住家附近红山弄(Redhill Close)第14座的红山老人活动中心,不时传出中西乐吹奏声,对年少气盛的他来说,是一种噪音。
“有一天我决定去‘警告’他们,先是在窗口张望。活动中心负责人出来跟我解释,说一个星期只有两天,让年长者从事一些爱好和兴趣,希望我忍耐一下。
“负责人好声好气地跟我说,活动中心内都是六七十岁老人家,我听了都不好意思,哪里打得下去。当时刚好一名30多岁男子,也凶神恶煞来投诉很吵,我觉得有必要保护他们,站起来说‘你要打他们,先打倒我。’我长得比较高大,样子又很凶,那个人就离开了。”
从此以后,俞肇斌和朋友们经常在活动中心外聚会聊天,形成另类“保护网”。有人致电到活动中心通报附近组屋有老人家跌倒、晕倒或打架,他们也会跟着去帮忙。
那一带住着很多孤苦无依的红头巾、妈姐和贫困老人,离世时只有简单搭篷和一副棺木。他和朋友常去帮忙,因此对殡葬流程有所了解。

成立义工队探访年长者
一些老人家因为生病或需要更多照料,转移到医院、疗养院或老人院,红山老人活动中心的任务告一段落。俞肇斌说:“我们之前一直在关心他们,突然不闻不问,我觉得不太好,也挂念他们,就和朋友们分批去探望。”
由于他们不是这些长者的家属,有些医院或看护中心会询问来自何处,俞肇斌于是在1986年成立“爱心团结”。当时他自己不过20出头,学历不高,薪水只有200元,凭一腔热血带领一批青少年从事公益活动。
这个团体后来越来越有规模,约有40人,介于十三四岁至20来岁。它在2003年正式注册为“爱心团结义工机构”(Love & Unity Volunteers Establishment),如今约有30名固定义工。
探访组每个星期到红山和女皇镇,陪伴年长者唱歌和运动,并协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需求。另外,机构会不定期组织活动,如带年长者出游或欢庆佳节。俞肇斌希望借此鼓励待在屋内的年长者出来活动,认识街坊邻居。

俞肇斌原本经营承接锦旗和布条的丝印公司,1996年开设祥红白服务。他说:“有钱的,我们可以赚钱。没有钱的,我们才出钱。”爱心团结义工机构的经费全凭大众乐捐,他本身则以商养善。

一站式送孤贫老人上路
爱心团结义工机构的能力和资源有限,目前只能接受四个机构的孤苦无依往生者。一接到电话,无论几点,他都会出动,先以公司车辆去接收遗体,载到新民路寿板店处理,遗体入棺后由玻璃灵车送到万礼火化场;累积五六个个案后,再安排捡骨及海葬。
“虽然是义务性质,我们整套流程做足,毫不马虎。像是领着骨灰去海葬途中,会说‘安哥(或安娣),要过桥了’‘要上船了’‘一路走好’。没有家庭的贫困单身人士,很多都担心自己走了之后没有人送终,我能做的是尽量让他们安心,而且不分种族和宗教。”
尽管本身是殡葬业者,俞肇斌送走一名往生者,花在棺木、火化场、海葬船和车油的费用,加起来至少要1300元。每年处理二三十个个案的费用加起来相当可观,他很感激“新加坡众弟子”的慷慨解囊,不足以应付时,他则自掏腰包。
俞肇斌常感叹时间不够用,希望一周能有八天。如今32岁长子已逐步接手成祥红白服务的生意,也帮忙义务处理后事,这几年他才有机会出国游玩。但俞肇斌从未能跟太太及三名子女全家出游,因为他和长子得轮流在新加坡待命,无论是自家生意或义务丧葬服务。
无人接手或关闭机构
与新加坡同岁的俞肇斌,40年来凭一己之力带领一群义工,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送上关怀,并为他们处理身后事。
往生者的手表、传呼机、手机等物品,火化前必须取下,他都妥善保存于家中,作为纪念。如果有人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送出,但很少人敢接受。正如他如今坚持做的义务丧葬仪式,仿佛是一只烫手山芋。
他感慨地说:“这个机构是我成立的,肯定会负责下去。讲真的,有谁会愿意这样付出?24小时一通电话就全家出动,出钱又出力,有人还以为我从中赚到多少,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倘若有一天他力不从心,孩子又不愿接手,这个机构只能随之画上句号。
“红山孝子”这个称号很沉重,但俞肇斌无怨无悔。要侍奉一对父母尚且不易,他却数十年如一日,把数百名老人当作自己父母,以实际行动关怀他们的身心健康,更在人生终点站出钱出力送他们最后一程。















千帆过尽才发现,壮龄正美丽。关注壮龄go! 特制内容,加入壮龄go! 社群,一起过好人生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