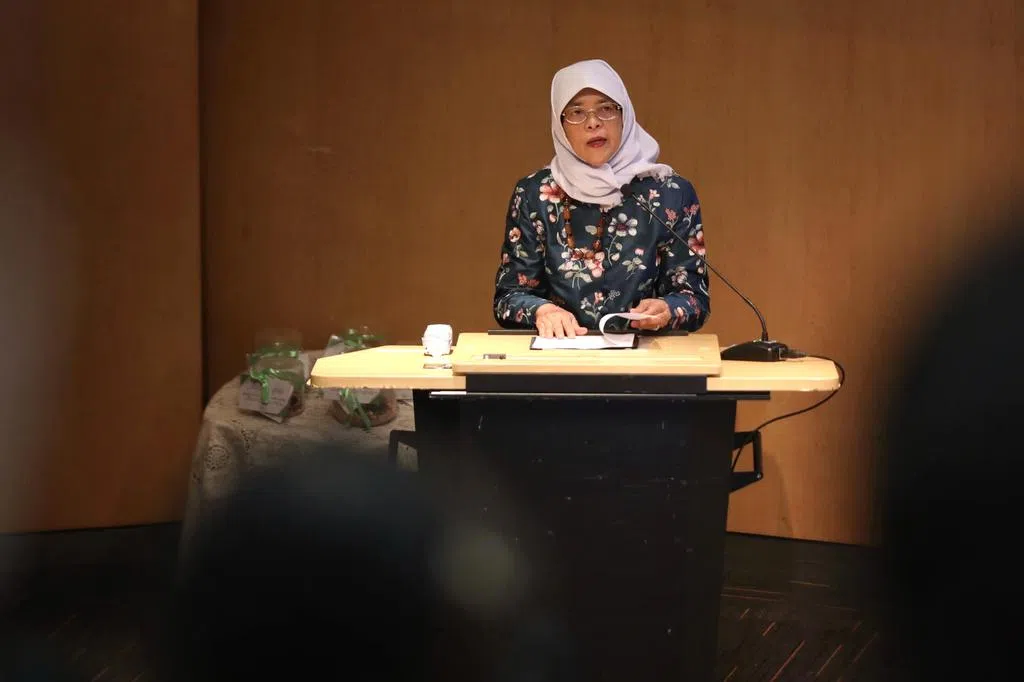已故高级税务官生前原将独立式洋房留给女儿,一年后改立遗嘱,把洋房及全部遗产转给儿子。女儿质疑父亲因失智丧失立遗嘱能力,上高庭挑战失败后提出上诉,但上诉审判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新遗嘱有效。
这对印族兄妹的遗产纠纷中,上诉审判庭三司确认2012年的第二份遗嘱具法律效力。上诉审判庭认同高庭法官观点——第二份遗嘱订立过程的确显得仓促,也存有疑点,尤其答辩人(儿子)在遗嘱草拟过程中高度参与,最终还成为唯一受益人;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推翻遗嘱的法律效力。
三司指出,答辩人的确曾催促父亲尽快改立遗嘱,可能引发遗嘱是否反映父亲真实意愿的疑虑,但并不代表父亲当时缺乏立遗嘱的能力。
三司:两名证人证实 当事人改立遗嘱当下头脑清醒
三司认为,上诉人(女儿)无法证明父亲于2012年立遗嘱时缺乏能力;而答辩人则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父亲清楚知道并确认遗嘱内容。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两名见证人的证词。证人甲是立遗嘱人友人之子。甲回忆称,签署遗嘱当天,立遗嘱人头脑清醒、精神警觉。证人甲看完遗嘱后,曾提醒立遗嘱人,除了答辩人将获配百分百遗产和洋房之外,其余四个子女的继承份额设为0%。
立遗嘱人当时瞪了甲一眼,回说:“他是我最疼爱的儿子,他会知道该怎么做。”当日,甲和立遗嘱人还闲聊约半小时,并未发现立遗嘱人生病,或缺乏理解能力。
另一证人乙也证实两人的对话。甲乙都证实,遗嘱人当时神志清醒、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
三司据此认定,立遗嘱人明白自己的决定,并有意将遗产留给答辩人。
涉案洋房位于东部的奥匹拉住宅区(Opera Estate),市值约700万元。
立遗嘱人生于1922年,曾任国内税务局高级税务官,学识渊博,精通英语,通晓日语、福建话、淡米尔语等五种语言。1957年,他曾在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半工半读法律课程,六年课程仅完成四年,却已掌握遗嘱相关法律,因此在立遗嘱时不愿另付费雇律师协办。
立遗嘱人有四男两女,妻子和长子已先后去世。高庭审讯时,另三个子女供证,三人形容父亲权威严格,重视纪律,子女成年后仍心存畏惧;他固执、意志坚定,常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子女身上,子女如果无礼顶撞,会遭父亲掌掴。
晚年他独居洋房。上诉人住在附近,常为父亲准备晚餐并陪同就医。
两份遗嘱仅相隔一年 上诉人难证父亲短期丧失判断力
2011年10月,父亲立遗嘱,将洋房留给女儿,并明确排除其他子女继承权。2012年11月,他另立新遗嘱,将洋房及全部遗产转给儿子,完全剔除其他子女继承权。当时,他仍能独立理财。
2015年2月,他在外迷路跌倒,被警方发现后送院,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并伴随游走行为”,自此病情恶化,至2019年3月去世,享年96岁。
上诉人声称父亲从2012年1月起已出现失智症状,2012年11月已无立遗嘱能力,并引用三份病历,指父亲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症或血管性失智,影响判断和理解能力。
然而,三司指出,上诉人未传唤医生或医学专家解释病历中的医学术语,也未证明父亲记忆衰退的程度,或为何父亲的判断能力会在短短一年内骤降至完全丧失。病历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父亲在2012年11月改立遗嘱时,能力已受到严重影响。
三司由上诉审判庭的王少凌法官、施奇恩法官,以及高庭法官洪清福组成。三司驳回上诉,并令上诉人支付5万元讼费给答辩人。判词并未公开遗嘱人、诉辩双方和见证人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