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泥炭地仅占地球表面的3%,但全球陆地中储存的碳,有高达31%储存在泥炭地中。遗憾的是,泥炭地被不断开发,东南亚的泥炭地更是重灾区,数据显示,1980年代以降,94%东南亚泥炭地受到砍伐、林火等天灾人祸的破坏,新加坡国立大学团队正努力研究,尝试复育区域内的泥炭地,减缓碳排。
热带泥炭地综合研究计划(Integrated Tropical Peatlands Research Programme,简称INTPREP)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所主任、生物学系副教授桑杰·斯瓦鲁普(Sanjay Swarup)所领导的跨领域研究计划,与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合作,动员35名研究员、15名田调人员,分别在两个总面积达3500公顷的废弃泥炭地,实验复育森林的方案,研究泥炭地中的微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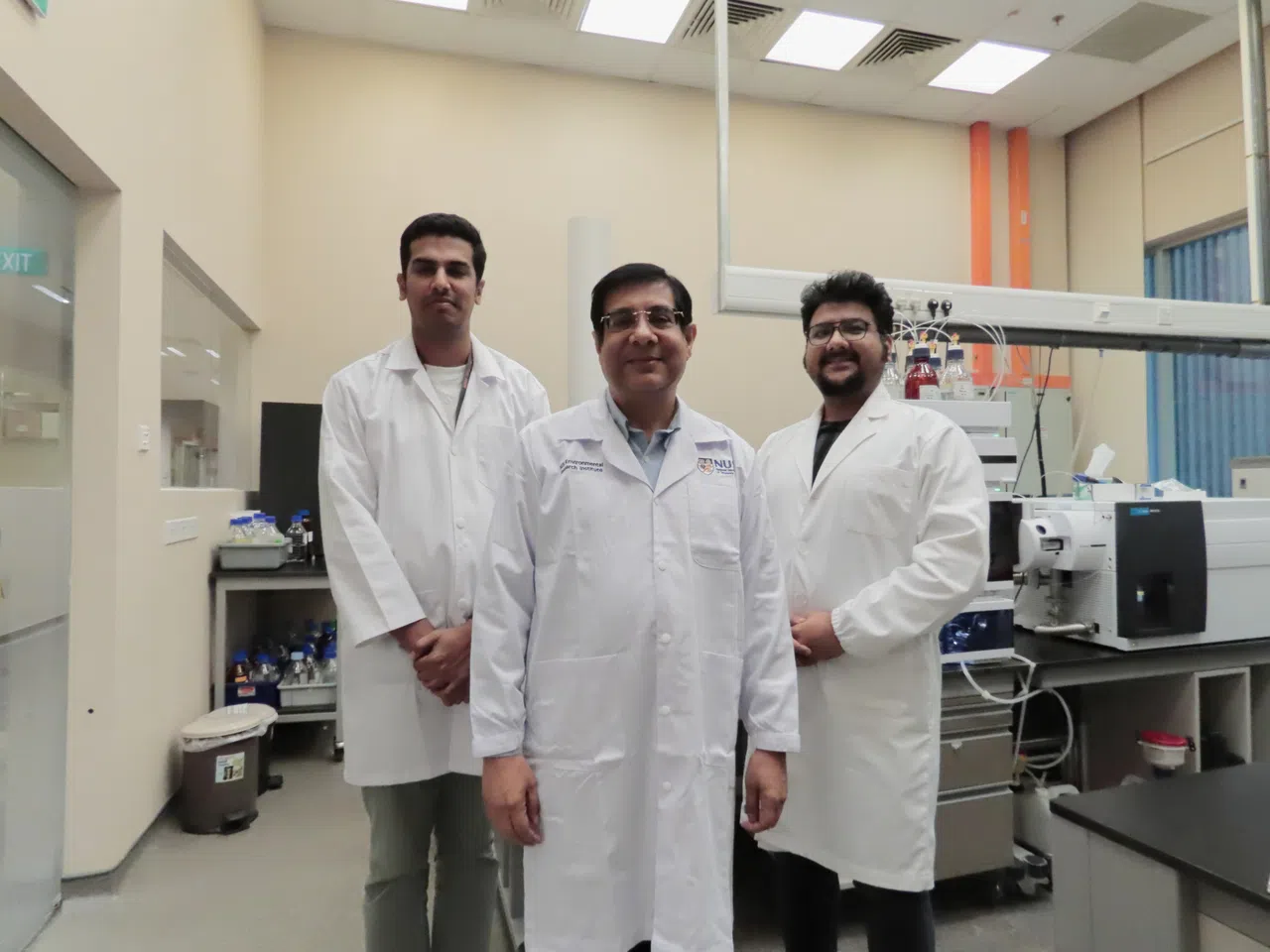
协助桑杰的高级研究员阿迪亚·班达拉(Aditya Bandla)博士说,第一阶段研究发现,重新为泥炭地表面灌注水,经过七年努力,可以将泥炭沉降量从每年7公分减少至1.5公分。研究人员估计,如此一来,每年每公顷土地可减少6.4至23.6公吨碳排。
桑杰受访时解释说,动植物死后沉积在沼泽底部,潮湿有机物质分解速度极慢,日积月累形成泥炭层,封存了碳等有机物质。当人类发现泥炭地适合种植油棕等经济作物,首先必须抽干泥炭地的水分,当水分流失,泥潭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气,里头的微生物就会开始工作,将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同时也有部分碳随水道排入河流最后进入大海。这系列过程中排放出来的物质都会影响水中的其他生物,造成连锁反应,其后果难以估算,这也是为什么泥炭地的保育与复育在极端气候变化的当下如此关键。
桑杰对泥炭地的研究已经超过15年。他说,过去20年,新加坡不时受烟霾影响,这都与邻国的自然林火、人为烧芭有关。他认为新加坡可以扮演科技与资源的中心,协助区域解决这一问题,于是积极投入研究。
此外,他指出开发泥炭地也会增加水灾的风险,因此保护泥炭地也能保护地方安全与经济。
桑杰说,泥炭地在自然界中扮演缓冲水流的角色,一旦失去泥炭地,大地便失去缓冲的滤筛,大水轻易漫漶。
借助人工智能加速资料分析

不幸中的大幸是,泥炭地是可以被复育的。
桑杰说:“我们都在冠病疫情中认识到大自然快速的复原力。”
2015年印尼一家纸浆公司将3000公顷“退役”的泥炭地清空,让自然修复,提供土地给研究团队观察哪些物种以何种顺序重新“占领”荒置的土地,最后研究人员记录了超过300种泥炭地植物,当中还有三种植物是新物种。
研究计划如今来到第二阶段,桑杰与团队正打算扩大范围,除了印尼,也要与马来西亚、泰国等周边国家合作。第一阶段收集的资料,在第二阶段也要通过人工智能加速分析,目前正与国大遥感中心(CRISP)、国大人工智能院、国大自然气候方案研究中心合作,发展AI工具与田调方案。
对桑杰来说,进行科研寻找保育方案需要时间,短则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但科研计划的资金周期往往只有三至五年,此外合作的政府单位也因为大选周期,增加了变数。
“这是我们的责任,让合作伙伴看见一个明确的长期研究路径与方案,同时也有短期的研究结果。”
桑杰也指出,开发土地是为了经济,保育工作者亦不能乡愿地一昧禁止砍伐,必须提出平衡的方案,更必须与当地伙伴合作,才能有效保育泥炭地。

泥炭地森林物种多样
泥炭地森林物种多样。三年前,团队就曾遇到野生苏门答腊虎,桑杰说:“我们的吉普车前方大概十多米处是一头老虎,它盯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动,当地的工作人员以印尼语窃窃私语,不敢声张。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老虎离开,我们也穿过森林。”

还有一次森林里的花集体盛放,形成前所未闻的香味,让团队记忆犹新。
将泥炭地森林变成生态旅游的景点,一方面刺激地方经济,另一方面保护环境,桑杰认为也是不错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