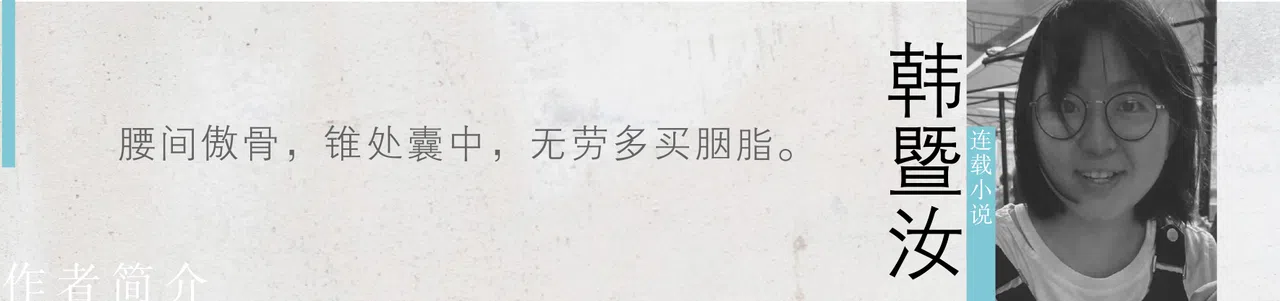故事简介:大约几万或十几万年以后,世界依旧被化分成许许多多个小个体,那怎么会没有流血漂橹、兵戈扰攘呢?高树所生活的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的腐败与权力争夺的混乱,外敌入侵时求生存的抵抗。而他所处其中,自然有了许多思考,也难免面临着种种艰难的选择,比如沉默或是反抗,适应或是改变,生或是死。有时他希望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局面,追求他心中最理想的社会;有时他又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他是太过渺小的存在。你权当在哪里拾到了他的日记,看看他的一生。
(二十)
母亲笑了:“走错了不是仍有沿途的风景么——” 在这个梦的开端,母亲是年轻时候的样子,身上还带着盈盈的脂粉香,发髻里簪着她最喜欢的白玉兰花。
在半梦半醒间,他哽咽道:“可是,阿娘,我倦极了。”
母亲的手抚上他的脸,他真真切切地感知到了一种触觉。可是,霎时间,母亲的手不再是柔荑似的了,手上的皱纹血管像枯藤般纵横交错,母亲的样子也变老了,悲哀的神情就浮现于她干涸的、久病得可怜的脸上。高树盯着她的手看,试着理清这些生命的纹路是如何交错的,一切皆得有个起源,方才有终点。
他知道自己是要醒来了,慌忙哀求道:“阿娘,再陪陪我吧!”
“你且走你的路罢。路上有何等奇绝的风景,又有几多的憾事,几十年后,你亲口讲与我听。” 她悲悯地回应他,像是将柔光撒向人间的菩萨。
他睁开眼,天蒙蒙亮了,再睡已是不可能。
他不知道梦里的是母亲,还是躲在母亲影子中的自己。
无论如何,这使他坚定了一些。早晨还是惯常用了些白粥糕点,之后他便开始一封封地写信,首先写的是将要递给司令部的,翻来覆去实则仍是之前那些话,在信的最后,他决计拿出些态度,甚至写出了如若逼不得已、自己势必要递辞呈一类的话。信刚递出去不久,就有人来报,说是堤坝已经给炸了。他盯着桌上那一沓子纸发呆。凝了凝神之后,他又开始写,要求拨款赈灾,这次竟有了回应,虽责怪他越级,但到底是应下来了。
他早知道自身言轻的主要原因: 他走了一条捷径,与其一步步从下往上地做起,体会民生之艰,他往往借助着机遇走到了今日的位置。这机遇里几分是后天的天时地利人和,几分是他出生时就已然决定的社会关系,谁也说不清楚。讽刺的是,相比于固化的社会,战乱反倒是更加民主的体现,出身草莽者亦能成英雄,且死亡常常增进了机会,更快地促使了上层社会的更迭,今天这个战死了,明天就会有另一个补上。而他这样的往往不能使人信服。
他陷入了一种迷惘当中,越想棘手的事越觉着倦,转而想着怎样部署城防,却也陷入了死胡同里。他站起来踱了几步,刚想接上思绪,又有人来通知说,半个时辰以后南营靶场边上集会。他烦得紧,去的路上迎面见着了平常谈得来的同僚,也不理人家,只匆匆点了个头,自顾自地疾步走着。
这位同僚倒是好脾气,快跑几步追上他,调侃道:“谁又惹着你了?”
“一天到晚不得安生。谁知道这回又是什么事。”
对方讶异:“你没听说?要处置假传军令的副官。怎么说来着的?儆……儆……” 他“儆”个半天,高树替他着急,不耐烦地打断对方:“杀一儆百?杀鸡儆猴?以儆效尤?”遂又有些好奇地问:“哪个副官?”
对方不紧不慢地回答:“这不知道,不过既然是赵将军下的命令,自然是他的副官了。你不是读书人吗?你猜猜是哪个副官。”
高树嫌他无趣,但三个里头挑一个,他有多于三成的把握,便随口说道:“我猜那个最高的,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两人一路打趣着,高树的烦恼竟也暂且消了大半,等到了的时候,靶场边上的空地早就乌泱泱一片人了。
那天天气怪讨人厌的。梅雨的季节,阴沉沉的天看不见层云,像是叫瓦匠铺了薄薄一层灰水泥,压得人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