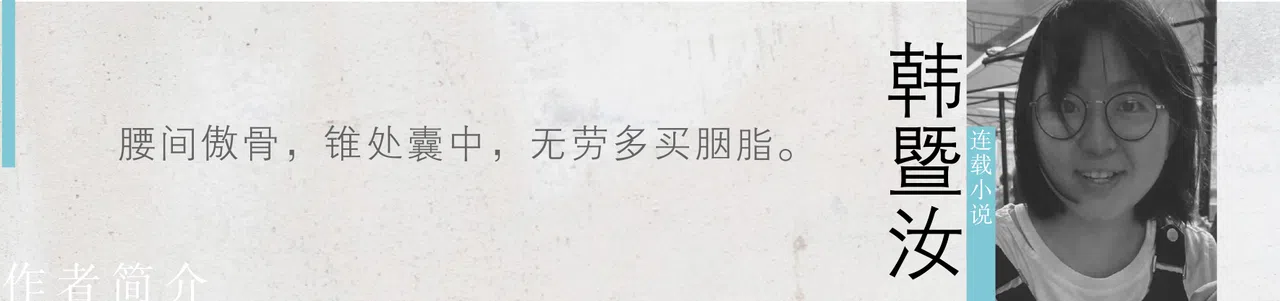故事简介:大约几万或十几万年以后,世界依旧被化分成许许多多个小个体,那怎么会没有流血漂橹、兵戈扰攘呢?高树所生活的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的腐败与权力争夺的混乱,外敌入侵时求生存的抵抗。而他所处其中,自然有了许多思考,也难免面临着种种艰难的选择,比如沉默或是反抗,适应或是改变,生或是死。有时他希望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局面,追求他心中最理想的社会;有时他又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他是太过渺小的存在。你权当在哪里拾到了他的日记,看看他的一生。
(二十四)
赵远山见他忙不迭地想着场面话,反倒笑了:“我其实并不在意。” 二人虽在大大小小的事上有许多分歧,但临别之际来得突然,高树此刻全念起人家的好来,加之高树得以从他身上窥探自己所期盼的、沉默中的无我无人之境,当下便直言道:“多谢你的照顾。”
高树以为自己越来越不擅长分别了,有许多话来不及说,但若真给足了时间却又如鲠在喉,在赵远山即将转身离去时,他又叫住他,无缘无故地问道:“你觉着世间有对错之分吗?”
赵远山似乎知道他有未讲完的话,在回身之时便想好了答案似的,缓缓答道:“对错是个人衡量。个人衡量里却难免掺杂着他人看法。但没了对与错就好比没了指南针,人又恐惧失去方向,所以世间一定是有对与错的。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恐怕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了。”
高树默了半晌,方才道:“他日再见时,我或许就会懂了。” 他其实想明白了。那晚,他从陈桐城处离开,回到自己的窗前,盯着窗棂外面树枝交横的影子,仿佛身处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他对赵远山的处理方式是愤怒与不解的,但无论赵远山有意与否,事后回看全局,他的做法似乎仍旧是最优解。对与错,我之所见同你之所见,是树枝与树枝间的错落纠缠,还是像树与树影一般,处于平行的两个世界,虚实分离,却亦步亦趋?
多年以后,他仍旧会像当时那样整夜地思考。
他后来又见过赵远山,两个人过得不算不如意。攀谈间赵远山提起陈桐城的死讯,其滞后感使高树觉得时光被无限地压缩,直至薄如蝉翼。他听着他平静地陈述事情的经过,却好似感受到湿冷的雾气,整个情景在他眼前徐徐展开:
陈桐城以为自己已经趋于平静。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终结,是无边的黑暗,如同他所处的社会一样;在黑暗的垂怜里失去眼界意识界,或许也是一种祝祷。可当这一刻比预想中来临地缓慢时,他竟然感知到了不可避免的恐惧与不舍。
黛青色的天就要亮了。他再一次看了看四周,在愈来愈模糊的视线里,他看见了隐在雾里的遥远的山,郁郁葱葱的树,有些潮湿的泥土,是刚下过雨吧。
天就要亮了,他是知道的。他听见山上簌簌的虫鸣了,山上的僧人或许要从难舍难分的睡梦中睁开眼,在有些冷的清晨里舀水、洒扫,偶尔有几声鸟叫,究竟隐匿在春山的哪个角落。
他的心里蓦地生出一种希望,也许他不会死——毕竟,没法见到日出是一件多么遗憾且残忍的事。而当天亮的时候,光就会给山与树与云镶上一层金边,将一种稳定的永恒撒向人间。那么,彼时他也会像孩子一样虔诚,匍匐着接受这种恩赐。
“天……亮了吗?” 陈桐城有些急切地问。
天还没有亮。天就快亮了。山寺里,僧人辗转反侧,已经要起身了。
“还没有。”赵远山俯下身回答道,“但快了。等你睡醒了,我们到山顶上看日出。”如果要是在山顶上的话,可以看着太阳如何从天边撕裂一个角,悄无声息地在这座小城构出的底板上晕染,在丝毫没有云翳的、湛蓝的天上倚马千言。不知不觉间,天就会亮了。
陈桐城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爬山看日出,茫茫然不见山顶,在半山腰停下听风吹过松树的声音,而天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间亮了。
赵远山听见他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了,他的嘴唇已经完全没了血色,干裂地像未曾开垦的广袤大地,了无生机。然而生机正蕴藏在其中,等待着下一个春天:“桐城,睡吧。等你醒了,我们去山寺里,求今年也顺遂平安。”
陈桐城渐渐没了声响。长久的沉默。就在赵远山将要起身离开的时候,陈桐城突然用尽全力似的,想说些什么。赵远山凑过去,听见他最后喃喃说:“天又凉了……您的大衣在柜子里,熨好了。”
然而此时此刻,天真的快亮了。黛青色的天过渡成了群青,远处的山看得清楚了。
山寺的钟声传来,在亘古的悠悠的天地里,很快就被淹没了。
(每周五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