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这个月,我们开启对话,让年轻的字食族,两人一组,寻找彼此要探索的主题。这一期昭然与思媛写了杜鹃的故事。杜鹃可以是花可以是鸟可以是人,总有无远弗届的可能,在两颗心的触碰下,故事就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一)
杜鹃从小就生得水灵,眼睛黑白分明,睫毛翘得像村口槐树上的鸟窝。她的皮肤白皙,带着一点麦子的光泽,村里人都说,她的美是天生的,像田间随风摆动的野百合,不用雕琢,也能引人注目。可杜鹃的美丽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妈妈总念叨,叫她少在人前晃悠。说闺女家家的,长得再俊又能咋样,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丽丽听不明白这些。她只晓得自己天天梳着那根油亮的大辫子,穿着哥哥们褪了色的旧衣裳。只要在学堂里不太落后就好。
她的童年像一条蜿蜒的小溪,清澈见底,却也平淡无奇。
那年,杜鹃16岁,夏日炙热如火。她正蹲在田埂边抓泥鳅,满手泥泞。她的裤腿卷得高高的,脚上沾满了湿漉漉的泥土。脚趾在泥水里摸索,浑身湿漉漉的。她的头发被汗水浸透,几缕贴在脸颊上。杜鹃正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捞一条泥鳅,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哒哒哒,像是敲在石板上的音符。她抬起头,远远地看见一个身影,白得晃眼。只见,那女人穿着一件修身的连衣裙,腰肢纤细,裙摆在风中轻轻摇曳。她的步伐轻盈而优雅,每一步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味。杜鹃愣住了,手里的泥鳅滑落,溅起一片泥水。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美得让她心生敬畏,又忍不住想要靠近。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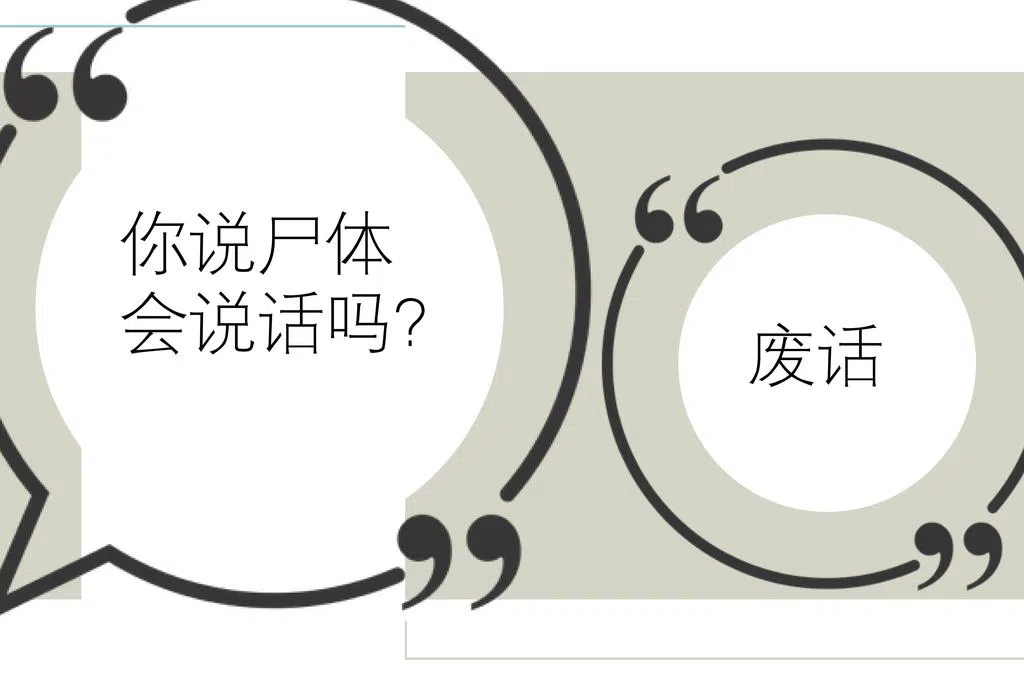
那女人带着一股不属于这个村庄的气息。
村子里顿时炸开了锅。女人们围在一起低声议论,目光中满是揣测;男人们则悄悄打量着她的身影,眼神探究不定。有人在背后嘀咕,说她举止妖娆,怕不是在城里干着见不得人的营生。母亲站在门口,脸色阴沉,冷冷地吐出一句:“那个狐媚子,怎么回来了?”
这个狐媚子,竟是自己的小姨。

杜鹃起初与村里人一样,对这个花枝招展的小姨心存戒备,甚至带着几分不齿。她的美过于肆意,像一株不合时宜的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孤傲地开着,惹人侧目,也惹人忌恨。然而,小姨并未因那些冷眼与流言退缩。她以一种近乎温柔的固执,悄然走进了杜鹃的生活。
她用旧床单为杜鹃裁出一条合身的连衣裙,针脚细密,仿佛缝制着一个未曾启封的梦。她轻声道:“女孩生来就该美丽,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活得更有尊严。”那声音柔和,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如一缕风,拂过杜鹃的心田,掀起了某种沉睡已久的渴望。
她偷偷教杜鹃化妆,用一支廉价的口红在她的唇上晕染出一抹淡淡的嫣红,再用指尖轻轻抹开。每次母亲回来前,杜鹃都得匆忙卸掉妆容,仿佛这一点点精致都是不该有的罪证。但那短暂的美丽已在她心中扎下根,成为暗夜里悄然生长的光。
夜深时,她们并肩躺在炕上。窗外的月光泻进来,为她们的低语镀上一层柔和的银辉。小姨讲起城里的故事,讲那些高楼大厦、霓虹街巷,讲那些自由自在、活得毫无歉意的女子。她的声音让杜鹃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女孩不该被困在锅碗瓢盆里。”小姨说,“她们应当有选择的权利。她们可以去爱,可以去恨,可以去追逐自己的梦。”
杜鹃渐渐明白,小姨从不憎恶那些墙角窃语的妇人。她们不过是土地与男人捏塑的影子,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消磨了自己的轮廓,最终沦为牢笼的一部分。小姨真正厌恶的,是那些躲在女人们身后,披着道德外衣,行苟且之事的男人。他们用鄙夷的目光丈量她,用贪婪的欲望窥视她。他们的恶意织成无形的网,试图将她困住,让她收敛、低头。可她从未屈服。她仍旧站在风口像一株无人问津的野花,不惧尘土,不畏风霜。兀自生长,兀自盛放。
闷热的夏夜,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田野深处的炙热。忽然一场倾盆大雨席卷而来。
回家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杜鹃冒着雨跑回家,刚到家门口,就看到小姨狼狈地从屋里冲出来,眼里噙着泪水,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雨幕中。那一刻,杜鹃的心跳骤然加速,仿佛预感到了某种不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