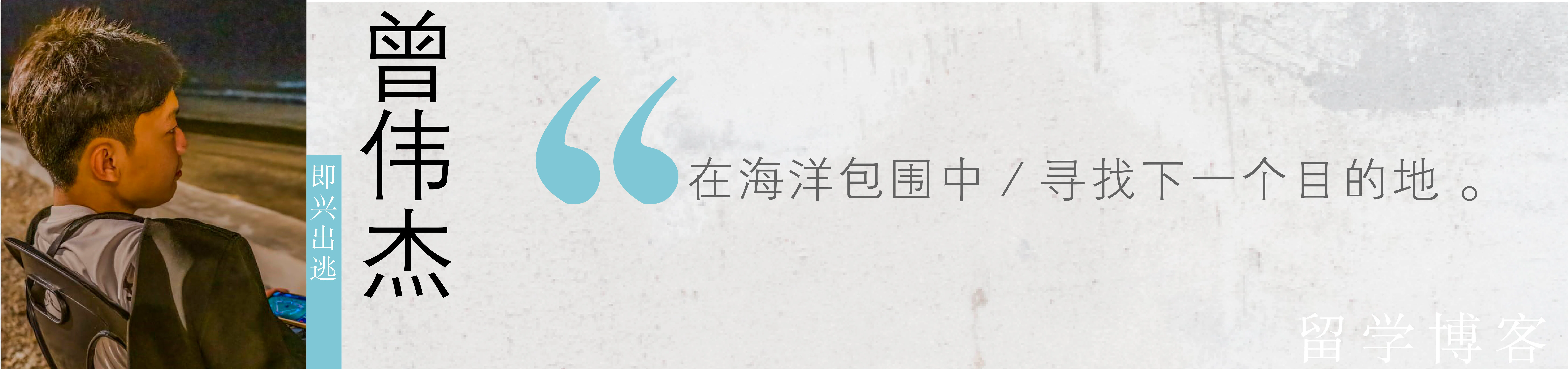从博雅教学馆走出,天空碧蓝无云,我踏进一片温暖而不炽热的阳光中。风吹来,树叶轻轻摆动,已不似月前的凌厉。连日阴雨过去,台北总算迎来名副其实的春天。春光难得,放晴的醉月湖畔引来不少游人于此散步、休憩,有同学索性躺在草坡上,用外套盖着脸沉沉睡去。
我沿着湖畔慢慢走着,心想自己还需要些时间,练习直接躺在草地的勇气,最终选了个小石墩坐下。几只鸭子在粼粼湖光上划出悠哉的水痕,情侣在树下相互依偎,老人坐在长椅上喂鸟,耳后传来排球场上学生打球的欢笑。耳目所及之处,没有人背着书包、紧皱眉头、行色匆匆。像是收到某种感召,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享受这亚热带的春天。
在国大,我不曾有过如此悠闲的时候。按理,我应该同公园里的其他人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片平静。
但望着湖面光影浮动,某种沉积在心底的情绪,在不知不觉间被搅动,浮起。
在一片春光之中。
——
“为什么决定去交换?”
这个问题我听过很多遍,家人、亲友……都问过。
人们总觉得,每个决定背后就一定有某个明确的原因。至少,离家四个月,总该有一些目标吧?比如看看世界学习独立,接触更多知识……这些听起来都站得住脚的理由,其实都说服不了我。
所以我每次的回答都不同。
虽然想去交换的理由模糊不清,在目的地的选择上却没花太多时间。我很快决定前往台大,理由有三:台湾是中文环境,有朋友在那里深造,台北有许多书店。这三点构成我不会客死异乡(精神上)的充分必要条件。
于是,我很快填好申请表格,未作过多犹豫,便点击提交。
——
着陆后,从桃园机场到台北的捷运上,透过一样是长方形的车窗往外看,入眼的已不是五颜六色的方格子,而是一片辽阔的森林、农田、乡镇。进入城市,公寓和工厂开始出现,建筑的外墙老旧暗淡,是熟悉的台北灰色调。这是这座城市长久以来被诟病的。但我非但不觉得丑,反而因18岁时造访这里的记忆在脑中涌起而感到欣喜。
新生活的模样开始具象化,我开始认为,我可以在台北找到些什么。本来讨厌出门的我,开始沉浸于探索城市:到阳明山上赏樱,在中山的狭窄巷弄漫游,在大稻埕的书店、咖啡馆或书店咖啡馆间钻进钻出。
我拼命填满时间表,不留空隙。
——
就只是为了事后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
物理上的距离并没有把我,从我想要逃离的地方,带走。
因为方程里最重要的变量,我,没有改变。
回顾当初收到交换录取通知的那天,我正被迟来的青春期焦虑和早到的quarter-life crisis双重夹击:一段即将走到尽头的感情,一段无法连接理想和现实的人生。在面对和逃跑之间,我选择了逃跑。
交换,是一个好得无法挑剔的借口。
于是,我决定接受录取通知,在想好交换于我的意义之前。毕竟,“意义”这东西,总是可以事后再用冠冕堂皇的话粉饰。
因此,哪怕这意味我大学最后一个暑假很可能找不到实习工作。
哪怕我会因此离她3000公里远。
哪怕我根本不知道逃跑之后要干什么。
我也要逃。
——
下课铃响起,排球课结束,耳后的欢声笑语蓦然止息。草坡上躺着的同学站起身,拍掉草屑背起背包,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
风依旧轻拂,阳光还是温暖,湖面的波纹依旧。我没有急着要走,我知道我还有一些时间。春天很快便会离去,而几个月后,我也终将离开这里。回去之后,这样的午后将不再属于我,坐在湖边发呆的余裕,也不会再有。那既然如此,就好好把握这片春光。
如果最终无法找到什么,那至少,也应该学会放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