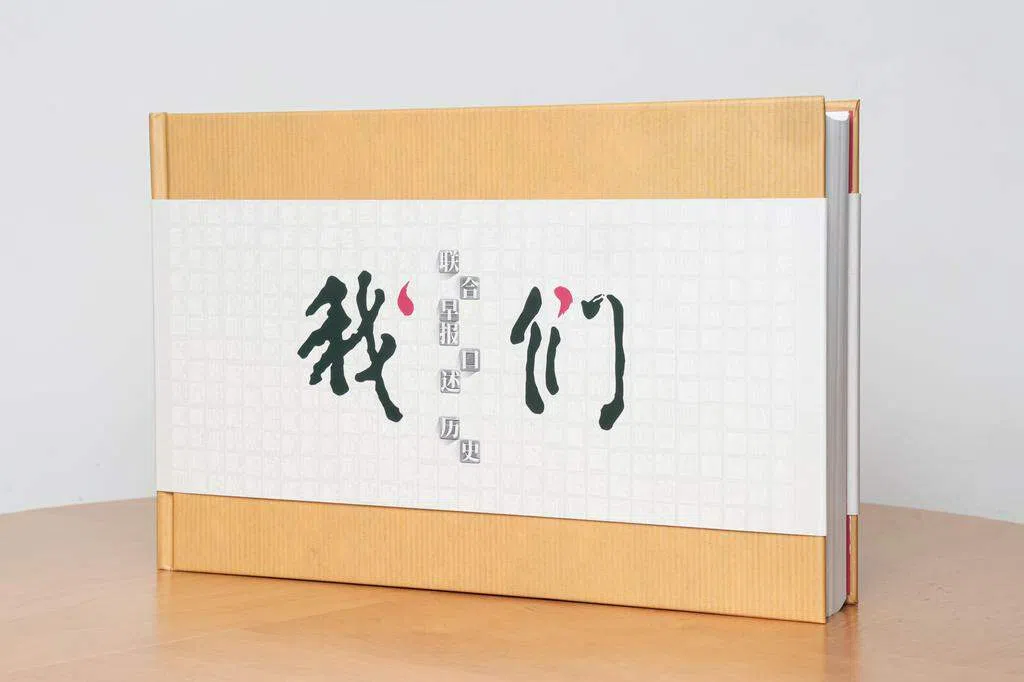从1967年开始为新加坡当时两大华文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撰写东京通讯稿件以来,本报前社论委员(1973-1989)卓南生教授的国际问题写作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曾经的时评,如今已成照见历史的明镜。卓南生2006年将200万字的日本时评结集出版,今年8月更将1973年至今的国际时评,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国际风云评析50年》上下册。新书分成四部分:一、国际热点问题追踪(1973-1975年);二、国际问题纵横谈(1979-1985年);三、汉城20年风云录(1973-1992年);四、安倍政治的“表”与“里”(2013-2022年)。
回顾半世纪的国际风云,卓南生受访时说,世界局势一直处在动荡之中,“缓和”“和解”与“和平”仍“位处边缘、表层的状态或大国的外交辞令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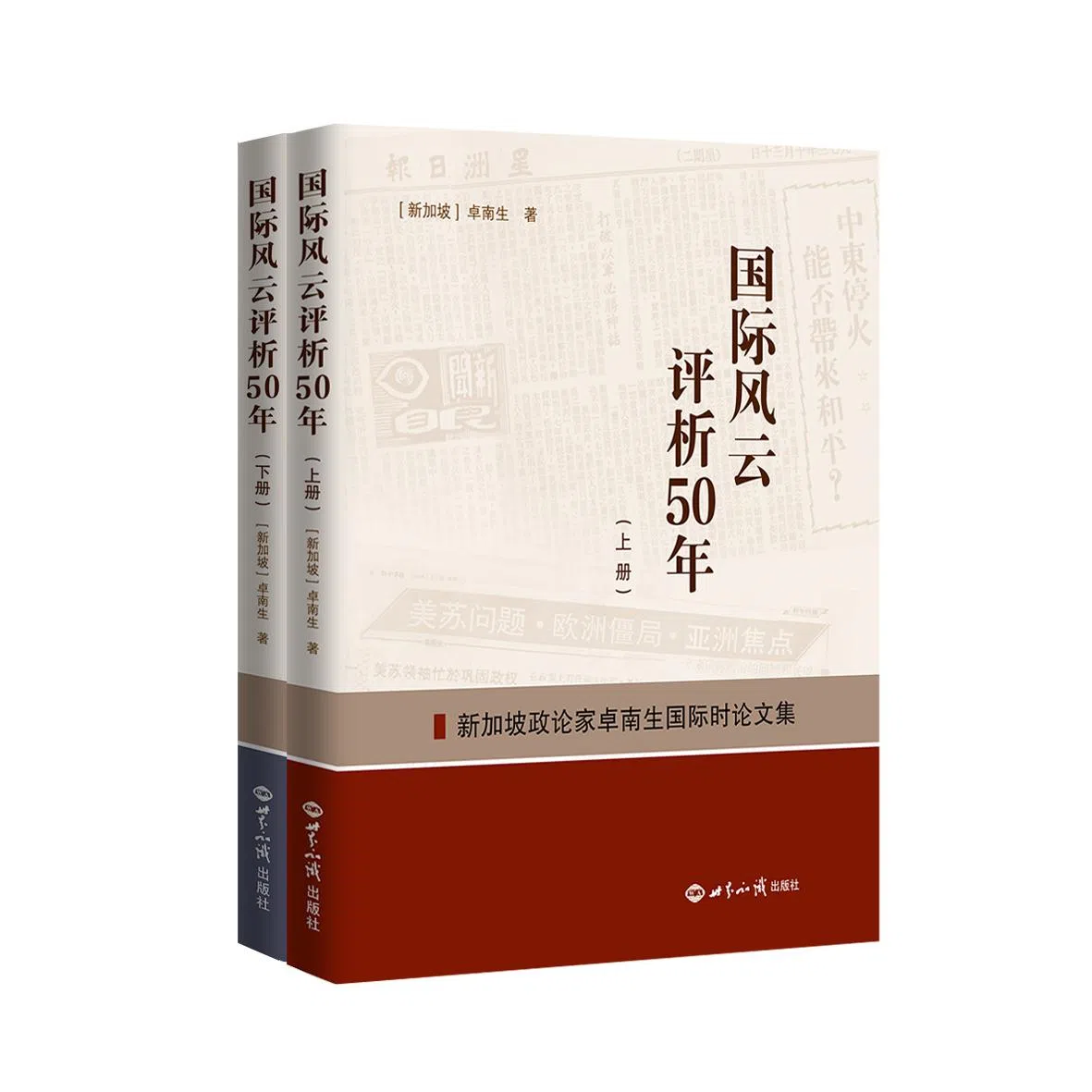
卓南生以近来升级的“巴以问题”为例,今日国际焦点往往是过去问题的延伸。他说:“就以‘巴以问题’而言,其根源与我50年前为《星洲日报》撰写的大量的有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社论与评论是一脉相承与相通的。本书收录的《中东炮火声中谈以阿战争》(1973年10月)等文章中,即简介犹太人的移民建国史、以色列国的诞生、四次中东战争的来龙去脉及由此造成巴勒斯坦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等难题,并着重指出‘以阿战争并非(简单的)宗教战争’的问题本质。”
早报首位特派员
1942年出生于新加坡,卓南生在华中与南洋大学接受教育,1966年负笈日本到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他在1973年加入《星洲日报》,撰写大量社论,接着在1983年历经了报业合并。对学术抱有理想的卓南生于1986年获得日本立教大学社会学(主修新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香港浸会大学的聘书。在他准备辞职离开报社之际,《联合早报》决定设立东京办事处,作为报社特派员制度的首个试点,诚意邀请卓南生担任第一位特派员,开疆拓土。卓南生希望在执教前能有采访国际大事的实战经验,于是展开近两年的派驻记者生涯。
留学日本、派驻日本,后来又在东京大学、日本龙谷大学任教,卓南生在日本生活超过30年,要不是疫情阻挠,他每年都会在日本住上几个月。在日本的朋友、师生给了他许多美好回忆。学生时代每周必访的东京神保町旧书店街、每次赴日必到的大学图书馆,以及他长居的京都,迷人的街巷、哲学之道,附近岚山、宇治川等名胜,令他难以忘怀。
忧心日本政治发展
回忆美好,但日本的政治发展仍令他忧心。
被问及日本鹰派势力抬头的问题时,卓南生回答,其实早在1947年战后日本实施和平宪法,部分日本保守政治精英就处心积虑要修改宪法,只是一直限于时局而没有进展。他指出,1990年代初期,日本政治从“国论二分”转向“总保守化”时期。前者指日本保守与革新派之间对国家出路的两种路线相持不下的时期,后者则指被视为日本修宪最大障碍的日本社会党消亡之后,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主导政局的时期。
“日本国内基本上已失去牵制当局修改宪法的政治力量。从这角度来看,日本宪法的修改,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在宪法尚未修改之前,日本当局对整军已情有独钟,一旦修宪成功,今后将否有如脱缰之马,这是各方视线之所在。加之战后日本当政者对教科书等事关史实和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等的问题一直采取回避乃至曲解的态度,日本的走向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
卓南生认为,日本大多数老百姓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爱好和平。不过在错误教科书与狭隘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彬彬有礼的普通人也可能走上战场。“这也就是为什么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篡改教科书、美化‘军神’与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保持高度警惕心理的原因所在。”
因为关心所以写作。
卓南生是学者也是时评人,学术论文与时评文章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对象也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得对自己所思所写的东西负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