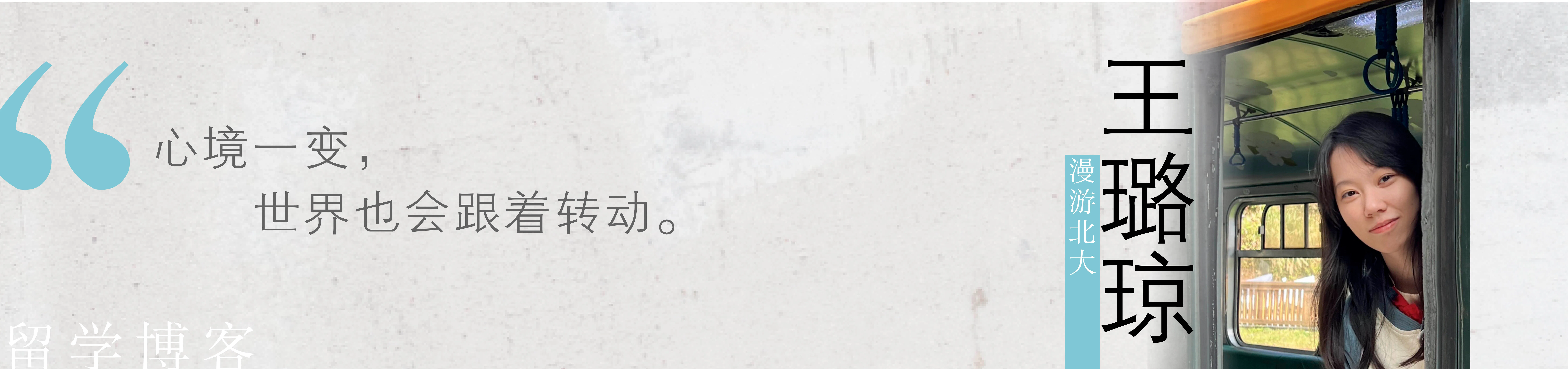“三月,天空中粉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 这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开头。当读到“似雨似雪的东西”时,只觉得十分唯美,但对于这个实际的“东西”会是什么,我想不到,小说也没能给出任何提示。直到四月的降临。我看到了那些飘浮在天空中,那些似雨似雪的东西。
它们先是出现在窗外,若不细心观察,几乎难以察觉它们的存在。接着,它们开始出现在我上下课的走廊,稍不注意便会悄然附着在我的身上。再然后,它们竟然形成了球形,在风中、路上围绕着我,不停翻滚。4月12日这天,我终于明白了它们的真相。
这天的整体基调是明亮且朦胧的,明亮是因为午后阳光,朦胧是因为北京的雾,这仿佛让我走进了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之中。朋友曾评价这部电影的影像表现,描述阳光如同薄雾一般缓慢地弥漫在整个画幅中,迷离的镜头像幻影一样,让他感到恍惚。所以,在泡影般的时空和空间里,参观杉本博司的摄影展《无尽的刹那》,似乎也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了。
摄影是瞬间的即时捕捉,电影是连续的时间流,而杉本博司选择拍摄记忆与永恒。走进展厅,站在《剧院系列》前,眼前呈现的是一排的黑白剧场。在星星飞驰的露天影院、在陈旧的戏院中,一部影片在播放。杉本博司操控着摄像机,从影片的开始到结尾,曝光持续不断。于是,影片失去了时间的维度,化作白色荧幕,化作从展览墙上、从头顶上方打下来的,摇晃的光。
朋友说,“人的眼睛是镜头,瞳孔是镜头的光圈。从落地后第一次睁开双眼的那刻起,到临终躺在床头阖眼的那刻为止,⼈类眼睛的曝光时间,只有一次。⼈一⽣依赖着映在视网膜上的倒立虚像,不断测量着自己和世界直接的距离。”我被这两句话打动了,若有所思地想到了什么,接着说道,“光不断穿入,世界持续曝光,所以人的一生是一张持续曝光的相片。过去的记忆不断堆叠,便会模糊并产生幻觉。所以每个阶段最开始时的记忆总是如此清晰,而后变得模糊。或许,在人生的尽头,最后浮现在眼前的就是这片白色荧幕。”我们俩的话语拼凑在一起,思绪也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延伸阅读

翻着朋友送的书,我发现杉本博司在《艺术的起源》中写下了这句:“记忆总是随着时间懵懂前行,甚至我都怀疑记忆不过是我的大脑捏造出来的一种幻觉。” 无独有偶,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也段相似的台词:“20年的功夫……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 回到自身,我又何尝不是在时间的间隙中反复探究一个确切的证明。
摄影展规模不大,但我们观看了三个小时。从建筑里出来后,天空中飘散着成堆的柳絮,时隐时现,朝着我的方向涌来。阳光明媚,和忽闪的柳絮叠加在一起,现实仿佛都在云朵之上。那晚,在小松原俊老师的吉他声中,我的思绪在舞台下慢慢沉淀。等到一切结束,我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柳絮再次迎面而来,车灯打过,他们在黑色泊油路上又亮起、翻滚着。我突然被王蒙的小说开头所击中,原来这似雨似雪的东西是柳絮啊!
“三月,天空中粉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 写下这句的王蒙,那时22岁。青年人的状态就像是那悬而未决的雨雪,他们处于世界的中间,看不清事物。这不仅贴合王蒙、故事里的林震,还有当时的姜文,和现在的我们。曝光仍在进行,若多年后回顾这天,我又会想起什么呢?
注释: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笔者在北京大学交换时,所修课程中读到的一篇文本。《无尽的刹那》是笔者与朋友在北京一起观看的杉本博司摄影展。《艺术的起源》是日本摄影师、建筑师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对自我创作回溯和追问的一本书。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笔者喜欢的一部电影。它们相互交叉使笔者写下了有关那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