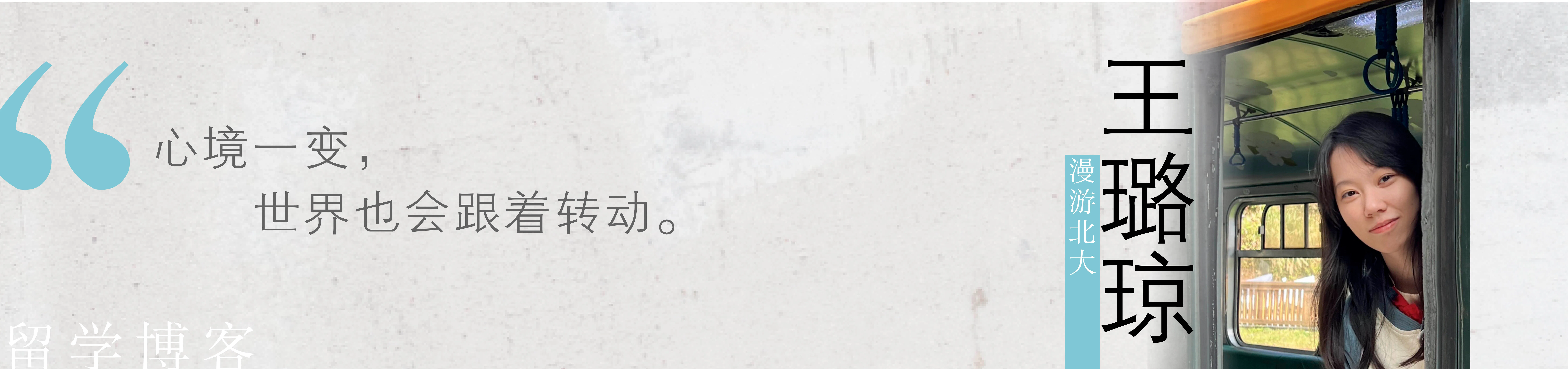在四季分明的地方上学,时间从漫长的夏天变成了四幅不同的油画。刚来时,冬天的白雪覆盖着每一寸土地,树木的枝桠像是冻住的标本。雪花上升后,生命被暖风唤醒,泥土和花朵在空中游玩。
夏季的北京温度不断攀升,有些日子的热度,甚至超过了新加坡。为了避开空气中的潮湿和闷热,午后我会蜗居在自己的宿舍里,选择在傍晚或夜间浅出水面。
北京的马路被分成两个区域,一条是供汽车行驶的车道,另一条则专门留给自行车(脚踏车)的骑行道。在车道与骑行道之间,有时会被一条绿化带隔开。穿行于中关村马路上,前方路灯的光线照射着我的瞳孔,过去、现在、未来仿佛被编织到了一起。无风,路边的小草便一如既往地守望四周。而我骑着车主动寻风,发丝飘向后方,视野中的两排路灯分散成了四排。
哈啰单车(脚踏车)陪我在傍晚的北京留下了很多道轨迹,其中最多是通往艺术的路线。我看过许多场电影和话剧,每次看完一部电影或是一场话剧后,内心总是充满了各种感触,但它们却似乎难以具象化。这时,我会觉得语言是特别奇妙的一种存在——它既简洁明了,也抽象复杂。我经常把文字看作是一种方块游戏,来回排列组合,便能超越其表面意义。
电影在虚拟空间中表演,话剧在真实空间中呈现。占据脑海最多的是一场叫《延迟》的默剧。那晚,我来到南锣鼓巷的蓬蒿剧场,在黑箱里观看默剧。蓬蒿剧场很小,但离观众很近。在黑暗中,人们若即若离。我坐在第一排偏中间的位置,等待烟雾散开,小雨出现。
《延迟》通过小雨荒诞的行为和肢体语言,表达了每个人心中隐藏的复杂世界。穿着病号服的小雨是一个有着短暂记忆的女孩。她游走在舞台上,穿越虚幻的火车站和泰坦尼克号的甲板,最终走向现实的那扇门。可以说,整部戏是由小雨的幻想支撑而成。导演通过背景音乐和小雨拥有的一些简单词汇,如“Jack”“苹果”“车票”,引导观众进入小雨的内心世界。
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雨身上,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有一个片段,小雨缓缓向我走来,停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她眼中的落寞和炙热,在这一刻透过眼眸展现在我的面前。谢幕后,导演菲利普·比佐上台致谢。他说,他与蓬蒿剧场的缘分像一场漫长的爱情。20年前,他在北京结束一场巡演时,偶然发现了蓬蒿剧场,从此开始了在这里的创作之旅。
那天的夜晚带着些许微醺的醉意。南锣鼓巷虽是个旅游景点,但蓬蒿剧场坐落在幽静的胡同里。推开分隔戏剧和现实的那扇门,我再次回到了白茫茫的路灯下,建筑的轮廓还是一样模糊。
我骑上哈啰单车,在马路上竭尽全力地踩着。商业化的北京一二环,在夜里还是如白天般耀眼。文学和艺术在后现代社会,在高楼大厦中显得颇为渺小。幸好还好许多这样的夜晚,很多需要人文缝补的缝隙在等待着我们。
车辆不多,路边行人零零散散,走这条路的人好像很少。我取消了导航,继续踩着哈啰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