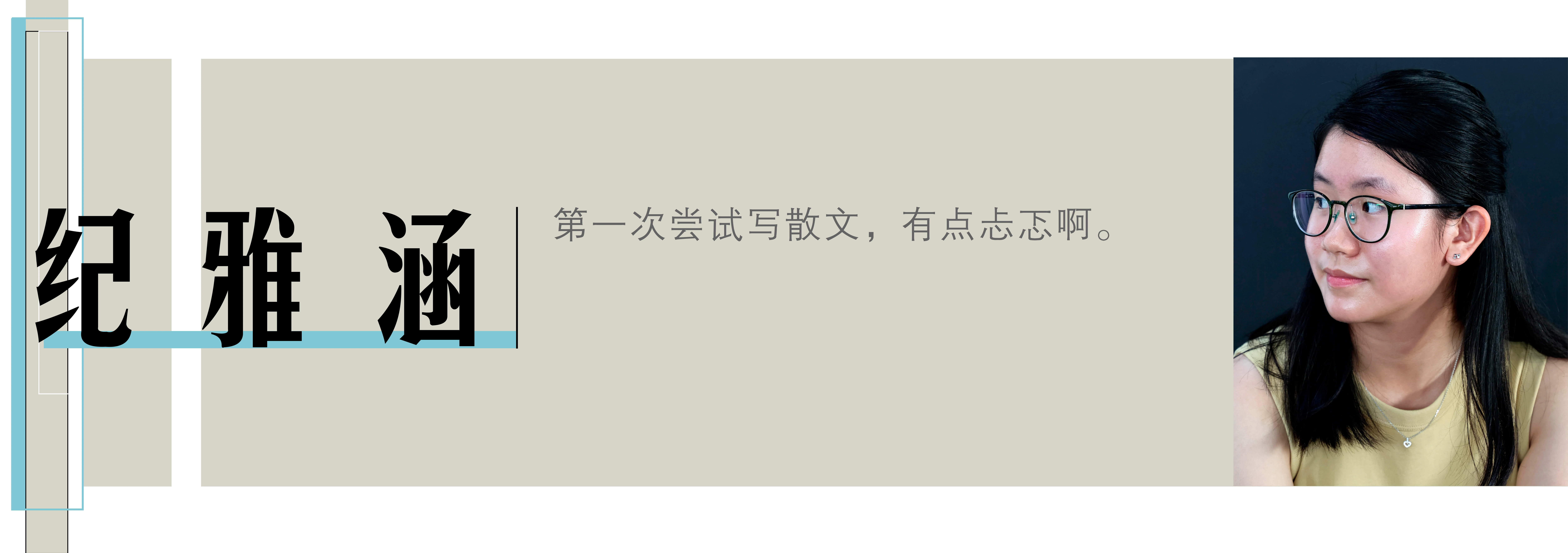“十年后,我们还会一起玩吗?”
在圣淘沙坐缆车时,我坐在最靠左的位置,头转向右边的三位儿时同伴。她们都是我小学的好朋友,不论在学校或在外头成天一起打打闹闹,直到四年前去了不同的中学才没有常常联络。那次我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和傍晚光线缓缓打到地上弯弯曲曲的道路,突然感慨也茫然失落。我望着她们,无力地问了这一个矫情的问题。
我一向早熟。上小学时,从四年级开始就有不认识我的大人以为我是中学生。到了中学,连自己的爸妈也觉得我比大学生还像大学生。可能是我长得比较成熟,短矮的鼻梁挂着一副黑眼镜,乖学生的标签早已形影不离地陪着我成长。
虽然现在离法定成年年龄还有一段距离(准确来说是一年),但是早熟的我,脑子并没放过这个烦恼和沉思的机会。
“未来你想做什么?”
刚中学毕业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的我们,随着对话的开展,总会问一问同伴这道问题。实不相瞒,我也喜欢问别人这个问题,看看别人对以后的规划和预想。但是自己被问到时,总是脑子一顿迟疑,明明之前和很多人都讨论过了,回答时却总是停停顿顿,无法坚定不移地说出答案。
或许是不喜欢幻想,那个充满未知数的未来。成年过后,开始为五斗米折腰的我,会是怎么样的?至少要逍遥快活吧!好似成人都是闷闷不乐的,有各种心慌意乱和烦躁不安。至少,对于以前一直想快点长大的我,这种欲望已经慢慢地消散了。我是真的早熟吧?
为什么我总是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小时候该玩耍该玩闹时,就想尽我所能讨好老师,觉得老师管教一班熊孩子好辛苦。再大一些,我狂追爱情剧,有韩剧也有陆剧,觉得深陷爱河的女主和男主真傻,总是擦肩而过或者迟迟不肯澄清误会,无端生出了忧伤和离别。那时,我的朋友们在看《蜡笔小新》和《熊出没》。
圣淘沙游玩那天,回家后,我仍是失落的。再一次和她们相见时,我依然不死心地重复问题,并问起那天缆车上她们是否听见。答案是肯定的,她们听见了,其中一位还笑我,没听清楚她当时那么大声的回复。
听见她们肯定而坚决地答应十年后的相约,我是吃惊的。现在想想,当初问问题的时候,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所以才没有听见其他的回复。大家长大成人,什么最最好的闺蜜,永生永世都在一块儿,都是空谈。分道扬镳才是常理,不是吗?
直到2024年最后两天,我抓紧时间清理旧物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在内心翻涌。我有一个黄色的盒子,专门用来装置朋友的信物和小卡片,里面有幼稚园牙牙班的生日卡,也有最近中学老师和朋友送的毕业信。我时不时会翻阅这些记录我生活的点点滴滴,看看在别人眼里我是个怎样的人。
或许是长大了,内心情感更丰富敏感了,那时整理盒子里的物件时,竟然落下了串泪珠子。就不知怎么了,感觉即使场景变了许多,周遭的人也换了,在她们的叙述里我似乎没什么改变:乖学生、责任感十足、好朋友。行行文字间,脑里也浮现出每个灿烂的定格,一张张从稚嫩变成沉稳的模样。
成长的道路上,我惊觉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在全球超过80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我曾经遇到这些可爱的人们,伴随我一点点长大和成熟。我对于相遇的感激,胜于一直折磨我许久即将到来的离别恐惧。谁又不害怕分别,和再也不见的威胁呢?遇到对自己好,能欣然接受自己优点和缺点的同伴时,谁又不想紧紧抓住不放手,恨不得日日相见,月月相伴?
想起托儿所老师的信里常写的一句名言:“再见”不是终点。“再见”是在我们再相逢之前我会一直想你。(Goodbye is not the end. Goodbye is I will miss you till we meet again.)
没事的,成年不该只代表悲伤和落寞,如果不成长又怎么会有这些美好的曾经?成年不是定格,它一直是个动词,代表往事的堆积,积成一条路,让你继续往前行时,不忘回头瞧瞧这一路上走过的风景和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