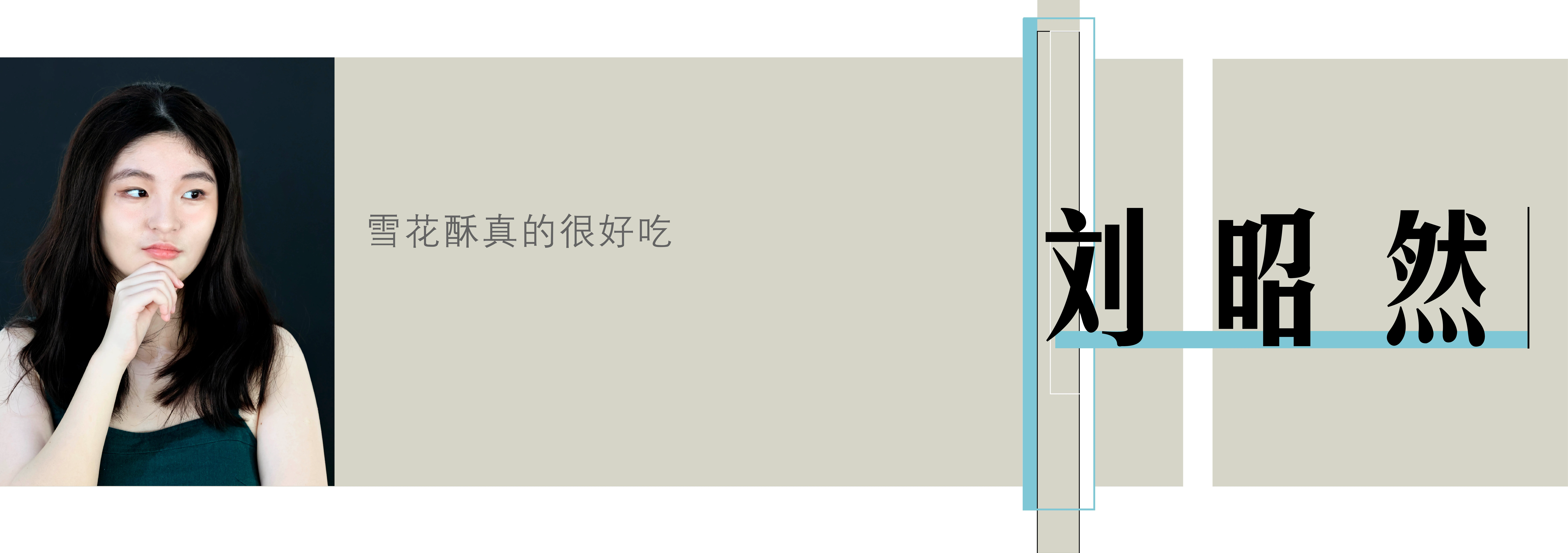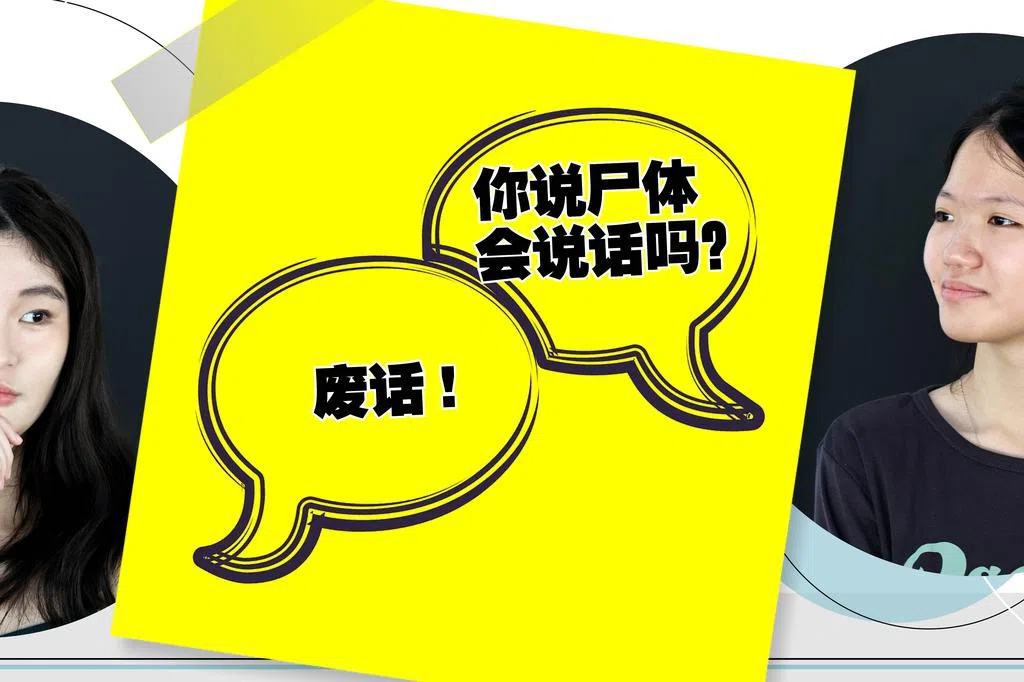海城的夏,总是来得迟。
5月将尽时,海雾还裹着半城楼房,湿漉漉地粘在红瓦上。待到6月初,那雾才被阳光一寸寸舔净,露出湛蓝的天色来。这时候,槐花便开了,细碎的白花藏在翠叶间。风一过,就簌簌地往下落,铺在青石板上,像是谁撒了一把碎银子。
我总爱踩着这些“碎银子”走。从家门口数起,33步,恰好能走到劈柴院的转角。那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支着个小小的摊子。一张褪了漆的木桌,两口铜锅,还有块被糖浆浸得发亮的大理石板。这便是记忆里最甜的地方了。
摊主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我们都唤她作“糖姐”。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那眸子清亮得很,像是刚被雨水洗过的玻璃珠子,映着铜锅里琥珀色的糖浆。她总爱扎个高高的马尾,发梢随着揉面的动作一晃一晃的,偶尔粘上些糖霜,便在阳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又来啦?”她见着我,眼角便弯成了月牙。手上的动作不停,腕子一翻,那团糖浆便在大理石板上铺展开来。花生、芝麻、蔓越莓干纷纷落下,被她用掌心轻轻压进糖浆里。这动作她做了千百遍,却每次都像在完成什么了不得的艺术品。
我最爱看她熬糖时的神情。铜锅架在小炉上,糖浆咕嘟咕嘟冒着泡,她的脸被热气熏得微微发红,睫毛上沾着细小的水珠。这时候的她最是专注,连呼吸都放得轻缓,仿佛怕惊扰了糖浆的变化。直到那琥珀色的液体泛起细密的泡沫,她才舒展开眉头,嘴角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尝尝。”她总是把第一块切给我。刚出锅的雪花酥还带着温度,咬下去时能听见“咔嚓”一声脆响,接着便是绵软的糖芯裹着果仁的香气在口中化开。那甜味很特别,不是糖果那种直白的甜,而是带着焦糖的醇厚,混着花生芝麻的油脂香,最后以蔓越莓的酸味收尾。我总舍不得大口吃,要一点一点地抿,让那滋味在舌尖多停留一会儿。
“糖姐”的摊子从午后摆到日头西斜。这段时间里,劈柴院的时光像是被糖浆黏住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卖蝈蝈的老汉摇着拨浪鼓从巷口经过,电车在远处的马路上叮当作响,隔壁茶馆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唱着黄梅戏。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却意外地和谐,像是专为配着雪花酥的滋味而存在的背景乐。
我从未想过这样的日子会结束。在我15岁的认知里,“糖姐”的摊子就该一直在那儿,像老槐树一样永远扎根在劈柴院的转角。
直到那年夏天,父亲递给了我一张机票。“去念书,”他说,“见见世面。”我盯着那张薄薄的纸片,默不作声。窗外的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几朵白花扑在玻璃上,又无声地滑下去。
临走前,我特意绕到劈柴院。“糖姐”的摊子却没出,木桌和铜锅都不见踪影。邻居说,她母亲病了,得回老家照料。我在转角站了很久,数着地上的青石板,一块,两块,三块……数到第33块时,一片槐花落在我肩上。
-
十年后再回来,劈柴院已经变了模样。青石板还在,老槐树也在,只是树下的摊子换成了一家连锁奶茶店。店里的姑娘用统一的语调机械地问着:“几分糖,去冰吗?”
我站在曾经数到33步的地方,缓缓抬头。槐花又开了。风一吹,那些细碎的白花便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蹲下身,在第33块青石的缝隙里,发现了一粒干瘪的芝麻。 我用指尖轻轻捻起它。十年了,它早已失去了香气,只剩下一点微不足道的重量。松开手指,那粒芝麻轻轻弹跳了两下,最终还是停在了石板原本的凹陷里。
奶茶店的门开了又关,带出一阵甜腻的香精气味。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第34块青石板上,一片完整的槐花正在阳光下慢慢卷曲。
如果没有如果,都已是十年后的6月,我又何必纠结那迟到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