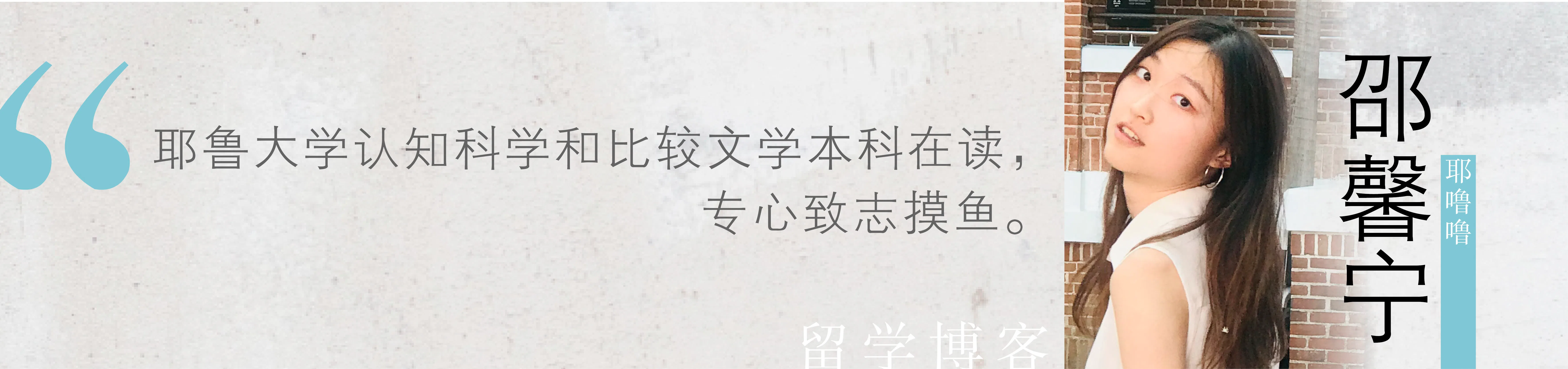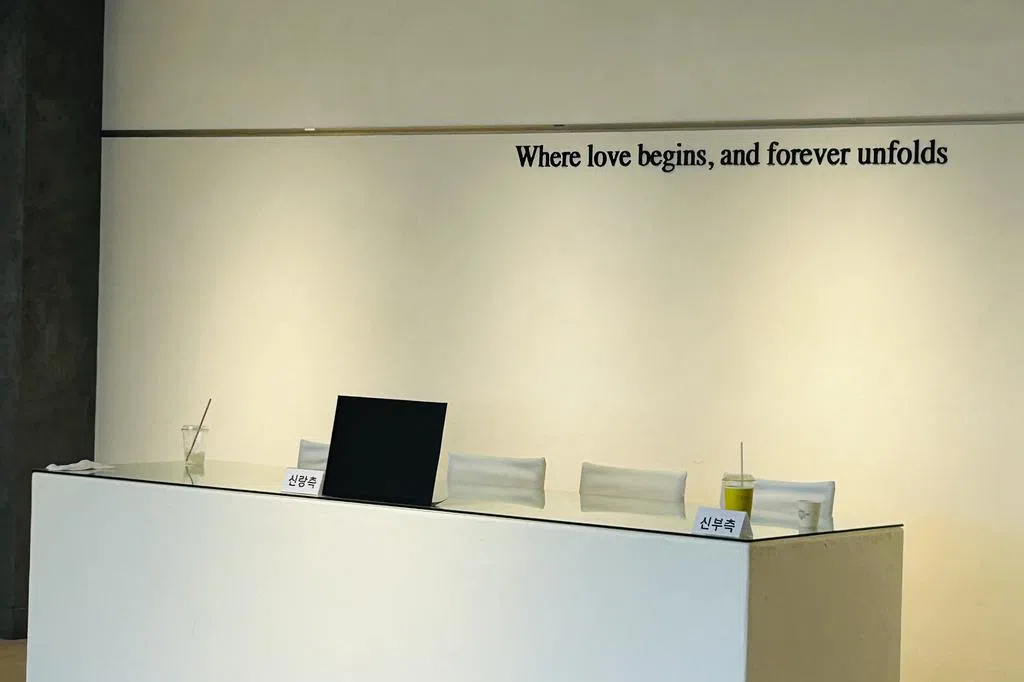我和中学时的朋友坐在首尔钟路某家咖啡店里。她第一次出国,也完全不会韩语,但点单时,她大大方方地举着翻译软件跟店主聊天,还能夸夸人家店里装潢好看。坐下来,我打趣说,你这确实看出来是东北孩子了,不怕生啊。她摆摆手:“出国之前有点怕,但昨天一落地,那个感觉就完全没有了。来都来了,有啥好怕的呢。”
中国东北的孩子,一般有两种。一种留在了家乡,另一种飞出来了,而且飞得很远。我们都是飞得很远的那种,所以觉得索性再飞远一点也不会害怕。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在南方打拼。现在一家人一起落到了南方,却也都共同在为房贷奔波。她说,我现在说“回家”,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指的是哪里。也不是东北,也不是南方,也不是那栋房子,可能就是我们仨在一起的地方。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提起“家”,我第一个想到也是我们一家三口,但不是在一个房子里,而是每次去机场的那辆车里。我爸在开车,我妈坐在我旁边,后备箱里装着那两个陪了我快十年、磨到破皮却依然坚挺的行李箱。我看着窗外,北方平原的雪地在车窗外流动着,像江水,不知道是它在送我,还是我在送它。我习惯了这样飘着,一开始不愿意把宿舍叫“家”,结果现在每年搬家搬到麻木,连管回到暂时只住两天的酒店叫“回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是啊,”她说,“东北人毕竟有游牧民族的基因嘛。”
可是什么“四海为家”,其实是“四海无家”吧?
我跟她说起最近那段让我很难放下的感情,是因为在那个人身上,我好像看到了自己落地的可能性,我看到了一种我从未期待过的,稳定的、平淡却幸福的生活。我细数着我和那个人有多么合拍,我可以想象和他像家人一样打闹、争吵、吃饭睡觉。她吸着咖啡,看着我,轻轻地说,“原来你在找家啊。”
原来我在找家啊。
她说,她回老家的时候,别人都说像我们这种飞出来的孩子,有出息、有能力,独立、坚强,但好像有点冷血、有点不通人情。“那些亲戚都说,这孩子心太野、想要的太多,连家都不回了。可是谁不想要家啊?只不过是家已经回不去了。”
她问我有没有回过老家看看。我想了想,去老家祖坟拜访的经历已经不太记得了,可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去看望太爷太奶。他们的骨灰葬在嫩江里。我们开车到嫩江公路大桥,第十一盏路灯的地方,把准备好的鲜花、包子和酒洒进江水,那时候我还没有栏杆高,伸着胳膊抓住栏杆向下看,江水就那样不停地从我脚下流过去,看久了就会开始眩晕,仿佛会被吸进去,觉得不是江水而是我在流动,怎样也停不下来。
我提起有一次韩语课,让我们画一年后、五年后和十年后的自己。她说你画了什么?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副三个火柴棍人走路的简笔画递给她,她看了看说,“都是在路上哦”。我说对。这是不是我落不下来的原因?我想到的,美好的未来,只能是一直在路上。
因为我们是看着江水长大的孩子。可是江水要流到哪里?
我们有一会儿没说话。她戳了一口蛋糕,叉子敲在盘子上,声音清脆。
她说:“十年前,你能想到我们现在正坐在这里吗?”
十年前,我们在上初三。我们座位中间只隔了一个过道,那时候中午她总会分享给我从家里带的长白糕,我总是很期待读到她的作文。那个夏天我们准备中考,73个人挤在一间没有冷气的教室里。我们那一届的校服是公认有史以来最丑的,我们那一届的中考成绩很高,但我们两个都没有考好。我说,那个时候我好像真的没想过以后会怎么样。她说,我也没有,那个时候也想象不到,十年之后,我们还能这样坐在一起,就像没分开过一样。
窗外天开始黑了,透过窗户的倒影,我们看到旁边一对韩国情侣也安静地各自喝着一杯冰咖啡,女生在看书,男生在平板电脑上写写画画。我说,再十年后,可能我们还坐在这里呢。
她说,“对啊。毕竟我这次办的韩国签证是十年有效期,钱都花了,不来白不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