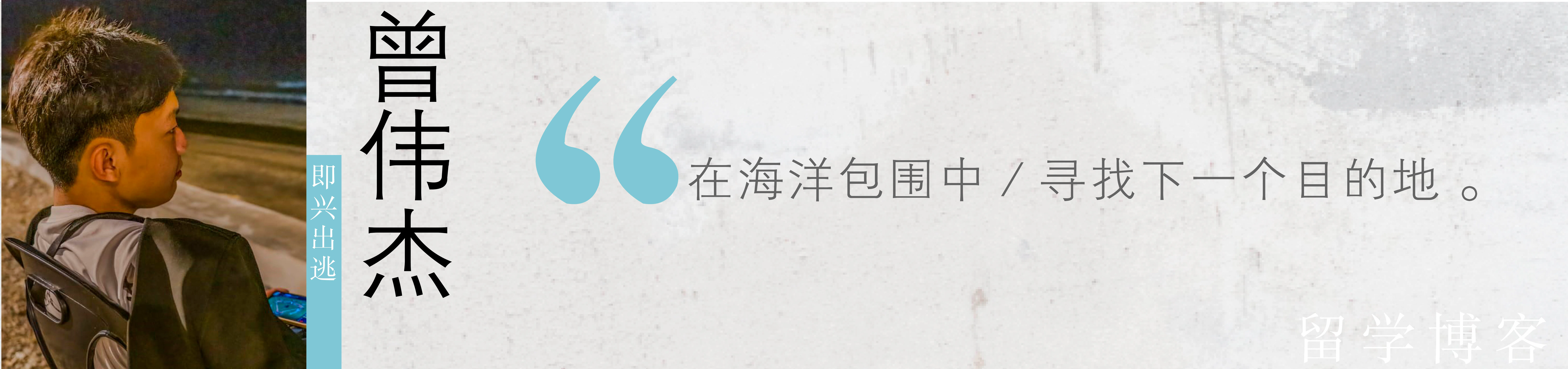回来近两个月,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在台北的我常常被迫走路。
台北的公车不算方便,租到一辆Ubike也往往是小概率事件。无论想往哪儿去,从捷运站出来,往往还得再走上一段。在这座总是阴雨绵绵的城市,穿着布鞋踏在路上,没多久就湿透。从伞檐下看出去的街道,遍处都镀上一层薄薄的水。
当然,台北街道并不漂亮。建筑的瓷砖外墙多已褪色,商店的卷帘门上布满随手涂就的涂鸦,行人道和骑楼也常被机车占满,只留一点勉强能通行的空间。
慢慢走,在不同的时间走,城市的脉搏经络便缓缓浮现出来。
若是在清晨时分,颓唐的街道可能就变成人声鼎沸的市场,卖菜的大叔大婶吆喝,屠夫的刀剁在砧板上,早餐摊子油锅沸腾的声音。空气里混杂着生鲜的腥气与油炸的香味。
一种有秩序的混乱,或者混乱中的秩序。
有一次,下课后在台大周边闲晃,偶遇一家书店。大门敞开着,一对母女守着电视机前关注大罢免,并没有理睬我。我自顾自地在书架间随意浏览着,突然一位老伯闯进来,把一份文件拍在柜台叫女儿签。三人随即用台语吵了起来。我听不大懂,但从只言片语里能隐约猜到,这是父女对于书店债务的争执。女儿最后愤而骑车离开,老伯在风扇前坐下,沉默着喝水。
在书架之间躲藏许久,最终我还是拿了一本书走到柜台,结账时老伯给我打了七折。我匆忙收下找零离开书店,回家的路上这件事一直缠绕在心头,等回到宿舍后才后悔——书自有其价,我或许不该接受他的折扣。
之后仍旧经常走路,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家书店。
回到新加坡,手机的计步功能告诉我走得少了。这里的公交精确而高效,下车就是目的地,街道仿佛只是两点之间的连线,走路只是无谓的消耗。
即便偶尔想绕远,我也总觉得在组屋区的街道也难碰上什么新鲜事。更多时候只是在相似的走廊间迷路。邻里中的购物中心千篇一律,每一座都像彼此的克隆生物体。若某天想逛点特别的,比如想淘些二手游戏光碟,只能往市中心跑,可那对我来说是45分钟车程以外的地方。附近的公园倒是整治得不错,但赤道的太阳无所谓四季,惧热如仇的我,往往打消念头蜷缩在沙发之中。
但事情总有意外。
返新后的某个晚上,我参加完城市阅读节的讲座,想着既然难得来到市中心,在前往地铁站的路上,我特地绕了一段远路。
沿途我用手机的灯光读完达豪施纪念碑上的碑文。沿着加文纳桥跨过新加坡河,抬头可见宏伟的富丽敦酒店。河面被霓虹染上紫蓝色,一侧是热闹的克拉码头和半轮月亮,另一侧则能望见摩天轮与天际线的轮廓,当时浑然不知父母过去曾站在同一处凝望大海——我已沉浸于这座城市的温柔之中。
以相对慢速的方式前进,行走,是了解一个城市的最佳方式。其真实面貌存在于巷子深处、拐角之后、在地图未标示的最快路线之中。
现在我仍记得台北的雨巷,如今也会记得夜晚的加文纳桥。于是我明白,无论在何处,行走,总有它的必要。